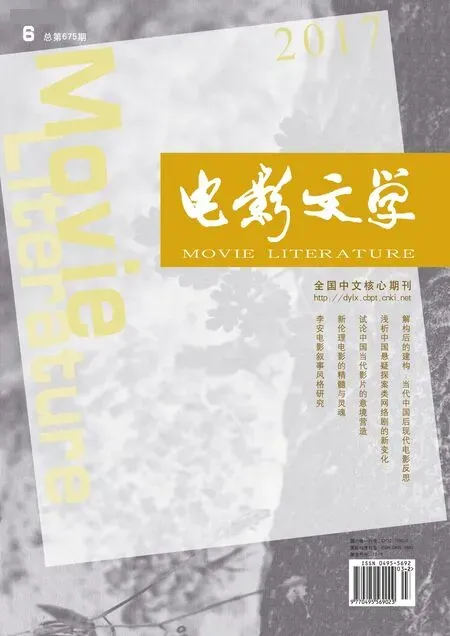奧斯卡獲獎(jiǎng)黑人女演員生態(tài)困境研究
李 莉 范忠影
(東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文法學(xué)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30)
從電影社會(huì)學(xué)的觀點(diǎn)來看,電影不僅是一門藝術(shù),由于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緊密相關(guān),所以其既是人的欲望的投射,也是整個(gè)社會(huì)思想、文化的反映。單就社會(huì)映射而言,電影的演員——角色形象無疑是社會(huì)思想最重要的表現(xiàn)及傳播的載體。那么,獲得奧斯卡獎(jiǎng)項(xiàng)的黑人女演員便兼具兩個(gè)方面的意義能指:一是作為黑人女演員在電影工業(yè)系統(tǒng)中的生態(tài)意義,二是所飾演角色展現(xiàn)出來的美國黑人女性真實(shí)的生活、生存困境。
黑人女演員作為一個(gè)特殊的群體依然是黑人女性的一部分,黑人女性受男性和白人雙重宰制的生態(tài)困境,也直接或間接地體現(xiàn)在黑人女演員身上。所以,黑人女演員不僅自身要承受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宰制,還要通過其扮演的角色形象來表現(xiàn)黑人女性所遭受的歧視。獲得奧斯卡獎(jiǎng)項(xiàng)的黑人女演員因其更大的代表性、社會(huì)影響力以及關(guān)注度,相應(yīng)地具有更大的解讀和詮釋空間。本文即以生態(tài)女性主義理論為基礎(chǔ),以獲得奧斯卡獎(jiǎng)項(xiàng)的美國黑人女演員為對(duì)象,對(duì)黑人女演員及其承載的黑人女性形象的生態(tài)困境進(jìn)行深入研究。
一、奧斯卡金像獎(jiǎng)和女性生態(tài)主義
生態(tài)女性主義是相對(duì)邏各斯中心主義而言的,認(rèn)為“‘女性’已成為一種文化隱喻,代表了人類歷史上所有曾經(jīng)或尚處于邊緣地位,飽受男性/人類/資產(chǎn)階級(jí)/西方/白人等占統(tǒng)治地位的壓迫者欺侮的弱勢(shì)群體”[1]。主張改變?nèi)私y(tǒng)治自然思想以及父權(quán)價(jià)值觀,關(guān)注所有二元論中那些處于弱勢(shì)地位的一方:這其中既有女性、有色人種等被剝削階級(jí),還有自然、東方等外在的方面。
奧斯卡的生態(tài)女性觀對(duì)黑人女演員及其扮演角色的生態(tài)問題的研究尤為重要。對(duì)黑人女演員而言,奧斯卡的生態(tài)主義立場(chǎng)可以從種族和性別兩方面進(jìn)行剖析。一方面,奧斯卡獲獎(jiǎng)影片體現(xiàn)出濃重的種族歧視。西德尼·波蒂埃憑借《原野百合花》獲得第36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jiǎng)。西德尼·波蒂埃是第一位獲此獎(jiǎng)項(xiàng)的黑人演員,然而《原野百合花》卻是在肯尼迪遇刺、舊種族歧視法被廢除等事件背景下公映并獲獎(jiǎng)的。波蒂埃就曾說:“如果我不能獲獎(jiǎng),800萬黑人會(huì)砸爛電視的。這我可賠不起了。”最著名的奧斯卡獎(jiǎng)項(xiàng)歧視黑人的事件,是第45屆最佳男主角獎(jiǎng)獲得者白蘭度(《教父》中飾教父),認(rèn)為好萊塢歧視美洲印第安人,并因此拒絕出席頒獎(jiǎng)典禮。此外,無論是以白人視角審視種族主義問題的《撞車》(第78屆奧斯卡獲獎(jiǎng)影片),還是描述白人與有色人種和諧關(guān)系的《與狼共舞》(第63屆奧斯卡獲獎(jiǎng)影片),都透露出白人中心的美國文化觀。另一方面,奧斯卡獲獎(jiǎng)影片的女性形象體現(xiàn)出性別歧視。獲獎(jiǎng)奧斯卡影片中兩類女性最為常見:一類是扁平化存在的女性形象。從早期的《關(guān)山飛渡》(第12屆奧斯卡獲獎(jiǎng)影片),到中期的《虎豹小霸王》(第42屆奧斯卡獲獎(jiǎng)影片),女性形象都是點(diǎn)綴和陪襯,僅起到性別符號(hào)作用,在電影敘事中無足輕重,無論是白領(lǐng)、主婦還是酒吧女都是男性形象的附屬,活色生香的女性被類型化和扁平化。另一類是情色類型化的女性形象。從《亂世佳人》(第12屆奧斯卡獲獎(jiǎng)影片)中的費(fèi)雯麗,到《羅馬假日》(第26屆奧斯卡獲獎(jiǎng)影片)中的奧黛麗·赫本,“女性被按照種種目的和因由隨意地塑造和變形,在銀幕隔離起來的外部和內(nèi)部世界里,女性實(shí)質(zhì)上都沒有權(quán)利,沒有地位”[2]。種族和性別兩個(gè)方面表明,對(duì)奧斯卡而言,黑人女演員以及女性形象既在社會(huì)的宏觀層面被種族歧視所壓制,又在電影的微觀層面被性別歧視所困擾,綜合而言,就是為整個(gè)電影系統(tǒng)所宰制,處于奧斯卡生態(tài)中的底層。
二、黑人女演員的生態(tài)困境
黑人女演員的生態(tài)困境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電影受眾和電影工業(yè)系統(tǒng)。一方面,電影受眾在極大程度上限制了黑人女演員的生存空間。“黑人是票房的死神”,這句話曾作為格言,在好萊塢流行一時(shí)。因?yàn)樵诿绹兹酥辽系臅r(shí)代,白人對(duì)反映黑人生活的影片和黑人演員是不屑一顧的。受眾狹窄,票房沒有保障,電影公司不愿意向黑人電影進(jìn)行投資,獨(dú)立電影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資金和市場(chǎng)保障等,以上這些因素導(dǎo)致黑人女演員很少有機(jī)會(huì)參與黑人電影的拍攝。同時(shí),符合美國白人觀眾口味的黑人電影,也多是經(jīng)過導(dǎo)演們量身定做的“偽黑人電影”,這些電影對(duì)于黑人的現(xiàn)實(shí)生活和心理世界的表達(dá)和描寫是蒼白的;同時(shí)由于導(dǎo)演的白人身份,無法完全從黑人的角度真實(shí)地反映歷史、事件和人物。因此黑人女演員或是被排除在“偽黑人電影”之外,或是飾演那些缺少生活和生命體驗(yàn)的“黑膚白心”“偽黑人”形象。直至20世紀(jì)60年代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xié)進(jìn)會(huì)與工會(huì)組織聯(lián)手施壓后,陸續(xù)才有黑人女演員們出演了影片中的重要角色,但這些角色是眾多白人演員包圍下的“一點(diǎn)黑色”,黑人女演員的符號(hào)意義大于實(shí)際意義。
另一方面,電影工業(yè)系統(tǒng)中黑人編劇、導(dǎo)演、制片人等“黑色”生態(tài)環(huán)境匱乏,進(jìn)一步限制了黑人女演員的發(fā)展空間。黑人女演員的電影生態(tài)環(huán)境十分惡劣,幾乎體現(xiàn)在電影制作的所有環(huán)節(jié):從拍攝前的制片人意向、故事構(gòu)想、編寫劇本、選擇演員,到拍攝中的鏡頭分配、演員支配、角色表演、演員薪酬,再到拍攝后的剪接、配樂、預(yù)告片、宣傳等。比如據(jù)《人物》周刊統(tǒng)計(jì),20世紀(jì)70年代,在美國只有2.3%的電影導(dǎo)演和不足2.6%的電影編劇是黑人。毫無疑問,占絕大多數(shù)的白人導(dǎo)演和編劇的生活環(huán)境大多與黑人無關(guān),他們只會(huì)寫和拍自己熟悉的白人生活,更大程度上以白人演員、白人受眾為基礎(chǔ)進(jìn)行電影的制作工作。黑人導(dǎo)演和編劇數(shù)量不足,在極大程度上抹殺了黑人女演員出演電影作品的機(jī)會(huì)。再如薪酬,哈莉·貝瑞獲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后,在好萊塢年薪為1500萬美元,而相同經(jīng)歷、地位的白人女星則能達(dá)到4500萬美元,差距巨大。20世紀(jì)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黑人電影的文化被人接受,環(huán)境得到改善,專門培養(yǎng)黑人的電影學(xué)校才得以出現(xiàn),在一些綜合高校中,黑人學(xué)生與白人學(xué)生可以同時(shí)接受電影藝術(shù)專業(yè)培養(yǎng)。
此外,奧斯卡獎(jiǎng)項(xiàng)的運(yùn)行機(jī)制對(duì)黑人女演員極不公平。奧斯卡獎(jiǎng)項(xiàng)的提名和獲獎(jiǎng),掌握在6000多名會(huì)員手中,其中94%會(huì)員是白人,70%會(huì)員是男性。因此,對(duì)于黑人女演員而言,要比大多數(shù)黑人男演員以及絕大多數(shù)白人演員都優(yōu)秀,才有可能獲得奧斯卡獎(jiǎng)項(xiàng)。
三、獲得奧斯卡獎(jiǎng)項(xiàng)黑人女演員所扮演黑人形象的生態(tài)困境
(一)獲得奧斯卡獎(jiǎng)項(xiàng)的黑人女演員
獲得奧斯卡獎(jiǎng)項(xiàng)的黑人女演員共6位。哈蒂·麥克丹尼爾是歷史上第一位獲得奧斯卡獎(jiǎng)項(xiàng)的黑人演員,在《亂世佳人》中扮演女仆瑪格麗特,獲得第12屆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jiǎng);烏比-戈德堡在《人鬼情未了》中飾演靈媒奧塔,獲得第63屆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jiǎng);哈莉·貝瑞在《死囚之舞》中扮演死囚羅倫斯的妻子莉蒂莎,獲得第74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jiǎng),成為歷史上第一位獲此殊榮的黑人女演員;詹妮弗·哈德森在《追夢(mèng)女郎》中扮演歌手埃菲,獲得第79屆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jiǎng);莫妮克在《珍愛》中飾演瓊斯,獲得第82屆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jiǎng);奧克塔維亞·斯賓瑟在《幫助》中扮演黑人女仆米妮·杰克遜,獲得第84屆奧斯卡最佳女配角。
(二)黑人女性角色的生態(tài)困境
以上六部電影反映出兩方面問題:一方面是六部電影中的黑人女性形象群像都是底層小人物。在影片中,白人塑造的英雄形象,對(duì)于好萊塢的制片人更具有吸引力。因此,雖然很多電影中出現(xiàn)了黑人女性,然而這些影片卻并不屬于她們,她們飾演影片中不重要的角色。哈莉·貝瑞就曾說過:“至今我苦惱的是好萊塢里我是個(gè)女人,不是演員。”現(xiàn)實(shí)中黑人女演員個(gè)體還會(huì)因膚色、性別差異而被區(qū)別對(duì)待,美國電影中的黑人女性形象幾乎成為類型化的符號(hào),黑人女仆、黑人女招待、收銀員、妓女等是黑人女演員在電影中扮演最多的黑人女性形象。受類型化限制,黑人女性角色很難體現(xiàn)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的黑人女性,也很難表現(xiàn)黑人女性豐富多彩的內(nèi)心世界。以上六部電影中,我們看不到黑人主婦、黑人女教師或是黑人女公務(wù)人員的日常生活和內(nèi)心世界。此外,以上六部電影中除了《亂世佳人》和《人鬼情未了》之外都直接表現(xiàn)了黑人女性的生態(tài)困境:處在社會(huì)邊緣地位,被白人歧視,被男性欺侮,無所適從,無處可棲。
哈蒂·麥克丹尼爾、奧克塔維亞·斯賓瑟扮演的都是黑人女仆。“黑人女仆”是美國電影中黑人女演員扮演角色的代表,僅哈蒂·麥克丹尼爾就扮演過40多個(gè)女仆形象。《亂世佳人》中雖然表現(xiàn)了白人主人和黑人仆人間的和諧關(guān)系,但黑人女仆瑪格麗特依然在客觀上表現(xiàn)了其卑微的社會(huì)地位。《幫助》沒有從血腥、暴力的角度去表現(xiàn)種族歧視,而是以白人家庭和黑人女仆群像的方式講述小鎮(zhèn)上黑人女仆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比如黑人女傭康斯坦丁在斯基特家中工作了26年,卻因?yàn)椤皳p害”了斯基特母親的面子而被攆回鄉(xiāng)下,郁郁而終;西麗太太從不照顧自己的孩子,卻以保護(hù)孩子健康的名義,建立“家庭幫傭衛(wèi)生守則”,為黑人女傭建立單獨(dú)的戶外衛(wèi)生間并視為恩賜。這些黑人女仆類似的命運(yùn)表明,種族歧視下黑人與白人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黑人并未能真正融入美國主流社會(huì)。
《人鬼情未了》中烏比-戈德堡扮演了一個(gè)騙子、靈媒;奧塔奇特、夸張的造型以及在劇中對(duì)白人的怯懦都表明她毫無社會(huì)地位。《死囚之舞》中哈莉·貝瑞扮演的是黑人女招待——和黑人女仆一樣最常見的黑人形象。《死囚之舞》中莉蒂莎深刻展現(xiàn)了種族歧視下黑人女性的生活、生存困境。泰路偷吃巧克力,莉蒂莎則告訴泰路:“在美國,作為黑人,不可以那樣胖。”“莉蒂莎在給泰路傳遞著美國黑人生存的價(jià)值觀,莉蒂莎希望能夠融入美國白人社會(huì)。”[3]種族歧視使莉蒂莎無法信任白人社會(huì),在白人警察要給泰路做尸檢時(shí),莉蒂莎并不相信,貝克解釋警方想查出肇事司機(jī),莉蒂莎更加質(zhì)疑:“你認(rèn)為他們真的會(huì)查?”莉蒂莎先后失去了丈夫和兒子,因?yàn)闊o力還貸而被攆出了住所,莉蒂莎走投無路,處在絕境之下,只能以愛的名義與貝克一起生活——即使貝克是自己丈夫死刑的實(shí)際執(zhí)行者!受困于貧窮和膚色,黑人女性一直生活在社會(huì)邊緣,自尊、自愛意識(shí)與生存相比,是無足輕重的,她們只能放棄它們。
《珍愛》中莫妮克扮演的瓊斯是一個(gè)又丑又胖的黑人女孩,因被父親性侵,16歲的瓊斯兩次懷孕,與殘暴的母親決裂后獨(dú)自帶著兩個(gè)孩子生活,但又患上艾滋病。瓊斯的人生飽經(jīng)磨難,慘淡而無奈,父親的強(qiáng)暴是男性對(duì)女性宰制的直接體現(xiàn),而母親因?yàn)椤八?指瓊斯)搶走了我的男人”而十分殘暴地對(duì)待瓊斯,則是男性權(quán)威根深蒂固之下女性的荒誕和無奈。對(duì)于生活在底層、被侮辱和被傷害的瓊斯而言,父母就是男性權(quán)威的具象,是生命悲劇的根源,是生態(tài)困境的直接體現(xiàn)。“瓊斯的遭遇不是每個(gè)黑人女性都會(huì)經(jīng)歷的,然而很多黑人女性都能夠找到某些影子,電影中那些每天都生活在擔(dān)驚受怕中的黑人女性是對(duì)美國黑人生活的真實(shí)寫照。 ”[4]
《追夢(mèng)女郎》講述了三個(gè)黑人女孩追逐美國夢(mèng)的故事,美國夢(mèng)也是電影表現(xiàn)黑人的經(jīng)典主題。劇中懷特和蒂娜的命運(yùn)則表現(xiàn)了黑人男性對(duì)黑人女性的宰制。泰勒為包裝歌唱組合,因?yàn)榈倌韧庑戊n麗,可塑性強(qiáng),便頂替了唱功最好的埃菲·懷特成為主唱;深愛著泰勒的埃菲因失去領(lǐng)唱地位深受打擊,最終被泰勒排擠出組合;蒂娜與泰勒結(jié)婚,成為一代偶像,卻又遭到泰勒的欺騙和背叛,身心疲憊。雖然最后是歌舞劇類型片的完美結(jié)局,但泰勒對(duì)懷特和蒂娜的背叛和欺騙卻顯得異常沉重,玷污了埃菲和蒂娜心中的愛與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