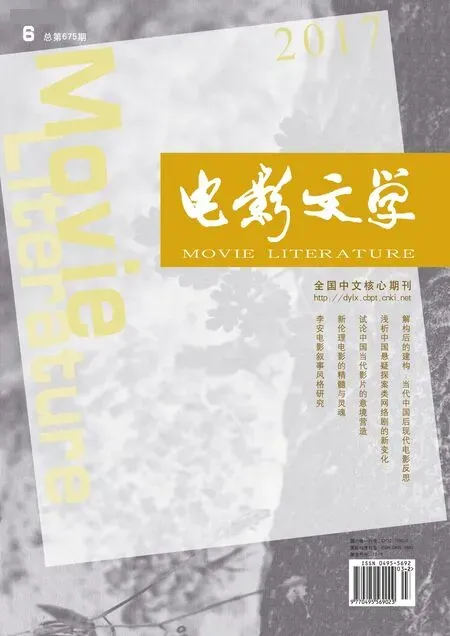波蘭斯基影片中的欲望書寫
張文娟
(內(nèi)蒙古大學(xué)滿洲里學(xué)院,內(nèi)蒙古 滿洲里 021400)
出生于20世紀(jì)30年代的法國導(dǎo)演波蘭斯基是一位世界級的電影大師,如今已年逾80的他依舊沒有停止創(chuàng)作,并在影片中不斷對一些關(guān)乎人性的基本主題進行探討。波蘭斯基在他六十余年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獲得了很多榮譽,他的電影涉及過很多不同的題材,如涉及真實歷史與猶太民族命運的《鋼琴師》,改編自經(jīng)典莎劇的《麥克白》等。但在波蘭斯基豐富的創(chuàng)作序列之中,有一部分電影的模式和主題十分相似,即在封閉空間情境中對性別、身份主題的探討,包括《水中刀》《苦月亮》《不道德的審判》《殺戮》《穿裘皮的維納斯》等。
在這一序列的影片中,波蘭斯基試圖探討人性中某些基本主題,他從不忌憚在自己的電影中將欲望推至極限,封閉空間將背景環(huán)境和人物原本的社會關(guān)系都最大限度地去除了。在相對隔絕的處境之下,人物之間的關(guān)系開始發(fā)生轉(zhuǎn)變,流動的欲望主宰了人物的情緒和行動。波蘭斯基對欲望的展示往往通過兩性之間的角力展開,他一方面在構(gòu)建不同的性別主體,一方面又在不斷尋找這種構(gòu)建之中的裂縫,并在敘事的進程之中不斷擴大裂隙,實現(xiàn)反常規(guī)的突破。在這種絲絲入扣的深入過程中,一切都顯得匪夷所思卻又合情合理。波蘭斯基似乎很享受這種打破觀眾心理期待和心理底線的過程,在封閉空間的隔絕之下,他試圖摒棄既有的社會構(gòu)建,直接深入到人性最深處探索其本質(zhì),而欲望這一無法被窮盡的話題即為導(dǎo)演的著力點。
一、欲望的產(chǎn)生:性的壓抑與釋放
波蘭斯基影片中的欲望書寫往往有一個完整的過程,影片中出現(xiàn)的人物原本有著正常的社會背景和固定的社會關(guān)系,然而隨著情節(jié)的推進,人物與社會的關(guān)聯(lián)逐漸被遺忘,人物之間的關(guān)系開始松動、變質(zhì),原本在社會身份下被抑制的東西被不經(jīng)意間釋放。在《水中刀》中,原本只是一對夫婦與一位青年男子的普通出游,最后卻產(chǎn)生了丈夫與男子的爭斗;《苦月亮》中的癱瘓作家和性感嬌妻咪咪之間維持著一種畸形的關(guān)系,當(dāng)二人之間的虐戀關(guān)系被揭示出來之后只會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穿裘皮的維納斯》更是走到了極致,一位男導(dǎo)演和一位女演員在排演戲劇的過程中不斷顛覆既有的權(quán)力與性別關(guān)系。在波蘭斯基的影片中,人物在不斷地走向自己的反面,突破既有的身份限制,挑戰(zhàn)人性的底線,而支撐著人物做出種種反常舉動的核心動力即為欲望。
“欲望”在波蘭斯基影片中的呈現(xiàn)從不脫離性與權(quán)力。在《水中刀》這部充滿寓言和批判色彩的影片中,“水”與“刀”的隱喻契合了欲望的本質(zhì),它包裹在溫和柔情的外殼之下,內(nèi)里卻是鋒利冷酷的。一對中產(chǎn)階級夫婦和一個青年學(xué)生之間存在著身份、階級等多種差別,他們原本在各自的世界中以不同的社會身份生活著,但這次旅程卻在撬動他們原本穩(wěn)固的根基。中年夫妻雖生活優(yōu)渥卻感情淡漠,丈夫因身份、地位的優(yōu)越感而凌駕于青年之上,對他的態(tài)度十分強硬,青年只能極力維護自己的尊嚴(yán)。當(dāng)他們上船之后,丈夫與青年之間的爭吵和沖突實際上是男人之間的權(quán)力之爭,這一權(quán)力之爭內(nèi)在隱含著性的爭奪,因為妻子終于找到了一個突破口來反抗丈夫,在兩個男人的爭斗之間她選擇偏袒青年。當(dāng)青年窺探到船艙中妻子裸露的背時這種性吸引力更加強烈了,丈夫的察覺令二人之間的角力真正轉(zhuǎn)到了性的層面上。
影片中真正的沖突爆發(fā)在丈夫?qū)⑶嗄甑牡蹲尤舆M水中,青年下水去找的時候夫妻之間爆發(fā)了爭吵,當(dāng)丈夫下水去找青年的時候青年卻回到船上吻了妻子,性的壓抑得到了釋放,青年也間接證明了自己的能力。《水中刀》的核心沖突產(chǎn)生在兩個男人之間,從社會地位的差距到性的爭奪都隱含著權(quán)力秩序,而妻子作為欲望的客體,則具有曖昧不明的含混氣息。她以女性的方式來表達(dá)對既有婚姻狀況的不滿,但這種不滿又只能通過另一個男性得到釋放。女性主體的權(quán)力表達(dá)無法得到清晰有效的彰顯,妻子只能在婚姻關(guān)系中處于從屬地位,雖然借助青年的出現(xiàn)釋放了心中壓抑的欲望,但回到岸邊之后仍舊要繼續(xù)維持和丈夫的婚姻生活,走回壓抑之中。
《水中刀》中充滿了波蘭斯基式的懷疑,但他的處理方式同時是冷靜而克制的,黑白影像的冷酷和詩意透露出隱含在陰影之下的欲望,人物之間的對抗和情緒流動具有十分豐富的層次,三角關(guān)系的形成與失衡不僅體現(xiàn)了欲望的壓抑與釋放,同時也揭示出既有社會秩序的僵化,具有很強的批判色彩。
二、欲望的錯位:身份的轉(zhuǎn)換
波蘭斯基在《水中刀》里對既有的權(quán)力秩序提出了懷疑,欲望的壓抑與釋放挑戰(zhàn)了原有的人物關(guān)系,但人與人之間的對抗和欲望尚且處于可控的范圍之內(nèi),回歸現(xiàn)實之后的無限可能性有待觀眾自己去思考。到了《穿裘皮的維納斯》,欲望早已不止于激起一點漣漪,而是要引發(fā)一場狂風(fēng)暴雨。影片同樣將場景鎖定在一封閉空間之內(nèi),男導(dǎo)演托馬斯和前來試鏡的女演員旺達(dá)之間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和性別關(guān)系在扭結(jié)中對抗,最終實現(xiàn)了徹底的顛覆。二人之間關(guān)系的復(fù)雜性因“戲中戲”的設(shè)置而加倍,兩個人物在現(xiàn)實中和戲劇中切換身份,他們實際上承擔(dān)著四種身份,戲劇與現(xiàn)實之間的裂縫被不斷彌合,并滲透到人物身上,最終達(dá)到統(tǒng)一。觀眾可以發(fā)現(xiàn),無論現(xiàn)實如何一步步滑向戲劇,人物原有的社會身份如何逐步失效,還是虛擬的戲劇如何取代了現(xiàn)實并最終實現(xiàn)了徹底的顛覆,其核心都在于欲望的推動。
《穿裘皮的維納斯》開頭所設(shè)置的人物對立相當(dāng)明確,托馬斯作為導(dǎo)演以一位成功男性的身份主導(dǎo)影片的拍攝,而前來試鏡的女演員旺達(dá)則在狼狽不堪的狀況下請求導(dǎo)演給她試鏡的機會,在現(xiàn)實中托馬斯明顯凌駕于旺達(dá)之上。從現(xiàn)實的層面來看,旺達(dá)對于托馬斯毫無吸引力可言,但在戲劇的排演過程中旺達(dá)卻迅速激起了托馬斯的興趣。在這部戲劇中,女性與男性構(gòu)成了一種虐戀關(guān)系,女性作為施虐者是在男性的主導(dǎo)之下去施虐,實際上還是為了滿足男性的想象和受虐的需求。旺達(dá)希望顛覆這一男性主導(dǎo)之下的性別想象,她不斷引領(lǐng)托馬斯去領(lǐng)會受虐一方的心理狀態(tài),將男性隱藏的欲望全部激發(fā)出來。在影片的結(jié)尾處,托馬斯戴上了頸圈,披上了裘皮,涂上了口紅,穿上了高跟鞋,被旺達(dá)用長襪綁在了象征男性的石柱上。旺達(dá)則化身為酒神巴庫斯,在狂歡化的表演中成為精神上的主導(dǎo)力量。旺達(dá)利用自己精湛的演技和強大的控制能力顛覆了既有的性別關(guān)系與權(quán)力關(guān)系,而托馬斯則任由自己的欲望呈現(xiàn)出真實的面目,戲劇中的男性角色渴望旺達(dá)的愛,渴望一種永久性的支配,在這種欲望的驅(qū)使之下,受虐本身是一種享受,帶來無盡的快感。
然而托馬斯在任由欲望逐漸流露出來的過程中,卻沒有意識到欲望已經(jīng)從戲劇中滲透到了現(xiàn)實中,這種欲望的錯位最終為他帶來了無可挽回的后果。旺達(dá)始終知道自己什么時候在演戲,托馬斯卻在現(xiàn)實與戲劇的切換之間迷失了自己,原本他只是在戲劇中聽從旺達(dá)的指令,后來在現(xiàn)實中也無法不遵從她的意志。托馬斯妻子的電話始終提醒他外面還有一個現(xiàn)實世界,旺達(dá)則命令他告訴妻子今晚不回家了,并扔掉了他的手機徹底切斷了現(xiàn)實的羈絆。托馬斯逐漸拋棄了原有的性別構(gòu)建與權(quán)力構(gòu)建,被支配的欲望統(tǒng)攝了這個意識主體,他最終也不得不為自己放縱欲望而付出代價。
托馬斯將自己的欲望訴求錯置于現(xiàn)實之中,在戲劇中他所飾演的角色只是在性的層面上享受受虐的快感,在現(xiàn)實中他則在精神層面上將旺達(dá)視為繆斯女神而頂禮膜拜,因此他享受被支配、被奴役的生理狀態(tài)和精神狀態(tài),通過對既有身份構(gòu)建的解構(gòu)而實現(xiàn)欲望的表達(dá)。旺達(dá)準(zhǔn)確地抓住了托馬斯錯位的欲望,成功地實現(xiàn)了身份的反轉(zhuǎn),打破了原有的身份構(gòu)建,將男性虛偽的一面徹底揭露出來。波蘭斯基不斷地挖掘男性心中最隱秘的部分,呈現(xiàn)最原始的欲望,其目的仍舊是探討人性中的黑暗之處。
三、欲望的悲劇:死亡與毀滅
不可控的欲望到底會走向何方?波蘭斯基1992年的作品《苦月亮》給了我們一個極為殘酷的答案。這部影片依舊是波蘭斯基拿手的封閉空間設(shè)定,故事發(fā)生在一艘游輪上,正遭遇婚姻瓶頸期的奈杰爾和菲奧娜遇到了癱瘓的作家奧斯卡和他美艷的妻子咪咪。奈杰爾和妻子本想通過這次旅行來改善婚姻狀況,但他一遇到咪咪就被她的性感美艷所吸引,奈杰爾的欲望被奧斯卡看穿,于是他利用奈杰爾的好奇心,在壓抑的船艙中講述自己和咪咪的故事。
奧斯卡向奈杰爾講述自己與咪咪相遇、尋找到相愛的過程,毫不避諱地講述他們做愛的細(xì)節(jié),奈杰爾則無法忍受這尷尬的場面,他幾乎是在奧斯卡的強迫下繼續(xù)聽他講述這個故事。但實際上奈杰爾的內(nèi)在動力是對咪咪的欲望,他通過想象來接近自己所渴望的女性客體。于是奧斯卡得以繼續(xù)向奈杰爾講述他和咪咪之間的故事,他作為一個性冒險主義者和咪咪嘗試了各種猛烈的性愛,最終卻厭倦了她的身體,不顧她為自己墮胎的事實而拋棄她。咪咪在這場愛情中完全是受虐的一方,作為奧斯卡欲望的客體沒有任何發(fā)言權(quán)。奧斯卡沒有想到有一天他會為自己的無情付出慘痛的代價,當(dāng)他出了車禍之后咪咪在病房里將他拖下病床,導(dǎo)致他高位截癱,從此,她成了奧斯卡命運的掌控者,開始進行復(fù)仇,不斷摧毀他的自尊。奧斯卡最終吞噬了不負(fù)責(zé)任的欲望的苦果,他從施虐者轉(zhuǎn)變?yōu)槭芘暗囊环剑瓦溥渲g畸形的愛情關(guān)系讓雙方都承受著無盡的壓抑和痛苦。
奧斯卡無疑是欲望的悲劇,但即便如此,欲望本身仍讓人無法抗拒。奈杰爾聽完了奧斯卡講述的故事,認(rèn)為自己愛上了咪咪,這種可望而不可即的感情卻最能夠激起人的征服欲,正如咪咪親口所言:“愛,是你得不到我的原因。”奈杰爾沒有得到滿足的欲望卻讓他回歸了正常的婚姻之中,或許從側(cè)面證明欲望本身是一個十分危險的東西,倘若真的墜入其中便再無返回的機會了。正如奧斯卡和咪咪,他們之間的欲望太過強烈,只能在相互折磨之中渴求極致的愛情,然而愛卻永遠(yuǎn)是不圓滿的苦月亮。咪咪和菲奧娜的舞蹈與親吻令奧斯卡嫉妒,他最后開槍殺死了咪咪然后自盡。奧斯卡和咪咪都無法阻止欲望的無限膨脹,只能以毀滅的方式終結(jié)自我的貪婪。波蘭斯基用這樣一個令人感到脊背發(fā)涼的故事來探討無節(jié)制的欲望會將人帶入怎樣的深淵之中。
四、結(jié) 語
波蘭斯基影片中的欲望書寫足夠耐人尋味,欲望作為人性中的一個基本層面被置于各種極端的條件下加以探討,隔絕的封閉空間如同一個人性的試驗場,原本的社會構(gòu)建在這里都被徹底瓦解,人性的真實樣態(tài)被暴露出來。欲望是波蘭斯基影片中的人物去顛覆既有身份構(gòu)建的重要驅(qū)動力,在欲望的放大鏡之下,既有的人物關(guān)系,尤其是權(quán)力關(guān)系和性別關(guān)系都不再穩(wěn)固,因此,如何處理顯現(xiàn)出來的欲望成為關(guān)鍵。
波蘭斯基對人性的洞察無疑是十分敏銳的,他從不忌憚挖掘人性中的黑暗面,揭示出人性中被遮蔽的部分,通過敘事的不斷推進來展現(xiàn)欲望所帶來的一系列后果。或許波蘭斯基的目的從不在于引導(dǎo)觀眾壓抑自己的欲望,也不試圖在影片中融入任何說教的成分,他只是用藝術(shù)的眼光來觀察人性,將人性的真實樣態(tài)呈現(xiàn)出來,挑戰(zhàn)并顛覆觀眾已有的認(rèn)知,從而留下無盡的思考空間。
- 電影文學(xué)的其它文章
- 藝術(shù)百家
- 微電影兩部(餡餅/尋)
- 誰之過
- 浮 生 記
- 獨立電影《蛋糕》的女性形象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