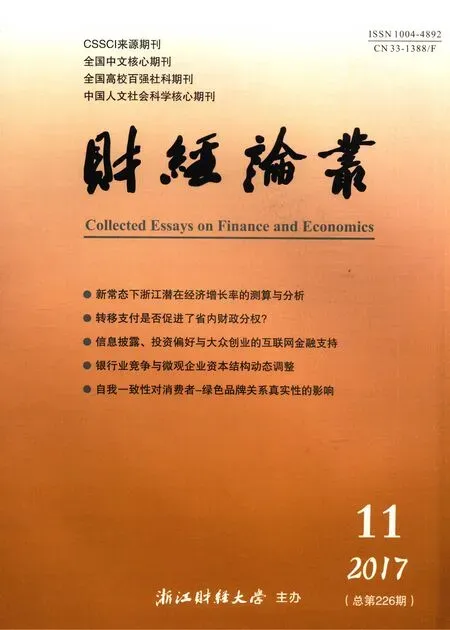新常態下浙江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測算與分析
——基于2005~2015年面板數據
俞佳根,崔日明,黃文軍
(1.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5;2.遼寧大學經濟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6;3.浙江萬里學院商學院,浙江 寧波 315100)
新常態下浙江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測算與分析
——基于2005~2015年面板數據
俞佳根1,崔日明2,黃文軍3
(1.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5;2.遼寧大學經濟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6;3.浙江萬里學院商學院,浙江 寧波 315100)
本文以2005~2015年浙江省市域面板數據為樣本,依據勞動增強型的結構時變彈性模型,測算浙江潛在的經濟增長率。研究結果發現,浙江人力資本產出彈性明顯低于資本存量和勞動力產出彈性,三者變化的幅度不明顯;浙江東北部地區的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產出彈性高于西南部地區,西南部地區的資本存量產出彈性日漸高于東北部地區;浙江實際經濟增長率總體呈現波動下滑態勢,增速變動不僅受潛在經濟增速變動等內在因素影響,也受需求管理等外在因素影響。最后,從教育體制改革、需求管理優化和區域發展協同等方面提出相關的政策啟示。
新常態;潛在經濟增長率;浙江
在歷經30多年的高速增長后,中國經濟已進入以“增速放緩、結構優化、動力多元”為主要特點的新常態。特別是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2016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已降至6.7%,與2007年金融危機前的14.2%相比下降超過一半。可見,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不容忽視。放眼全國、聚焦浙江,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排頭兵,浙江省委、省政府在歷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始終把穩定經濟增長、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作為全局工作的重點任務來抓。但不可否認的是,邁入新常態的浙江經濟也呈現增長速度放緩的跡象。去除價格因素,浙江實際經濟增長率從2006年開始圍繞在10%~14%間上下波動,但從2009年開始浙江實際經濟增速迅速下降至8%附近。近年來,浙江經濟增速穩定在7.5%左右,仍然呈現進一步下滑趨勢。
潛在經濟增長率與實際經濟增長率關系密切。那么,新常態下的浙江經濟進入低速增長通道,這一現象是否與浙江潛在經濟增長率的變動有關?浙江不同地區經濟增長潛力又有何差異?在新舊動能轉換的背景下,如何探尋浙江經濟穩定增長的新動力?面臨經濟下行壓力,浙江又該如何積極應對?可見,正確認識和全面把握新常態下浙江經濟增速放緩的本質特征,積極尋找新的增長空間,探索如何以更高質量、更好效益、更穩發展適應當前浙江經濟增速變化,已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一、相關文獻綜述
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研究,相關學者主要圍繞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內涵、測算方法等方面展開[1][2][3][4][5][6][7][8][9],研究內容較為豐富,為后續研究打下了較為扎實的基礎,對本文也具有較好的借鑒意義。但相關研究主要基于國家宏觀層面展開,較少從省域視角展開針對性探討,忽視了潛在經濟增長率與實際經濟增長率之間的動態關系。
在浙江潛在經濟增長率研究方面,盛世豪和杜平(2015)將研究視角聚焦于勞動生產率,認為浙江經濟發展主要歸結于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且勞動生產率與潛在經濟增長存在密切關聯[10]。章麗盛(2015)基于勞動增強型生產函數法估算了1978~2013年浙江全要素生產率,指出近年來浙江潛在經濟增長率逐年下降,經濟增速可能出現逐年放緩的發展態勢[11]。中國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課題組(2013)運用HP濾波法計算了1962~2012年浙江潛在經濟增長率,認為浙江經濟增速下滑主要是由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所致[12]。浙江省經濟信息中心課題組(2013)研究發現1979~2011年浙江實際經濟增速圍繞潛在經濟增長率上下波動,由于人口紅利逐步消失、資源和全球化紅利不斷枯竭等原因,浙江潛在經濟增速不斷下降[13]。此外,曹龍(2007)、韓蓓(2009)、謝戟等(2014)和曹正(2015)就安徽、北京、武漢和杭州等地潛在經濟增長率與經濟發展關系做了相關研究[14][15][16][17]。
綜上,潛在經濟增長率相關研究主要基于國家宏觀層面展開,諸多學者在研究潛在經濟增長率時大多采用局限于某一時期彈性固定的各類模型,因而得出的生產彈性為該時期的平均值,忽視了相關生產要素產出彈性的動態變化過程。本文以浙江為研究對象,深入分析近年來浙江潛在經濟増長率與實際經濟增長率的動態發展軌跡,在此基礎上嘗試分析浙江實際經濟增速趨緩的深層次原因。此外,浙江經濟的個案研究對促進與浙江省情相似的國內其他省市經濟發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二、模型構建與數據來源
(一)模型構建
鑒于生產函數法對模型相關數據的要求相對簡單且容易獲取,在具體測算潛在經濟增長率中被廣泛運用,本文借鑒郭晗和任保平(2014)相關研究方法,結合浙江實際,進一步拓展C-D生產函數,建立如下的勞動增強型的結構時變彈性模型[18]:
(1)
其中,αit、kit分別表示某區域內時間t內第i產業的資本產出彈性和資本存量比重,βit、lit分別表示該區域時間t內第j產業的勞動產出彈性和勞動力比重,λit、hit則分別表示該區域時間t內q類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和所占比重。將模型(1)兩邊分別取對數,則可得到勞動增強型的結構時變彈性模型(2):
(2)
此外,由于在生產總量和生產效率度量過程中存在隨機因素,模型(2)可能存在一定的效率損失,而隨機前沿模型(SFA)能有效避免測量誤差造成的隨機性誤差[19],因此本文進一步采用面板SFA模型來具體測算浙江各地區潛在產出。
(二)數據來源
由于《浙江統計年鑒》及各地級市相應年鑒中對浙江省分地區分產業固定資產投資的完整數據僅公布到2005年,且2004年以前浙江絕大部分地區的分產業固定資產投資數據嚴重缺失,考慮到數據的連貫性和一致性,為確保研究結果的準確性,本文選取2005~2015年浙江省11個地級市面板數據,采用Stata12.0作為計量分析工具對模型數據進行分析和檢驗處理。相關指標的數據來源和處理方法如下:
1.實際產出Y。《浙江統計年鑒》中的GDP數據為名義GDP,需根據GDP平減指數調整為實際GDP。首先將公布的浙江GDP平減指數(1978=100)調整為以2005年為基期的GDP平減指數(2005=100),據此測算出浙江各地區2005~2015年的實際GDP。
2.技術水平A。一般而言,代表某一地區的技術水平指標比較多(如技術市場成交額、R&D經費投入和專利授權量等)。鑒于《浙江統計年鑒》中各市縣國民經濟主要指標中包含專利的相關情況,故本文選取專利授權量這一指標來反映浙江各地區的技術水平。
3.資本存量K。本文選擇學者們普遍使用的永續盤存法來估算浙江各地區三產的實際資本存量。這種方法的關鍵在于分別確定浙江各地區三產的初始存量和資本折舊率。參考Hall和Jones(1999)的方法計算初始資本存量[20],借鑒郭晗和任保平(2014)、張軍(2004)等研究成果將資本折舊率統一設定為9.6%[21]。此外,通過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將浙江各地區歷年固定資產投資額折算成以2005年為基期的不變價格。
4.資本存量結構αit。根據估算的浙江各地區三產的資本存量,分別測算不同時期浙江各地區三產的資本投入結構比重k1、k2和k3。
關節電機的反饋信號最大為0.083 7 V,那么增益大小為3.3V/0.0837V=39.427,將增益取整G=39則RG=49.4kΩ/(39-1)=1.3kΩ。所以關節電機反饋信號的增益倍數為39,外部增益設置電阻RG=1.3kΩ。
5.勞動力投入L和勞動力結構lit。選取浙江各地區全社會就業人員數作為代表變量,同時測算不同時期浙江各地區三產的勞動力投入比重l1、l2和l3。
6.人力資本存量H和人力資本結構hit。勞動力素質高低決定著社會產出總量和效率,因此選用全社會就業人口素質結構作為變量具有較好的代表性。鑒于浙江僅在省級層面公布了每萬人口中在校學生數及其構成情況,缺乏地市級層面的統計口徑,故本文選取各類學校在校學生數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替代變量,以每10萬人口中高等學校、中等職業學校、普通中學(含高中和初中)及小學在校學生數占總人口比值分別計算浙江各地區不同時期人力資本結構h1、h2、h3和h4。最后,以各地區各類學校在校學生數占總人口比值為權重,將總人口中高等學校、中等職業學校、普通中學及小學的教育年限分別賦值為16、12、10.5和6年,加權計算浙江各地區不同時期就業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三、模型分析與實證檢驗結果
(一)模型總體分析
本文采用F檢驗方法檢驗面板數據的混合效應和固定效應,BP檢驗方法檢驗面板數據的隨機效應和混合效應,Hausman檢驗方法檢驗面板數據的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經檢驗后最終選擇固定效應模型(FE)對模型(2)進行研究分析。同時,采用Wooldridge檢驗、Pesaran檢驗和修正的Wald檢驗方法,分別檢驗模型(2)存在序列相關性、截面相關性及截面異方差性問題。為消除面板統計結果中的序列相關性、截面相關性及截面異方差性,本文分別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Driscoll和Kraay(1998)提出的非參數協方差矩陣估計方法(DK)予以修正(如表1所示)。
從回歸結果看,固定效應模型經非參數協方差矩陣估計方法修正后,模型各變量系數雖沒有發生變化,但模型R2達到0.988。除h2lnH和h3lnH外,各變量系數符號均符合預期,資本和勞動力指標相關系數較為顯著。與此同時,采用面板SFA模型各變量系數和顯著性與修正后的固定效應模型結果相似,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修正后固定效應模型的穩健性。因此,下文分別以修正后的固定效應模型和面板SFA模型進行具體分析。
從修正后的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來看,技術水平對實際產出存在正向影響,但其影響相對較小。在資本存量結構因素中,第一、二、三產業的資本產出彈性依次下降,而在勞動力投入結構因素中,第一、二、三產業的勞動產出彈性依次上升。技術水平、資本存量和勞動力投入變量系數顯著為正,人力資本存量結構中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對實際產出存在正向作用,而中等教育(包括中等職業教育和普通中學)對實際產出存在負向作用。得出這一結論的原因可能與浙江教育資源分布不均勻有關:浙江中等教育資源分布比較均勻,而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資源則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

表1 模型具體回歸結果(N=121)
注:***、**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括號內為t值。
(二)浙江各要素產出彈性分析

圖1 2005~2015年浙江各要素產出彈性
根據修正后的固定效應模型及面板SFA模型回歸結果,將資本存量、勞動力和人力資本存量的相關產出彈性系數與不同時期各要素比重相乘,可得到2005~2015年浙江各地區各要素的產出彈性變動情況。在此基礎上,將浙江11個地區按地理分布劃分為東北(NE)和西南(SW)兩個區域,據此計算浙江東北和西南區域各要素的產出彈性(如表2所示)。同時,將不同時期浙江各地區各要素匯總重新計算相關要素的比重,再乘以相關要素的產出彈性系數,可得到2005~2015年浙江各地區資本存量、勞動力和人力資本存量的產出彈性變動情況。
由圖1可知,浙江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呈現逐年上升趨勢,而資本存量的產出彈性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但三者的變動幅度不明顯。浙江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低于資本存量和勞動力的產出彈性,主要原因可能是浙江人力資本內部結構包含四個不同層次,與資本存量和勞動力的產業結構相比差異較大。固定效應模型的資本存量、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分別高于SFA模型相應的產出彈性。

表2 2005~2015年浙江省東北和西南區域各要素產出彈性*根據地理劃分,浙東北區域包括杭州、寧波、嘉興、湖州、紹興和舟山6個地級市,浙西南區域包括溫州、金華、衢州、臺州和麗水5個地級市。
由表2可知,分區域看,在固定效應模型下,2005~2009年浙江省東北區域的資本存量產出彈性高于西南區域,而2010~2015年浙江省西南區域的資本存量產出彈性則高于東北區域;在面板SFA模型下,2005~2007年浙江省東北區域的資本存量產出彈性高于西南區域,而2008~2015年浙江省西南區域的資本存量產出彈性則高于東北區域。可見,隨著內部結構的不斷完善,浙江省西南區域的資本存量產出彈性逐漸高于東北區域。2005~2015年浙江省東北區域的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高于西南區域。除資本存量的產出彈性外,浙江省東北和西南區域的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呈現逐年上升趨勢,這與浙江省的總體變動趨勢相一致。
(三)浙江各要素增長水平分析

圖2 2006~2015年浙江各要素增長率
根據浙江各地區不同時期各要素的產出彈性和相應比重,通過匯總求和,分別計算2005~2015年浙江各要素存量及其變動情況(如圖2所示)。
由圖2可知,2006~2015年浙江省的資本存量呈現波動式上升,增長水平維持在13%~20%之間。勞動力和人力資本存量的增長率呈迂回下降態勢,勞動力增長水平維持在5%以下,人力資本存量則呈現不斷下降趨勢。浙江省的勞動力和人力資本存量增長水平的下降可能與近年來浙江省人口的增長率和出生率下降有關。鑒于浙江各要素產出彈性之間差距遠小于各要素增長水平,因此可基本確定資本因素是近年來浙江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動力。
(四)浙江潛在經濟增長率總體分析
根據固定效應模型和面板SFA模型回歸結果,分別計算浙江省11個地級市的潛在產出。在此基礎上,通過累加得到2005~2015年浙江省潛在產出,據此計算2006~2015年浙江潛在經濟增長率。通過計算浙江省名義經濟增長率和實際經濟增長率,得到2006~2015年浙江經濟增長率變動情況(如圖3所示)。

圖3 2006~2015年浙江經濟增長率
由圖3可知,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和面板SFA模型得到的浙江潛在經濟增長率差異不明顯,且呈現相同的變動規律,這也從另一個層面說明本文模型結果的準確性和穩健性。浙江省名義經濟增長率和實際經濟增長率總體呈現相似的波動發展態勢。2006~2009年,浙江名義經濟增長率和實際經濟增長率雙雙下滑并降至最低點,而從2010年開始,浙江名義經濟增長率和實際經濟增長率迅速回升,在2010年達到最高點。隨后,浙江名義經濟增長率和實際經濟增長率又呈現下滑態勢,且后半階段的下滑態勢有所減緩(特別是浙江實際經濟增長率逐漸趨于穩定)。2006~2011年,浙江實際經濟增長率和潛在經濟增長率呈現相似的變動規律,實際經濟增速變動滯后于潛在經濟增速變動趨勢,表明這一階段浙江實際經濟增速變動主要取決于潛在經濟增速變動。換言之,2006~2011年浙江實際經濟增長率變動主要由潛在經濟增長率變動導致。2012~2015年,浙江實際經濟增長率變動與潛在經濟增長率變動基本呈現相反的發展方向,說明這一階段浙江實際經濟增長率變動不僅受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內在影響,還受需求管理等外在因素的影響。這意味著此階段如果采取擴張性需求政策的外部刺激,可使浙江實際經濟增長擺脫潛在經濟增長的內在約束,從而實現浙江經濟的穩定增長。
(五)浙江潛在經濟增長率區域分析
根據相關回歸結果,在分別計算浙江省11個地級市的潛在產出的基礎上,按照地理劃分,分別匯總計算得到2005~2015年浙江省東北和西南區域的潛在產出,據此計算浙江省各地區的潛在經濟增長率。通過計算浙江省東北和西南區域的名義經濟增長率和實際經濟增長率,得到2006~2015年浙江省東北和西南區域的經濟增長率變動情況(如圖4所示)。

圖4 2006~2015年浙江省東北和西南區域的經濟增長率
由圖4可知,除2013年外,2006~2015年浙江省東北區域的實際經濟增長率高于西南,且東北和西南區域的實際經濟增長率總體呈現相似的波動下滑發展態勢。以2009年為分界點,浙江省東北和西南區域的實際經濟增速表現與浙江省的總體實際經濟增速相似。由固定效應模型和面板SFA模型得到的浙江省東北和西南區域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差異仍然不大,且呈現相同的變動規律,進一步說明本文模型結果的準確性和穩健性。此外,以2010年為分界點,2010年以前浙江省東北區域的潛在經濟增長率高于西南,2010年以后浙江省東北區域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則低于西南。分區域看,2006~2015年浙江省西南區域的實際經濟增長率與所在地區相應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仍與浙江省的總體經濟呈現相似的變動規律。2006~2011年,浙江省西南區域的實際經濟增長率的變動情況滯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而2012~2015年該地區的實際經濟增長率的變動情況則與潛在經濟增長率呈現相反的變動趨勢,在此階段的浙江省東南區域的實際經濟增速則仍呈現滯后于潛在經濟增速的變動趨勢。
四、相關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依據勞動增強型的結構時變彈性模型,應用2005~2015年浙江省11個地級市的相關面板數據,具體測算2006~2015年浙江省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并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總體而言,近十年來浙江省的資本存量、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變化不大,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略微上升,而資本存量的產出彈性則略微下降,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明顯低于資本存量和勞動力的產出彈性。這表明當前過度依賴投資驅動的浙江經濟亟需轉變增長方式,在優化投資結構、注重投資質量和效益的同時,應充分發揮人力資本在提升經濟增長中的直接效用,未來浙江經濟的增長驅動更多地要依靠人力資本升級。因此,應繼續深化教育體制改革,注重教育投入與產出,培養高端科技人才,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提升勞動者職業素養,增強人力資本積累,充分挖掘未來浙江經濟新的增長潛力。
第二,分區域看,近十年來浙江省東北區域的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高于西南,而浙江省西南區域的資本存量的產出彈性則呈現逐漸高于東北的發展態勢。因此,在建設浙江經濟強省中應注重區域協同發展,充分考慮區域差異,在鞏固東北區域先發優勢的同時,通過政策引導,加大投入,充分發揮浙江省西南區域的勞動和人力資本的產出效益提升等后發優勢,促進浙江經濟協調、平穩發展。
第三,綜合來看,近十年來浙江實際經濟增速變動主要受潛在經濟增速變動等內在因素和需求管理等外在因素的共同影響。浙江實際經濟增長率總體呈現波動下滑發展態勢,近年來則逐漸趨于穩定。在早期,浙江實際經濟增速變動主要由潛在經濟增速變動導致,而在后半期,浙江實際經濟增速變動主要受需求管理等外部因素的影響較多。可見,浙江在優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需注重需求側的有效提升,打好二者的組合拳。在各項政策制定、實施過程中,注重體制機制創新,強化需求管理,優化需求結構,通過適度、有效的政策刺激,擴大有效需求,促進浙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1] Samuelson P. A. and Solow R. Analytical Aspects of Anti-inflationary Polic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0, (l): 177-94.
[2] 羅來軍,王永蘇.新型城鎮化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河南省為例[J]. 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6): 73-76.
[3] 楊旭,李奠,王哲吳.對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測算——基于二元結構奧肯定律的實證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10):14-23.
[4] Cerra V. and Saxena S. C. Alternative Methods of Estimating Potential Output and the Output Gap: An Application to Sweden[Z]. IMF Working Paper, 2000, (3).
[5] Camba-Mend G.and Rodriguez-Palenzuela D. Assessment Criteria for Output Gap Estimates[J].Economic Modelling,2003,(3):529-562.
[6] 謝太峰,王子博.中國經濟周期拐點預測——基于潛在經濟增長率與經驗判斷[J].國際金融研究,2013, (1):77-86.
[7] 郭豫媚,陳彥斌.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估算及其政策含義:1979-2020[J].經濟學動態,2015,(2):12-18.
[8] 黃森.交通基礎設施空間建設差異化影響了中國經濟增長嗎——基于2001-2011年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數據的實證分析[J].貴州財經大學學報,2015,(3):9-20.
[9] 劉雅君,田依民.中國經濟波動率對潛在經濟增長率影響的實證分析[J].經濟學家,2016,(8):46-54.
[10] 盛世豪,杜平.從勞動生產率看浙江經濟增長——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一個視角[J].浙江經濟,2015,(5):30-33.
[11] 章麗盛.對浙江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幾點認識[J].浙江金融,2015,(1):64-69.
[12] 中國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課題組.浙江經濟增長周期、動力及趨勢[J].浙江金融,2013,(7):16-20.
[13] 浙江省經濟信息中心課題組.浙江經濟增長潛力及趨勢展望[J].浙江經濟,2013,(10):31-33.
[14] 曹龍.安徽省經濟潛在增長率的分析與測算研究[J].統計與決策,2007,(1):101-103.
[15] 韓蓓.北京市潛在經濟增長率測算與HP濾波平滑參數探討[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09,(2):139-146.
[16] 謝戟,游天屹,胡動剛.關于武漢市潛在經濟產出的研究[J].統計與決策,2014,(7):143-145.
[17] 曹正.杭州市“十一五”經濟潛在增長率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2005,(5):9-13.
[18] 郭晗,任保平.結構變動、要素產出彈性與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4,(12):72-84.
[19] 邊文龍,王向楠.面板數據隨機前沿分析的研究綜述[J].統計研究,2016,(6):13-20.
[20] Hall R. and Jones C.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2): 83-115.
[21] 張軍,吳桂英,張吉鵬.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經濟研究,2004,(10):35-44.
ResearchontheCalculationandAnalysisofZhejiangProvince’sPotentialEconomicGrowthRateintheNewNormal——BasedonthePanelDatafrom2005to2015
YU Jiagen1, CUI Riming2, HUANG Wenjun3
(1.Business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Hangzhou 310015, 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3.School of Business,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Ningbo 315100, China)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15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potential economic growth rate of Zhejiang Province in detail according to the time varying elastic model of the structure of labor enhancement. It is found that Zhejiang's human capital output elasticity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apital stock and labor, and the output elasticity which varies among them h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labor and human capital in the northeast of Zhejiang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outhwest. However,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capital stock in the southwest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theast. In recent years, Zhejiang’s real economic growth rate shows a trend of fluctuating slowdown. It is not only affected by the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potential economic growth rate changes, but also by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demand management.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ome related policy implications in aspects of educational system reform, demand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New Normal; Potential Economic Growth; Zhejiang Province
2017-02-05
浙江省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LY17G030001);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7CJL008);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5ZDA056);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14AZD017)
俞佳根(1982-),男,浙江富陽人,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商學院講師,博士;崔日明(1963-),男,內蒙古赤峰人,遼寧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黃文軍(1979-),男,山西忻洲人,浙江萬里學院商學院副教授,博士。
F015
A
1004-4892(2017)11-0003-08
(責任編輯:化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