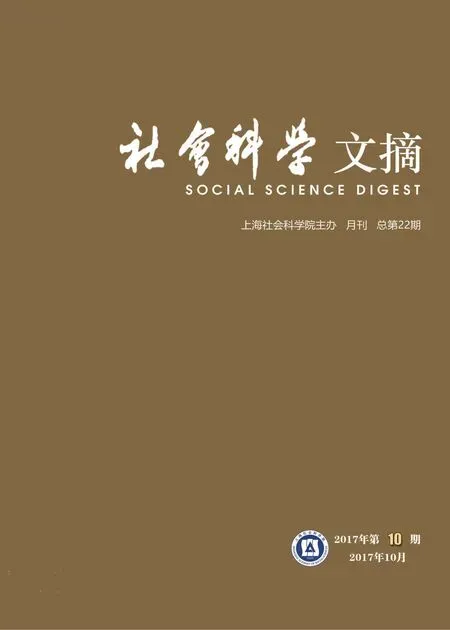石黑一雄小說中的懷舊與身份認同
文/魏文
石黑一雄小說中的懷舊與身份認同
文/魏文
引言
在英國作家石黑一雄的長篇小說作品中,懷舊始終是一個重要的議題。石黑一雄的主人公大多是在現代社會中被邊緣化的“無家可歸者”,面臨著由現代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動蕩所造成的身份危機或存在焦慮感。身處困境的主人公往往訴諸于懷舊,力圖通過對往事的懷想和對曾經短暫存在過的那個“家園”的回憶,從而重新認識自我,穩(wěn)固并重申自我身份。
然而在其不同的作品中,小說家對自我身份的強調卻有著不同的側重點。例如《長日留痕》的主人公史蒂文斯試圖建構一個單一、靜止、排外的身份,這個身份有兩個核心要點:尊嚴和英國性。然而他的懷舊敘事卻充分暴露了這種身份模式的內在悖謬性。小說敘事實際上解構了他所信仰的“尊嚴”和“英國性”,從而徹底否定了那種一層不變的固定身份認同模式的合法性。不同的是,在另一部小說《群山淡景》中,敘事者悅子通過自反性、反諷式的敘事,重構自我身份。這種身份實則是一個永遠在被言說、被建構的過程,一個永在進行中的敘事話語實踐;它永不完結,也沒有排他性,而是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
現代社會中的懷舊與個體身份
懷舊的英文“nostalgia”來自兩個希臘語詞根:“nostos”意為“返鄉(xiāng)”,“algia”意指“懷想”。因此懷舊的大意是指對往日家園或往昔時光的懷想。作為一種心理活動和情感體驗,懷舊是古往今來普遍存在于人類生活中的社會現象。傳統社會中人類通過祭祀活動所表達的對先祖的崇拜可以看成是一種懷舊;當今社會中諸如黑白照片、復古音樂、歷史題材影視劇等大眾文化產品所引起人們對往昔歲月的回憶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懷舊。因此可以說,懷舊是無時不在和無處不在的。
而在現代性語境下,人類的懷舊則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可以說,懷舊是現代個體維持自我身份穩(wěn)定和統一的重要方式。在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看來,現代人普遍面臨著“本體安全感的缺失”以及“存在的焦慮”這兩大問題。對于處于紛繁復雜的社會變遷中的現代個體來講,若要維持自我身份穩(wěn)定、緩解“存在的焦慮”,就需要回溯過去,通過從傳統與往事中尋找確定性,從而為生活在當下變化中的自我樹立信心和安全感。在這個意義上,懷舊為個體探尋自我之源、維持自我意識的統一提供了可行的途徑。為了應對現實情境中所面臨的身份認同危機和存在焦慮感,主體通過回溯過去,挖掘存在于往事中的個體形象和生存經驗,從而為當下的自我提供應對困境所需要的信心和確認感,從而避免處于不斷變遷的現代社會中的自我被分裂、被異化的命運。總之,懷舊就是個體在當下的混亂中用來不斷建構、維護和重構自我身份重要方式。
與此同時,美國俄裔學者斯維特蘭娜·博伊姆將懷舊現象劃分為兩大類:復原性懷舊與反思性懷舊。復原性的懷舊者往往不承認懷舊敘述中的虛構成分。他們在某個主導性的意識形態(tài)力量的驅動之下,通過有選擇性地恢復某些傳統、重構一個神話式的本源,從而試圖為當下的世界樹立某種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因此,復原性懷舊的個體總是試圖通過構建一段共同的歷史,回溯一個穩(wěn)定不變的起源,從而為集體中的所有個體確立一個本質主義的、單一化的身份。與此相反,反思性的懷舊所關注的并非某個存在于過去的絕對真理,而是對歷史和時間的思考。此類懷舊并不企圖重建某個神話般的家園,而是借助關于過去的敘事探索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關系。因此,反思性懷舊者所重申的身份也不可能是一種固定僵化的實體,而是一個變動不居的身份認同的過程。
懷舊同樣是石黑一雄所關注的一個重要議題。他的所有長篇小說均探討了記憶、懷舊等話題。此外,除了《被埋葬的巨人》之外,其余六部小說的情節(jié)皆是以主人公對過去經歷的懷舊敘事為基礎而展開。因此,本文以《長日留痕》和《群山淡景》為例,探討石黑一雄對懷舊與個體身份認同之間的關系。
復原性懷舊與英國性的悖論
《長日留痕》是石黑一雄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出版于1989年。小說的敘事者史蒂文斯是一個“典型的”英式老管家,他所工作的地點也是一棟“典型的”英國鄉(xiāng)間府邸——達靈頓府。小說的故事始于1956年,此時的達靈頓府如同大英帝國一樣,早已失去昔日的輝煌。“二戰(zhàn)”后英國社會經歷的劇烈變化使得史蒂文斯這位遲暮之年的老管家對現實倍感困惑。隨著自己效忠多年的主人達靈頓勛爵的離世,史蒂文斯和達靈頓府一起被打包售給美國富商法拉戴先生。對現狀的失望迫使史蒂文斯只能訴諸于懷舊,借舊日的榮光慰藉當下的苦難。個人身份的困惑讓他回望過去,企圖通過回歸本真的起源、恢復現已遺失的某種絕對真理并將其作為最高價值和道德的判斷標準,最終構建一個封閉且排他的、個人和集體高度一致的英國民族身份,或英國性(Englishness)。
按照博伊姆的定義,史蒂文斯的懷舊屬于“復原性”的。博伊姆認為,“復原性懷舊體現于對過去紀念碑的完美重構”以及“對傳統和習俗的重新發(fā)明和復原”。而史蒂文斯企圖重建的“紀念碑”便是曾經的達靈頓府以及與之緊密相連的傳統價值和道德標準。此外,達靈頓府還是史蒂文斯理想中的那種英國民族身份的基石。在他的懷舊敘事中,作為民族身份的英國性由三個基本方面構成:達靈頓府、紳士階層以及男管家。這三者共同蘊涵的傳統價值和道德標準被史蒂文斯總結為“偉大”和“尊嚴”。
在史蒂文斯看來,達靈頓府即是英國的象征。他驕傲地告訴自己的美國雇主法拉戴先生:“這些年來我十分榮幸,能夠欣賞英國最美的風景,就在這四周的高墻之內。”實際上,在英國文學傳統中,鄉(xiāng)間莊園通常被認為是定義英國性的最佳地點,因為其建筑結構象征著嚴密而整齊的社會結構,其經久不衰的歷時性則暗示著“民族身份連續(xù)性的幻象”。他們作為一種關于英國民族身份的懷舊話語,讓過去重新顯現于當前,同時也讓現在能夠重新創(chuàng)構過去。正因如此,史蒂文斯才試圖從往日歲月中尋找到達靈頓府所體現的價值和理想,從而復原某個已逝的民族身份。除此之外,如果說莊園府邸是英國民族身份的物理表征,那么居于其中的紳士以及男管家則承載著關于該身份的價值取向和道德標準:偉大的英國紳士階層是人類文明進步之重任的承擔者;而男管家之偉大則體現于他們?yōu)閭ゴ蟮募澥糠眨瑥亩簿褪菫槿祟愔l矶铡4送猓@兩者又與“英國”這一概念融為一體、密不可分。在史蒂文斯看來,“只有英國才有真正的男管家......一個偉大的男管家,根據定義,一定是一個英國人”。
不幸的是,史蒂文斯并未意識到,他試圖重構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卻被自己的懷舊敘事所顛覆和解構。他的復原性懷舊敘事非但沒有重構一個理想化的英國身份,反而暴露了這種身份神話的在內悖謬性:這種單一化、排他性的本質主義英國民族身份只不過是一個自身充滿悖論的幻象。
首先,達靈頓府早已淪為某種文化商品,無法表征具有本真起源的民族傳統。在小說中,美國人法拉戴買下達靈頓府后,曾邀請友人韋克菲爾德夫婦前來做客。這對夫婦詢問史蒂文斯:“這個拱門看起來像十七世紀的。它不會是最近才仿造的吧?”他們最終得出結論:“我覺得是仿造的。技術很好,但依然是仿造的”。而法拉戴先生也曾以相同的方式質詢史蒂文斯:“你是正宗的老式英國管家,而不是一個假裝管家的服務員。你是真的東西,對吧?”這一情節(jié)的反諷意義在于,當史蒂文斯把達靈頓府視為表征民族身份的神話而與之認同時,美國人法拉戴卻把這種神話作為一種文化資本的形式將其挪用。在英國文學傳統中,莊園府邸之所以被認為是英國民族身份的象征,是緣于其物理結構的完整性表征著社會的高度統一性;然而在《長日留痕》中,作為文化商品的達靈頓府卻因為本身的流通性和易變性被切斷了與歷史起源的關聯。它不再通過繼承或傳承而見證歷史交替,相反,它現如今只能在資本市場進行流通和轉移。
其次,史蒂文斯所宣揚的“偉大”和“尊嚴”的本質乃是對貴族階層的愚忠和奴性。在他看來,對雇主的絕對忠誠就意味著男管家沒有必要具備獨立批判性的思維能力。以這種方式,他將道德價值判斷的責任讓渡給諸如達靈頓勛爵這樣的紳士。換言之,高貴的紳士們不僅是英國民族身份的象征,同時還是知識和道德方面的權威專家,以及國家命運的裁決者。具有諷刺性的是,達靈頓勛爵對“二戰(zhàn)”前的政治時局作出了錯誤判斷,支持對納粹德國的綏靖政策,最終將英國推向了戰(zhàn)爭的深淵。此外,為了討好來訪的納粹特使,達靈頓勛爵要求史蒂文斯解雇府邸里兩名猶太女傭,盡管她們“一直都是非常令人滿意的員工”。為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顧公平、正義等道德原則,這說明達靈頓勛爵根本算不上是一位謙謙君子。
可見,晚年的史蒂文斯試圖在對往事的懷舊中尋找并復原一個穩(wěn)定不變的個體身份和民族身份,并重新發(fā)明與此身份相關聯的傳統價值和道德標準,從而應對當前所面臨的身份危機。然而他的懷舊敘事卻反諷式地顛覆和解構了自己試圖重建的價值觀和傳統。他所引以為豪的“尊嚴”只不過是對貴族統治階級的盲從;而他所試圖證明的關于英國民族身份的“偉大”實際上是一個極其空泛的概念。
反思性懷舊與身份重構
與史蒂文斯的復原性懷舊不同,《群山淡景》中的敘事者悅子的懷舊則是反思性的。小說的敘事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敘事者悅子是一位寡居英國的日本女性。一方面,她由于大女兒景子的自殺而感到愧疚和痛苦;另一方面,作為一名亞裔移民,她還是文化偏見的受害者。有研究者指出,“錯位(displacement)”是小說的重要主題。而英文里,“displacement”還有“驅逐、離家”之意。因此,悅子的遭遇不僅是各種層面的錯位,更是遠離精神家園的放逐。被流放至社會邊緣的她,只有借助于對往昔歲月的回顧與懷想,才能夠找到認清現狀、化解危機的可行方案;也只有求助于懷舊,她才能想象性地重構已經喪失的自我身份。
然而,悅子并沒有試圖去恢復記憶中那個虛幻而美好的家園,因為她深知自己曾經生活過的故土日本長崎早已被戰(zhàn)爭摧毀;她也沒有企圖通過回憶的想象去建構某種排他性的民族身份神話,因為在她看來,東方和西方“有著如此多的共同點”。簡而言之,她關于過去的敘述是“諷喻性的、碎片化的、非終結的”。反思性的懷舊使得悅子能夠想象性地重構一種并非固定僵化,而是處于動態(tài)建構中的身份;或者說,悅子的懷舊是一個始終處于進行之中的、關于自我身份的敘事過程。這種敘事具有以下兩大特點:
悅子的懷舊敘事摘除了父權思想為女性貼上的柔弱、溫順的標簽,并逆轉了“男性/女性”二元對立中不對稱的權力關系。在對往事的敘述中,悅子巧妙地借用另一位母親幸子的故事,顛覆了“男性作為欲望主體,女性作為幻想客體”的性別神話。根據悅子的描述,幸子是她在長崎生活時所結識的友人,一位叛逆、獨立、勇敢的女性。讀者不難發(fā)現,悅子和幸子很有可能就是同一個人。例如,兩人均有一段不幸的婚姻以及一個性情孤僻的女兒;幸子一直希望美國大兵弗蘭克將自己帶到美國,而悅子則是同英國記者謝林漢姆結婚并移民英國。此外,當悅子勸說幸子的女兒真理子跟隨她母親幸子移民去美國的時候,她誤將“你們”說成了“我們”——“如果你(真理子)不喜歡那里的話,我們可以隨時回來”。也就是說,悅子似乎并不是在對別人的女兒講話,而是在向自己的女兒景子作出承諾:如果你不喜歡那里(英國),我們可以隨時回來。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幸子的經歷填補了悅子關于自己的敘事中的空白,還原了被省略的信息,并揭示了被敘事者刻意隱藏的秘密。從這個角度來看,上述幸子堅強獨立、敢于挑戰(zhàn)傳統道德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敘事者悅子本人的所作所為。她的懷舊敘事假借她人之口顛覆了性別神話。悅子實際上將自己對命運的不屈抗爭“投射”到幸子之上。在這兩位女性難分彼此的故事之中,男性(悅子的英國丈夫謝林漢姆以及幸子的美國男友弗蘭克)不再扮演拯救者的角色,而是淪為女性為達成目標所借助的手段。被凝視的客體(女性)逆轉成為能動的主體,而欲望的主體(男性)則成為了女性為達成目標所利用的工具。
除此之外,悅子非線性的懷舊敘事所呈現的內在不確定性和開放性意味著她身份的重構永不完結。在《群山淡景》中,悅子的敘述總是在“現在”與“過去”之間頻繁無規(guī)律地跳躍,這使得她的懷舊敘事呈現出非線性和碎片化的特征。而悅子和幸子兩者之間模棱兩可的關系也印證了她的敘事的內在不確定性和開放性。從接受美學的角度來看,敘事中的意義空白增加了讀者的閱讀興趣。隨著悅子碎片化的回述緩慢展開,讀者自己也經歷了伊瑟所說的“連續(xù)修正的過程”。正如作者書寫了悅子的故事那樣,讀者也通過自我的閱讀策略重新創(chuàng)造了相同的故事,建構了一個由角色和情境所組成的網絡,推動情節(jié)走向最終結局。值得注意的是,悅子關于自我的敘事永遠不會終結。在小說里,悅子的小女兒尼基告訴她,“我的一個朋友正準備寫一首關于你的詩”,并要求悅子提供“一張照片,或其它東西,關于長崎的......這樣她能夠了解所有的事情”。悅子卻不知道該給女兒什么,因為沒有什么東西能夠展示“所有的事情”。正如悅子本人的懷舊一樣,尼基的朋友所要書寫的詩歌同樣是關于悅子的敘事;同樣,如同沒有什么可以展現“所有的事情”一樣,沒有什么敘事能夠展示關于主人公的一切。個人的身份與其說是一種從過去一直持續(xù)到現在的穩(wěn)定不變的實體,還不如說是一段通過懷舊來書寫的、永未完結且需不斷修正的敘事。
結語
在回顧自己的成長歷程時,石黑一雄認為自己接受了“典型的英式教育”,但同時又否認自己“在文化意義上完全是英國人,因為(他)由日本父母撫養(yǎng)長大”。也許正是因為這種特殊經歷使意識到了自己的特殊身份,他曾聲稱自己“既不是英國的,也不是日本的”。這并不是在否定自己所繼承的文化遺產,而是對身份作出有別于傳統的闡釋。正如他在自己的作品《群山淡景》和《長日留痕》里通過主人公的懷舊敘事所證明的那樣,“身份”不可能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或者排他性的概念,也無法簡單地置于某一個單一的框架內去定義。它只能是一個開放性的動態(tài)概念,永不完結,一直在修正。
(作者系北京林業(yè)大學外語學院講師;摘自《外國語文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