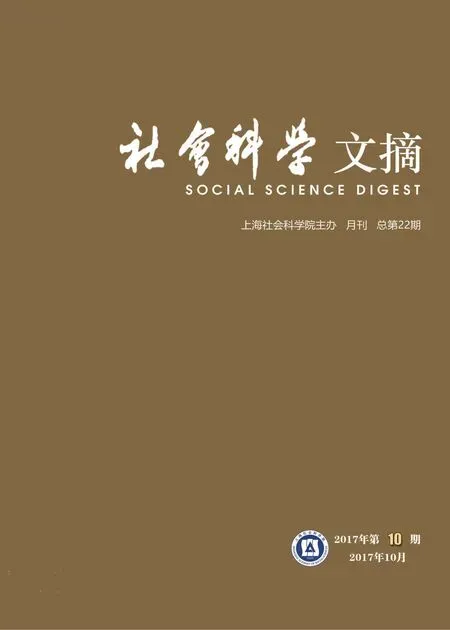文學史作為中國文學教育基本模式之檢討
文/高玉
文學史作為中國文學教育基本模式之檢討
文/高玉
文學史研究,學術界已經有了豐碩的成果,很多問題都有非常深入的探討,但絕大多數成果都是屬于文學史“內部”研究,也即在認同文學史作為學術和教育方式的合法性和權力的前提下,研究文學史的方法、模式、內容等。而更為宏觀的從外部對文學史的價值、作用和意義等進行反思則相對比較少。“文學史”作為文學研究的學術問題,這是無可懷疑的,“文學史”作為文學教育的基本途徑和方式,這也有合理性,但作為學術方式的“文學史”和作為教科書的“文學史”是有所區別的。本文主要討論作為文學教育基本模式的“文學史”,包括歷史形成、現狀、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等。
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史是現代高等教育的產物
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史一定意義上說是現代高等教育的產物。20世紀初,清政府開始實行“新政”,教育上改革科舉,試辦新式學堂。1902年管學大臣張百熙主持制定《欽定學堂章程》,次年又與張之洞一同修改制定《奏定學堂章程》,并頒布實施。《欽定學堂章程》中的《欽定高等學堂章程》和《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均仿照日本大學體制,設七科,其中“文學”科的“詞章學”,就是后來“文學”專業的濫觴。《奏定學堂章程》中的《奏定大學堂章程》其“文學科大學”設“九門”,“中國文學門”從原來的大“文學”中分化或者說獨立出來,相當于現在的“中國語言文學”專業,包括課程16種。其中的“歷代文章流別”這門課后來就固化為龐大的中國“文學史”家族,包括“通史”“階段史”“專史”以及屬于“史”層面的文學流派、文學社團、作家作品研究等。
1904年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它實際上是作者根據《奏定學堂章程》的要求,為了上課而應急編寫的,其本質是中國大學教育的產物。之后的100多年來,中國出版了大量中國文學史著作。這些文學史絕大多數也是應大學文學教學而生,很多是講課的產品,是在講義的基礎上修改而成。民國時期把“中國文學史”當作學術論著來寫作的雖不乏其人,但非常少。
當今,一般所說的“中國文學史”主要是指中國古代文學史,不包括現當代文學史。中國現當代文學雖然只有不到100年的歷史,時間長度上與有3000年歷史的中國古代文學相距甚遠,但迄今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不論是數量還是規模都可以說不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之下。1949年之前,現代文學雖然有30多年的歷史,文學成就也非常大,但現代文學那時卻沒有一部真正的“文學史”。
回顧現代文學史學史,我們可看到,“新文學”很早就在“史”的層面得到關注,但新文學“史”不具有獨立性,這當然與新文學時間太短有關,但更與當時的大學教育課程設置有關。民國大學教育學制、分科以及課程設置基本上是沿襲晚清的“大學章程”。1913年之后,“國文學”課程雖然有很大的發展和變化,但總體框架和結構沒有根本的變化。1949年之前,“新文學史”著作很少,且作為“史”很不純正,即使僅有的幾部不純正的“史”也與大學講課有關。這些新文學課以及講稿與著作殘缺或粗糙,既不為外界重視,也不為作者自己所重視,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新文學在當時的大學中文系課程設置中是邊緣化的,沒有被納入體制中去。
但1949年之后,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學教育學科設置。1950年,“中國新文學史”作為課程正式納入教育部規定的中國語言文學系課程體系。1951年,教育部委托老舍、蔡儀、王瑤和李何林4人擬定“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這兩件事意義非凡,其明顯的結果就是,隨著課程的確立,應聲產生了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由此也成就了這本書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奠基之作的地位。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之后,各類“中國新文學史”著作接連產生。從此,中國新文學史成了中國大學中文系最重要、最基礎的課程之一,并在此基礎上衍生出各種“專史”。“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也成了新文學教育的最重要方式。
20世紀90年代之后,“文學史”著作迅速增加。90年代以來,中國大學大規模地擴招,中文系的學生人數也迅速增加,另外還有很多與文學相關的專業也開設文學史課,所以文學史教材用量迅速增加。同時,大學的類型和層次不同,大大豐富了文學史的類型和層次。90年代之后產生的各種文學史絕大多數是根據學生層次和學習要求編寫的,很少是出于學術的沖動,因而也很少真正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這深刻地說明了當代“文學史”著作的教學性。
中國“文學史”深深受制于高等教育
中國的“文學史”興起于高等教育,又深深受制于高等教育。但中國“文學史”在成長和發展的過程中,又與中國傳統的“史傳”觀念以及西方科學的“專業”觀念緊密相聯,本質上是被建構起來的,其中有很多誤解。
自《奏定大學堂章程》頒布以來,或者說自“中國文學門”設立以來,中國“文學史”著作的數量已經非常龐大。中國的大學教育催生了一個龐大的“文學史”家族。查看民國大學以及新中國大學中文系的課程表,雖然“文學史”課程只是眾多課程中的一門課,似乎只是開設的時間比較長、學時比較多而已,但其實不然。仔細分析,可以看到,眾多的文學課其實是圍繞文學史開設的,“文學史”是中心。“文學史”不僅確定文學課程的坐標,確定文學經典,確定框架,而且從深層上確定文學課程的思維模式。“史”在中國大學文學教育中,具有靈魂性,中國大學文學教育不僅是“史”的方式,而且是“史”的思維,當然也是“史”的形態。
當初張伯熙設計大學章程包括課程,主要是仿照日本的大學體制,而日本的大學體制又是來源于歐美,因此,歐美的大學體制才是中國現代大學體制的深層模本。而歐美現代社會包括大學精神的根源是“科學”,所以“科學”精神也是中國現代大學的基本精神。20世紀初興起的中國大學非常注重實學,在專業設置上重視課程的實用性和知識性。文學本來是一種“虛文”,與知識無涉,但“文學”一旦加上“史”,就變成了知識,就變成了“實學”。這樣,中國古代繁榮的文學與“史”結合,和西方的“知識”“科學”相遇,一拍即合,迅速合流,從而以“實學”的形式迅速發展。所以,本質上“文學史”是西方科學精神與中國古代“史傳”文化的一種契合,是傳統的“四部”向現代“七科”轉變的一種產物。也因此,中國大學文學教育的“文學史”其實是中國對西方“科學”和“專業”的一種誤讀和誤解。“文學史”作為一種文學教育模式,并不具有必然性,也不是普遍現象,而是一種中國特色。
回顧中國大學100年來的“文學史”教育,我們可以看到,作為教育形態的“文學史”其實重在“史”而不是“文學”,也可以說對象是“文學”,而歸結點則在“史”,本質上是學術研究,而不是文學教育。民國時期,大學的文學教育從根本上說是學術性的,是以“史”為中心,更強調學術研究,目的是培養知識性的、學識性的人才,且其研究的對象是中國古代文學,而不是新文學,不是培養學生的“文學”才能,包括文學欣賞能力和寫作能力。正是因為如此,民國時期文學教育的文學研究和語言研究以及文學史研究聯系非常緊密。
對照民國時期的大學文學教育,我們可以看到,民國大學教育“文學史”是第一位的,“文學鑒賞”是第二位的,是通過文學史教育附帶性完成的,“文學創造”幾乎就沒有,相反是被排斥的。民國時期,大學也開設寫作課,但這種課程和教學這種課程的老師都是很邊緣化的,而且還多是教文言文寫作,內容上則相當于現在的應用寫作,文學寫作還不如一般文章寫作重要。民國時期,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要是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和語言,而新文學創作則無所歸屬,勉強可以歸入到外文系,因為當時的新文學主要是受西洋文學的影響,主要是學習西方文學而來。因此民國時期大學中文系事實上與文學創作之間沒有關系。
這種模式一直延傳至今,當今的大學文學教育基本上是以“文學史”為中心展開的,學生的文學能力也是通過文學史的學習來完成的。當今中國大學文學課程,實際上是由三大塊組成的:一是“文學史”;二是理論課;三是專題課。學生的考核則是二種方式的:考試,知識性的;論文,學術性的,當然是各種層次的,最高級別的是畢業論文。這些課程以及考核方式看起來豐富多樣,其實很單一,可以歸結為文學知識和文學研究,更簡單的概括就是“學問”二字。也許學生在“學問”的過程中其文學欣賞能力也有所提高,其寫作水平也有所提高,但這種提高并不是當今文學教育的本義,而是意外收獲。
文學史教學需要進行模式的改革
但是,這種以文學史為中心、重學術的大學文學教育是值得商榷的,是值得檢討和反思的,文學史教學需要進行模式的改革。
清末和民國時期的大學文學教育不重視文學創作和文學欣賞水平有它的原因。中國現代大學不是自然生長起來的,是從西方學習而來,是在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的“興實學”背景下產生的。文學作為專業本質上是“以西方學科體系框定中國舊學”,即文學專業不是產生于對中國文學問題的探尋從而形成學科,而是從西方科學體系“文學”學科出發演繹出來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現象中尋找適合的對象,本質上是西方科學體系在中國的衍生物。所以它一開始就不是為了解決中國文學的發展問題,不是為了解決中國文學的創作問題,也不是為了解決中國讀者的閱讀和欣賞問題,它是生硬“移植”的,其學術性質是規定的,其研究對象也是規定的。雖然新文學在1949年以后正式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進入課程體系,但整個中國大學文學教育性質始終沒有質的變化,從根本上仍然是學術性的。
民國時期的大學是大師匯集的地方,是學術圣地。大學中文系尤其強調學問,老師和學生的工作著重圍繞學問研究和學術訓練展開。這種模式或者說體制一直延續至今。但大學作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應該是豐富而多元的。就文學教育來說,文學研究、文學知識的生產和傳播是一方面,文學創作、文學傳播、文化繁榮等也應該是一方面。文學欣賞能力、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是“三位一體”的,三者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促進,文學欣賞是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所以,即使從文學研究的角度來說,大學文學教育加強文學創作和文學欣賞與批評也是有益的。
民國時期,中國的大學實行的是精英教育,主要是培養尖端人才。但今天的中國大學,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現在中國的大學本科教育實行的是通識教育,主要培養通識類人才。但就文學教育來說,今天的大學各個層次的中文專業甚至準中文專業,其文學教育模式基本上還是學術性的。從就業的角度來看,反而是大學教育中極其邊緣化的,沒有多少學術含量的寫作教育更為重要,更有實用價值,實際工作中,大學教育中花大量時間和精力學習和培養的“文學史”知識和學術研究能力反而無用武之地。
雖然1949年以后“中國現代文學史”作為獨立的課程進入教育部課程體系,并且不斷繁榮壯大,衍生出大量的子課程。但新文學只是作為文學史合法了,而作為文學創作并沒有得到認同。外文系也沒有把新文學創作納入自己的課程體系,這樣,新文學創作實際上被大學教育拋棄了。目前,雖然越來越多的作家進駐大學校園,有一些大學研究生教育也開設了“文學寫作”專業,但這并沒有對大學中文系文學教育體制構成真正的沖擊,當今大學文學教育整體上還是排斥文學創作的。
大學教育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學以致用”,但大學文學專業則是中國大學教育中少有的“學以不致用”的專業。學習文學不是為了創作文學,從事文學創作的人不需要接受正規的大學文學教育,作家都不是大學文學教育培養的結果。大學的文學史學習對于作家沒有用,而對于創作有用的東西則又不是大學教育所能夠提供,所以文學創作似乎永遠都是自我摸索的結果,是閱讀和感悟的結果,是一個不需要教育的天才性勞動。因此在當今中國,文學研究和文學創作一直是被嚴重撕裂的。
大學文學教育應該走出“科學”的誤區。文學具有審美性,審美的最重要特征是感性,科學作為理性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釋審美性,但科學對于感性的解釋是有限度的。事實上,即使是文學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是科學的。文學知識可以以“科學”的方式來教育,但文學寫作,文學欣賞等很難用“科學”來解決。文學教育需要改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強寫作訓練。研究文學和語言不是中文的“專業”核心,寫作才是核心,當然,這里的“寫作”是寬泛意義上的,包括寫文章。
就文學史作為教育模式來說,值得改進的地方很多,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文學史模式改革,文學史教育需要加強文學性。文學史作為學術,作為學科,其合法性和權威性是毋庸質疑的,但作為文學教育的基本方式卻存在很多問題。我認為,作為教科書的文學史和學術專著的文學史應該嚴格區別開來,二者的差別在于教科書的文學史應該是批評化的、鑒賞化的,是集文學歷史和文學欣賞、文學知識和文學寫作為一體。文學史可以既具有歷史感、又充分展示或呈現出文學性,目前我們應該朝這個方向努力。
第一,文學史對作品要有充分的細讀和解析。作為教科書的文學史,目前主要是兩種模式的:一是知識型的,這種文學史的重心在“史”;另一種模式是鑒賞型的,重在“文學性”。知識型的文學史,因為它本質上只是關于文學,并不深入到“文學”內部。欣賞型的文學史,需要讀者具有良好的對于文學的理解和感悟,這種文學史其“歷史”只是構架,文學才是根本,學習這種文學史會真正提高人們對于文學的理解和鑒賞,會提高學習者的文學水平。文學教育應該采用鑒賞型的文學史。
第二,文學史學習應該和文學批評實踐結合起來。文學教育可以在文學史的學習過程進行文學批評訓練。具體辦法就是對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進行細讀和分析,從而訓練學生的文學判斷能力。同時,文學史學習應該有所應用,即把細讀和分析經典作品的方法應該運用于文學批評實踐,動手寫作文學評論,在文學批評的實踐中提高文學批評能力。
第三,把文學史教育和文學創作結合起來。目前中國大學文學教學更重視學術上的發現和學術基本功訓練。但這種模式是偏頗的,科研論文當然也是寫作,但寫作應該更寬泛一些。我認為學生學業考核方式可以是學術性的,也可以是創作性的。文學史學習一方面學習和解讀歷史上的經典文學作品,同時也學習和借鑒經典并模仿寫作,模仿不能產生文學大師,但對于文學寫作以及一般性寫作來說,模仿卻是很好的學習和訓練。
中國的大學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從就業來說,中文教育越來越成為一種文化教育、素質教育。陳平原說:“文學作為‘專業’的魅力正日漸消退,而作為‘修養’的重要性卻迅速提升。”我認為這個概括非常準確。中文專業已經沒有一般意義上的專業技能與專業水平。文學史教育應該適應大學的變化,應該適應就業的變化,應該從學術中解放出來,更具有實用性。
(作者系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摘自《文學評論》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