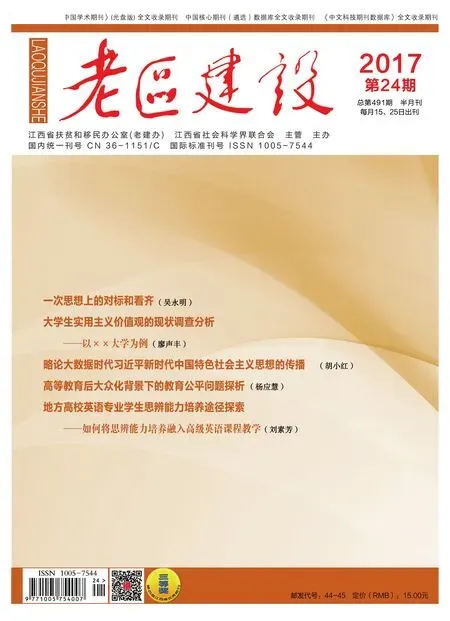明代復古書院研究
鄧惠蘭
明代學者聶豹曾言:“陽明先生悼俗學之涂生民也,毅然以身犯不韙,倡道東南,而以良知為宗。……有志之士聞風而興者,時惟江西為盛,江西之盛惟吉安,吉安之盛惟安福,故書院之建惟安福有之,題曰復古者。”[1]陽明心學惟安福最盛,書院之建惟復古書院,可見復古書院地位之高、影響之大。明代學者陳柏則云:“寰中書院如白鹿、嵩陽、石鼓、岳麓,其地本名勝……近若陽明青原、復古,又與諸區爭盛。”[2]陳柏把宋明兩代書院相比,認為明代復古書院可與宋代四大書院爭盛,可見當時復古書院可謂天下聞名。明代,安福是江右王門最富生氣的重地,復古書院是安福公有且規模最大的書院。安福鄒守益 (1491-1562)等學者長期在復古書院舉辦大規模陽明學講會,使得書院學者云集,名儒薈萃,盛極一時。
一、復古書院名稱的含義
要研究復古書院,有必要了解書院名稱所包含的意義。“復古”一詞被明代學者賦予了多種含義:
1.重振安福昔日人文盛況。鄒守益《復古書院記》中言:“惟昔安福以忠義文章顯于東南,邇來漸黯矣,自今且將復于古乎?”[3]唐宋時期,安福享有“文章節義之邦”的美譽,唐禪宗七祖行思、北宋文學家劉弇、北宋醫學家劉元賓、南宋詩人王庭珪等大批名人志士皆出自安福。鄒守益認為,通過復古書院文化教育,安福文化將再度興盛。
2.復興先師王陽明心學。聶豹《復古書院記》中言:“欲還古治,當求古人;欲求古人,當復古學。學之古何所始乎?‘執中’一語,萬世心學之源也。”[4]聶豹認為,陽明心學中蘊含了許多治理天下的智慧,要恢復古代和平昌盛之治世,就應該求學于古人王陽明。
3.恢復內心之良知。羅洪先《答復古問》中言:“圣人遠矣,心之精微不可得求矣。復之奈何?復吾心之精微,不異于圣人之心之精微,斯可矣。”[5]古代圣人思想隨著長久流傳,漸失去其原本含義。若要恢復圣人思想之精華,其實可以反求本心,在內心中證悟圣人之道。
4.學習古人良好品行。王時槐《重修復古書院記》中言:“書院以復古為名,必愿諸士為古人為己之學。居則為良士,敦孝友忠信之行以淑于鄉;出則為良臣,懋宣力濟世之業以輔于國。而后無負于茲院,且為不愧復古之名之真儒哉。”[6]以古人為學習榜樣,做真正的儒者。居家則為孝悌行于家、忠信著于鄉之良士,出仕則為濟世安民、輔政護國之良臣。
二、復古書院的創建
為惜陰會提供穩定講所是復古書院創建的根本原因。在復古書院創建的前十年,安福劉曉、劉邦采等人就創立了以惜陰為名的講會組織,王陽明特作《惜陰說》以示勉勵。安福士人聞風響應,紛紛組建惜陰會,惜陰會從單個講會組織變成安福地區講會的統稱。鄒守益歸鄉講學之時,“四方之士,聞風而來者恒數十輩,至市館不能容”[7]。惜陰會日益興起,然而講無定所、講所狹隘,阻礙了惜陰會的繼續發展。鄒守益就言:“惜陰之會……來者日興起……然靜言思之,間月為會,五日而止,則不免暴寒之乘;往會各鄉,近者為主,則不免供給之擾;自遠來者,雖欲久止,而隨眾聚散,則不免跋涉之勞……是則書舍之立,非為觀美,其于惜陰也尤急。”[8]惜陰會的發展有“暴寒之乘”、“供給之擾”、“跋涉之勞”三點隱憂,要克服這些缺點,創建書院是首選辦法。
陽明學者、知縣程文德的到來為復古書院創建提供了良好契機。建書院的想法從惜陰會創立之時就產生了,然而要建立一所能容納眾多會眾的大型書院,“非千金莫能室也”[9],故“惟茲書屋之議,蓋十有余載矣”[10]。直到嘉靖十五年 (1536),浙江永康人程文德(1497-1559)移為安福令,使得復古書院創建具有主持之人。程文德重視書院,熱衷講學,“好古宣教”[11]。 來到安福后,他感嘆:“(縣學)齋堂數楹,號舍無地,何以專志業、稱明詔也?”[12]安福全縣只有一學宮為居肆成藝的場所,難以滿足人才培養之需要。作為一縣之長,他自愿擔負起興學建院之使命,親自尋求建書院之地,募求建書院之金,規定建書院之制,為復古書院的創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官民通力合作促成了復古書院的成功創建。程文德在當年八月即改任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而書院于九月始建,故書院具體建設工作基本在鄒守益和地方官員組織、民眾輔助下完成。鄒守益是江右王門的開山祖和掌教者,被譽為最得陽明學真傳的承繼人,其“文章道德,巋然負重望,人咸以今之顏子稱之”[13]。鄒守益適時擔負起創建復古書院的重任,連發兩封公開信——《簡惜陰諸友》和《書書屋斂義卷》,倡導各方士友為書院建設捐財出力。于是,“蓄木者獻其材,藏書者獻其籍,積產者獻其田,眾志子來,罔有差池。 ”[14]江西提學徐階、吉安府同知季本、知縣俞則全、縣丞王鳴鳳等官員對書院建設更是勞苦功高。
建設完成的復古書院,前為道德門,大門額“復古書院”,儀門額“惜陰”,中為文明堂,左右為忠信齋、篤敬齋,后為茂對堂、尊經閣,另有翼室四間、東西號房八間,左有射圃、觀德亭,齋舍、庖湢、幾榻、器用俱備。
三、明代復古書院的發展演變
復古書院建成后,便成為江右王門講學中心地之一。鄒守益記道:“惜陰之會,春秋舉于復古,而四鄉各間月舉之。”[15]每年春秋大會,名儒宿學咸集于此,規模甚大。事實上,每有名家至吉安必至復古書院,錢德洪、王畿、羅洪先、聶豹、歐陽德等王門領袖皆曾會講其中。歸鄉講學的鄒守益把復古書院作為其講學授徒的大本營。在鄒守益等學者的潛心經營下,復古書院會講頻繁,書院發展興盛。現列舉書院舉辦的一些著名講會活動:
在經歷了發展巔峰后,書院發展日漸式微。書院發展走向低谷的過程分為以下四個階段:1.鄒守益逝世。“自廓翁(鄒守益)捐背后,青原復古諸會所,荒落殆甚。諸友悵悵,若無所歸。”[16]嘉靖四十一年(1562)鄒守益的逝世是復古書院由盛轉衰的轉折點。2.張居正毀書院。劉元卿曾言:“江陵柄政,修申商之術,孤立行一意。我安成傅、劉諸君詆訶時事,首犯其所最忌。于是嗾言者極論講學之弊,議毀天下書院。”[17]由于安福傅應楨、劉臺的上疏,萬歷七年(1579)張居正毀書院之時,復古書院首當其沖。書院改名為三賢祠,并割一半膳田供給官府。3.魏忠賢毀書院。天啟五年(1625),魏忠賢毀書院,書院改名為勛賢祠。4.明末毀于戰火。
書院雖每次受毀都得到修復,如尹一仁、知縣李忱、知縣閔世翔、知縣潘濬等先后修復書院,但由于書院講會難以再興,衰落成為其必然趨勢。清代,書院屢有興修,但不復講會,成為普通的考課式書院。
四、明代復古書院對當時區域文化的影響
1.促進了區域學術發展
明代復古書院講會的興盛促進了區域陽明學的發展與創新。復古書院擁有完備的講會制度,“有田若干畝,以資會撰之費。會有期,司會有長,會凡若干人”[19]。 會田、會期、會長、會眾等一應俱全,為明代安福學者提供了談經論道的優良場所。浙中王門領袖王畿就曾言,復古書院“每會四方翕然而至者,常不下二三百人,予每參次其間,上下論辨,有交修之益。 ”[18]復古會中,師生、學友通過不斷地質疑問辯、相互交流,學術思想得到完善,學術水平得到提高,學術理論得到創新發展。
復古書院講會開啟了地域書院講會之風,一大批講會式書院紛紛建立。明中后期,安福形成了以復古書院為中心,包括復真、復禮、連山、識仁、中道、一德、道東等書院的學術講會圈。王時槐曾言:“吾吉聞陽明先生之學結會聚講最盛者稱安福”[20]。 王畿亦說:“陽明夫子生平德業著于江右最盛,講學之風亦莫盛于江右,而尤盛于吉之安成(安福)。”[21]明代有“天下談學,動推安成”[22]的說法。 明代安福書院講會的興盛促進了區域陽明學的發展與創新。明張崧曾言:“良知之學,安福獨精,風流所暨,莫不根柢義行,士不談道即恥笑,以為匪類。 ”[23]清初施閏章亦說:“余觀于吉州而知理學之甚也,其最則安福。”[24]通過頻繁的講會活動,安福學者不斷砥礪各自學術,學術領袖輩出,鄒守益、劉邦采、王時槐、劉元卿等皆一代鴻儒。安福王學就被譽為陽明學修正派,繼承了先師王陽明優良傳統,極力強調工夫修養、道德修煉和追求實際。
2.加強了區域社會教化
復古書院學者在教學活動中常抱有移風易俗的責任感,注意下啟普通百姓,勸善規過。程文德在主持復古書院建造時曾言:“昔人謂移風易俗,莫善于學,其在此乎! ”[25]他認為,倡正學可淑人心,建書院可興禮義,“使人知謹于一念之微以達于五倫之實,將移風易俗,挽澆漓而還淳厚。”[26]復古書院自建設之始就被賦予了社會教化的職能。鄒守益則認為,對鄉里百姓講授陽明學可達到覺民行道之目的,是陽明學“萬物一體之實學”、“小試于鄉”的體現。嘉靖二十八年(1549),鄒守益在《惜陰申約》中曾言:“人立一簿,用以自考;家立一會,與家考之;鄉立一會,與鄉考之……居處果能恭否?執事果能敬否?與人果能中否?盡此者為德業,悖此者為過失。”[27]可見,復古書院學者極力將儒家傳統倫理觀念傳授給廣大普通民眾,使地方風俗與倫常觀念得到改善,維系并提升鄉村的道德與文明水平。
浙中王門領袖錢德洪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參加復古會時,曾感嘆:“窮鄉邃谷,雖田夫野老,皆知有會,莫不敬業而安之。 ”[28]可見復古會對當地民風民俗的影響。大約五十年后,王時槐在《重修復古書院記》中言道:“久之,英賢輩出,即四郊之民,知違教習非之為恥,鬭訟漸稀,邑以無事。 ”[29]復古書院教育真正實現了化民成俗的社會理想。
3.推動了區域人才培養
程文德曾言:“今萬家之邑而惟一學焉,奚惑乎人才之日靡也?書院者,固學宮之翼而群士之廨也。”[30]在安福縣學容納生徒有限的情形下,創建書院是挽救安福人才日靡問題的重要途徑。書院建成后,不但頻繁舉辦講會,還擔負科舉教育職責,推動了安福地區文化教育的興盛。復古書院被譽為“洙泗”,安福被譽為“鄒魯之區”。
在學而優則仕的時代,科舉的數量和質量往往成為衡量地方教育水平的重要指標。從進士數上看,明代安福進士高達222名,超過明代吉安府進士818名的四分之一,在全省各縣中名列前茅。“一門三進士”、“一門五進士”,在安福并不罕見。如鄒守益為正德年間探花,其父鄒賢、兒鄒善、孫鄒德涵、孫鄒德溥、孫鄒德泳皆中進士,開創了一門四代六進士的傳奇。安福地區取得如此驚人的科舉成就與復古書院的文化教育密不可分。復古書院把教育與學術作為書院生存發展的兩大支柱。崇尚教育,重視學術,復古書院成為明代安福地區培養優秀人才的主要基地。在復古書院學風影響下,安福地區形成了濃厚的讀書風氣和科舉氛圍,“尚詩書,安勤儉,比屋弦誦不輟,良子弟爭趨為士”[31],因而“人賢彬彬輩出”[32]。
[1][4][11][13][19]聶豹.復古書院記/汪泰容.吉安書院志[M].北京:中華書局,2013.
[2]陳柏.復中書院記/安陸府志卷 32[M].1669.
[3][14]鄒守益.鄒守益集卷 6 復古書院記[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5]羅洪先.答復古問/吉安書院志[M].北京:中華書局,2013.
[6][26][29]王時槐.王時槐集·重修復古書院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7]鄒德涵.文莊府君傳/鄒守益集卷 27[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8]鄒守益.鄒守益集卷 13 簡惜陰諸友[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9][12][30]程文德.創建復古院記/吉安書院志[M].北京:中華書局,2013.
[10]鄒守益.鄒守益集卷17書復古精舍輪年約[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15]鄒守益.鄒守益集卷11答復董生平甫[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16]王畿.與羅念庵/青原志略卷 8[M].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
[17][32]劉元卿.劉元卿集卷 7 復古書院續置田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8][21]王畿.王畿集卷 16 漫語贈韓天敘分教安成[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20]王時槐.王時槐集·朱康夫墓志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2]劉元卿.劉元卿集卷 3 簡朱玉槎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3]安福縣志編纂委員會.安福縣志卷 30[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
[24]施閏章.重修復真書院記/吉安書院志[M].北京:中華書局,2013.
[25]宋儀望.鄒東廓先生行狀/鄒守益集卷27[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27]鄒守益.鄒守益集卷 15 惜陰申約[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28]錢德洪.惜陰會語略/吉安書院志[M].北京:中華書局,2013.
[31]彭華.送過侯九皋之安福序/乾隆安福縣志卷 2[M].1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