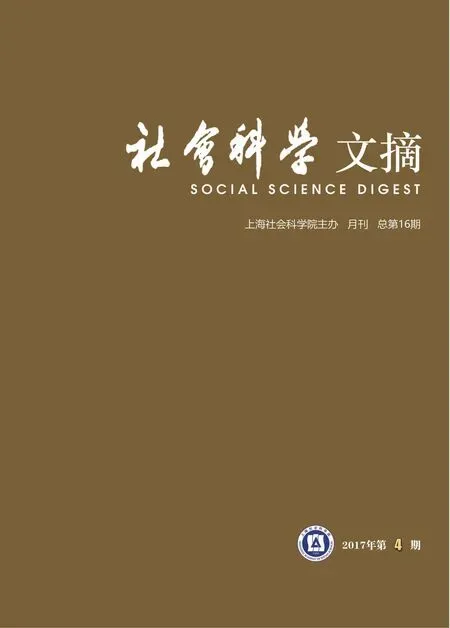中國政治精英吸納模式的歷史演進與轉換邏輯
文/王炳權 李海洋
中國政治精英吸納模式的歷史演進與轉換邏輯
文/王炳權 李海洋
精英(elite)是指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系統中所有最強有力、最生機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精英不分好人還是壞人。精英包括各類人才,分布在經濟、政治、文化以及社會等領域。一般而言,狹義上按照領域來劃分,人們往往將精英劃分為經濟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以及社會精英,等等。其中,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是指政治系統中的兩個群體:其一是掌握重大政治決策權的政治精英,他們制訂和頒布政策,由處于最高地位并握有權力的少數人組成;其二是統治階級中的其他成員,他們是第一個群體的支持基礎和后備力量。而本文所探討的政治精英,是指政治系統或政治組織中有才華、有能力和最精明能干的人,他們是握有權力之人,同時也包括其支持基礎和后備之人。如果其中握有政治權力之人及其支持基礎和后備之人沒有才干,那么這些人也不是政治精英。所以不能簡單地把所有握有政治權力的人及其后備者都定義為政治精英。在政治系統中,政治精英的多少主要取決于政治精英吸納模式的開放性和競爭性。一個良好的開放競爭性的政治精英吸納模式可以更多地吸納包括知識精英在內的社會精英,政治系統就會更為穩定并具有較強的治理能力,反之亦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精英吸納模式的歷史演進,大概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即非競爭性技術精英吸納階段(1980-2002年)、競爭性精英吸納階段(2002-2014年)和低競爭性精英吸納階段。相對而言,非競爭性技術精英吸納模式具有高開放性和低競爭性,但其精英吸納功能很強;競爭性精英吸納模式具有低開放性和高競爭性,其精英吸納功能具有中等強度;低競爭性精英吸納模式具有低開放性和低競爭性,其精英吸納的功能最弱。所以在時間序列的模式轉換中,政治精英的吸納功能并沒有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而逐漸走強,而是呈現漸弱的態勢,其政治精英流動結構體系也逐漸呈現出封閉性。這不僅阻斷了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向政治系統流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阻斷了政治體系內的精英選拔,而由此造成了大量的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既徘徊在體制外又流連在體制內。政治體系的治理能力和政治合法性總體減弱。
非競爭性技術精英吸納模式的形成和轉換
從新中國建立到20世紀60年代初,由于實施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干部委任制和革命“紅色”標準的政治門檻,所以政治系統對社會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的吸納十分有限,只局限于一些特別有名的知識精英群體,由此所形成的政治精英吸納體系實質上是一種較為封閉的模式。到文革時期,這種封閉的精英吸納模式遭到摧毀,政治精英吸納基本停滯。20世紀80年代初,中央以政治運動方式推動干部政策的實施以后,政治精英吸納停滯的局面得以改變,并形成了具有運動式特征的階段性的非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模式。
非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模式的主要特點是體現在非競爭性、高開放性和強精英吸納能力。
非競爭性是由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和制度安排所決定的。當時干部選拔制度仍然是委任制,干部任用的決定權主要掌握在領導手中,領導就是“伯樂”。這就意味著當時的政治精英吸納必須通過“伯樂選馬”的途徑來實現。雖然當時在“伯樂選馬”的過程設有諸如群眾評議和組織考查等程序,精英之間也可能存在一定競爭,但這種競爭只是精英之間的隱性競爭,在顯性的制度安排上沒有“賽馬”競爭機制。在中央以運動式和“四化”標準選拔任用干部時,由于年青知識精英的缺乏,所以除了教育系統以外(為了留住教育系統的人才,限制流動)的絕大多數年青知識精英沒有競爭對手而得到了任用。所以當時的政治精英吸納無論在制度設置上還是在實際的運行上都幾乎是沒有競爭性。
高開放性是指這個時期的政治精英吸納模式具有很大的廣度。由于改革開放時期的政府管理方式沒有脫離總體性社會的管理結構,政府部門十分龐大,無論是縱向還是橫向政府部門的干部選拔都是全方位的政治精英的吸納。不過,必須指出的是,由于知識精英主要集中于教育系統,為了防止他們從教育系統流出并進入其它政府部門,政府設置了具體的限制性政策措施——防止“教師改行”。一些擁有社會關系的從教知識精英也流入了其他政府部門。
強精英吸納能力最突出的表現是在很短時間內實現了精英流動,這得益于 “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干部政策的要求和政治運動式的推動。當時中央組織部向各級黨政組織提出了具體的任務指標和期限,要求各級黨政部門嚴格按照中央組織部規定的學歷和年齡配額組建領導班子,并在限期內完成組建工作。各級組織部門在執行中央“四化”干部政策時相應簡化原有耗時的干部選拔程序和過程,把群眾參與的民主評議會作為政治監督的輔助手段,所以從上至下的干部選拔和黨政領導班子重建在全國范圍內取得了預期效果。
以“伯樂選馬”的方式選拔政治精英存在明顯的不足。這是因為“伯樂選馬”的方式,不但受制于伯樂自身的知識結構、識別能力和政治道德水準,而且也受制于政治組織中人格化依附關系,所以這種具有“伯樂選馬”和非競爭性雙重缺陷的精英吸納方式在本質上是不能實現優良政治精英選拔的。然而,為什么這種非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方式又是有效的呢?這是因為這一方式是在特定條件下產生作用的,這一特定條件就是由精英的高度短缺性、運動式的政策推動以及剛性“四化”標準相互結合所構成的,這三個構成因素缺一不可。
競爭性精英吸納模式的實踐和反轉
2002年中共中央出臺了《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為非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方式的制度創新拓展了空間,并直接推動了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方式的形成。
一些地方根據《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基本要求,對干部選拔任用制度進行了大膽的創新,在實踐中形成了考任制、選任制和考選結合制的三大方式。考任制主要有“一推雙考”、“公推公選”、“雙推雙考”、“兩推一考”和“三推三考”等;選任制主要有“公推直選”、“兩推一選”、“三推一選”和“三推兩選”等;考選結合制主要有“三推三考兩票決”和“三推兩考一選”等。還有學者把以上領導干部公選制的實踐形式劃分為以考試、考評與考察為主的考任制;以推薦、自薦與選舉為主的選任制;以競崗、競聘與競爭為主的競任制。
考任制的主要特點是在領導人選產生的初始環節與決定環節上,以競爭性考試為主,以推為輔。選任制是在領導人選產生的初始環節與決定環節上,以選為主,以推與考為輔。其選拔任用環節主要包括職位及其資格條件面向社會公開、社會各方推薦報名與自我推薦報名、資格審查與公布、統一筆試或者投票初選,候選人演講再次投票選舉直接產生最終人選。競任制是在領導人選產生的初始環節與決定環節上,以競爭性的筆試、面試或者選舉為主,輔以推與議的方式。無論是考任制或選任制,還是兩者兼之的選拔方式,都是一種競爭性干部選拔方式,這種方式直接推動了非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模式向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模式的轉變。
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初政治精英吸納模式的轉變動力來源于經濟因素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央領導人的推力,那么,這一轉變的動力除了“四化”干部標準的慣性牽引和中央持續推動力外,主要源于干部任用上腐敗行為的倒逼。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紀初,由于干部任用權力掌握在主要領導手中,“領導說了算”的權力構架導致了買官賣官和任人唯親現象普遍蔓延,這不僅阻礙了政治體系對政治精英的選拔和吸納,而且嚴重影響了黨群、干群關系和黨的形象,所以中央想通過競爭的選拔方式來消除和減少干部任用上的腐敗行為,促進政治精英的吸納和流動。
但是,與非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模式相比,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模式的吸納能力并未超越前者,且而呈現不斷下降趨勢。其根本原因在于這一階段的干部選拔任用制度雖然嵌入了競爭性,但缺乏開放性以及在運用上的有限性。根據2002年以及2014年修訂版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規定,政治精英的吸納只能限定在體制內現任干部當中,雖然表面上其吸納范圍放大到了國有企事業單位,但其職級和職務剛性的要求使得選拔范圍縮小到以黨政部門為主的部分干部群體中。特別是當競爭性干部選拔方式僅僅作為試驗或者“點綴”推動時,那么由此構成的政治精英吸納模式并未因為競爭性的嵌入而產生常態化的吸納能力,未能對社會精英特別是知識精英產生廣泛的吸納。不僅如此,在2014年《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修訂版出臺以后,競爭性干部選拔任用方式的實踐活動也就基本停止。這是因為在修訂版《條例》第九章第50條中對“公選”做出了條件性限制,收縮了干部“公選”的空間,這就意味著競爭性政治精英的吸納模式向低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模式反轉。
導致競爭性政治精英的吸納方式向低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方式反轉的原因是由干部“公選”模式的實際成效和科層制組織特性導致的。從當時“公選”的情況來看,確實存在一些高分低能的情況,其能力和工作成績不盡如人意。表面上看,“公選”干部的成效不好似乎是導致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模式向弱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模式反轉的主要原因,但從實質上看,在人格化的科層制組織中,如果普遍地實行干部“公選”制度,即作為人格化官僚制組織控制的重要杠桿——人事權,通過非人格化和制度化運用,那么就會裂解了下級對上級的依附性,進而影響組織領導和黨組織的政治權威。所以干部“公選”方式必然遭遇自上而下的一致抵制和排斥,從而決定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模式向弱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模式反轉的必然性。
弱競爭性精英吸納模式的運行特征與人格化官僚制對其的影響
弱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模式是由當前干部選拔任用方式所決定的。現行干部選拔任用方式的運行特征及其人格化官僚制組織特性表現出弱競爭性精英吸納模式的基本運行特點。現行干部選拔任用方式的運行特征具有封閉性和弱競爭性,這種方式受制于官僚制(科層制)人格化依附結構,所以難以很好地吸納體制外和組織內部的精英并推進政治精英流動,從而影響政治效能的發揮以及政治穩定。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在政治體系中理性官僚制建構嚴重不足,官僚制人格化依附結構十分突出,所以干部選拔任用程序基本掌控在組織或者領導之中,有限的弱競爭性在這種結構中基本喪失殆盡,領導的意圖決定著選拔任用的目標。
官僚制(科層制)是當今中國政治組織的基本結構,與從上至下的政治動員型管理方式相契合。在當今中國政治組織中,由于權力高度集中和由此形成的“人治”格局的普遍存在,因而理性官僚制建構嚴重不足,人格化依附結構仍十分普遍。
在組織中,由于領導者掌握著組織個體的評價權、定崗權、職務晉升的決定權以及相關的處罰權,而且其權力很少受到組織運行中相關制度的約束,所以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和偏好選拔誰、任用誰、處罰誰,以至于在人格上抬舉誰,由此在組織內部形成自上而下的權力和利益的依附關系。在這種依附組織結構中,雖然干部選拔任用中有完整的動議-民主推薦-考察-討論決定-任職等程序,并且在程序中嵌入了輔助性民主和弱競爭形式,但不能改變或影響領導“說了算”的主導性控制地位。同樣,在其它程序中,一切都掌控在組織之中,并按照領導的意圖運行。雖然《條例》中有選人用人的德、能、勤、績、廉等賢能標準,但由于這一標準的抽象性和客觀上存在甄別上的困難,所以領導者獲得了很大的外溢性自由裁量權,并能實現自己的選人用人價值。
在人格化依附組織結構中,干部選拔任用的封閉性和非競爭性不僅阻斷了政治體系從外部吸納精英的路徑,而且阻斷了在政治體系內部選拔政治精英的路徑,由此導致大量的社會精英特別知識精英游離在政治體系之外,還有一些知識精英徘徊在政治體系內部,進而引發精英循環的障礙。
討論與建議
當前,由于干部選拔方式具有封閉性和非競爭性,并且受制于人格化官僚制組織結構,所以精英與精英之間以及精英與底層群眾之間的流動不暢。這不僅加劇了政治體系內部和外部精英循環的雙重張力,而且造成國家治理能力和政治合法性的降低。所以,必須構建開放性和競爭性的政治精英吸納體系,實現政治精英的內外兩個層面上的循環。
若要構建開放性和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體系,其關鍵是解決好干部選拔任用機制中的開放性和競爭性問題,同時還要解決人格化的官僚制問題。為此,首先要重啟競爭性干部公選模式,以“賽馬”機制代替伯樂“選馬”機制。競爭性干部公選模式的本質就是開放性和競爭性機制設置,主要是通過筆試面試或者票決制來選人。雖然這種模式出現了一些高分低能現象,但并不能否定這一模式的基本功能。因為引起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較為復雜,既有考試內容設置不科學、開放性不夠,又有對關系主義行為的約束不足等。所以,在進一步完善考試機制和對關系主義行為約束機制的同時,要著力推進開放性和競爭性機制建設:一是要適度降低干部公選模式中的競爭門檻,即降低在入口上的職務資格要求(可以把知識精英中的職稱換算成相應的職務,比如副教授對應副處),把競爭性范圍擴大到組織內部或者外部較大群體中,這樣既可以對社會精英特別是知識精英開放,也可以對其組織內部精英開放;二是要重啟民主投票推薦機制,盡量壓縮或者廢除談話推薦方式,并重新恢復2002年《條例》中的第十七條,“確定考察對象時,應當把民主推薦的結果作為重要依據之一”,而不是“重要參考”。同時要設置較為剛性和較高的專業門檻,把無專業性的人限制在外,其次要著力推進非人格化的理性官僚制建設。非人格化的理性官僚制建設就是要以法理性權威代替“人治”依附性權威,在組織體系中以民主法治和權力約束為基礎,建構包括干部選拔任用和功績制在內的系列管理制度,實現制度化管理,由此鏟除“人治”依附文化土壤和關系主義的風氣,促進開放性和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模式的成長。
(王炳權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海洋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摘自《學術研究》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