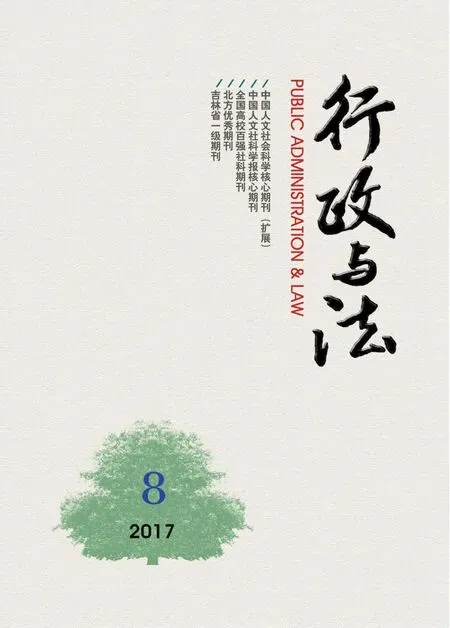校園霸凌行為法律規制進路探析
□滕飛
(吉林省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校園霸凌行為法律規制進路探析
□滕飛
(吉林省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近年來,多起校園霸凌事件頻現于公眾的視域之中,霸凌行為對受害者造成的身體戕害與心理創傷讓校園霸凌行為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本文以校園霸凌行為內涵界定及行為特質分析為切入點,借助對我國現階段校園霸凌行為規制現狀以及國外校園霸凌行為法律規制現狀的闡釋,提出校園霸凌行為法律規制的構想,以期為我國整治校園霸凌行為提供有益的參考。
校園霸凌行為;法律規制;規制手段
近年來,校園霸凌事件頻見于報端,引發了社會各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2016年4月,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2016年11月,教育部等九部門聯合發布了《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自此,校園霸凌行為規制再次成為社會輿論熱議的焦點。以往在對待這一惡性行為的看法上,研究者多是基于社會學、教育學等方面著手研究,給出的也多是集中于道德倫理教化層面的建議。[1]筆者并不否認道德倫理教化對于校園霸凌行為具有積極的調整與矯正意義,主體所做出的任何行為均是受其自身的內在價值觀所影響因而施加于外,傳統的道德倫理教化即著眼于此,力求通過對行為人所秉承的價值范式施加影響進而使其杜絕對他人實施此種行為。但從實效性的角度來看,主體所秉承的內在價值觀同其所實施于外部的行為之間并非表現為同一性。也就是說,即便主體內心具有實施霸凌行為的真實意思,但懾于社會規范的強制力約束,也會自覺收斂與控制自身行為。在諸多社會規范當中,法律規范以國家強制力為背書,因而具備其它社會規范所不具備的約束力。[2]有鑒于此,筆者認為,在整治校園霸凌行為過程中,應當依托法律規范對校園霸凌行為實現外部規制,同時再輔以道德倫理教化范式實現正向價值觀引導,從而達到對校園霸凌行為的有效管控。
一、校園霸凌行為的內涵界定及行為特質分析
“霸凌”一詞最初來自英語單詞“Bullying”,國內理論界多稱之為欺凌,考慮到“霸凌”這一概念已經成為國際層面的通說概念,故本文亦使用“霸凌”一詞作為研究對象。[3]從語義學的角度來看,“霸凌”多表現為行為人向相對人實施具有攻擊性的行為,進而通過特定行為向特定對象的施加,使得相對人的身體受到戕害、心理受到侵擾的一種惡性行為。依照對霸凌行為的解讀,筆者將校園霸凌行為定義為:霸凌行為人向相對人實施的,以言語攻擊、肢體攻擊等方式,造成相對人身心受創的一種惡性行為。由于校園霸凌行為中的雙方——行為人與相對人通常均處于相對封閉的環境即校園之內,容易造成行為人與相對人之間校園霸凌行為的反復重現。
從校園霸凌行為涉及的對象來看,霸凌行為的生成包括霸凌行為人、霸凌行為協助人、霸凌行為旁觀者和霸凌行為相對人。霸凌行為人是校園霸凌行為的實施者,其在整個霸凌行為過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其通過對霸凌行為協助人的引導以及對霸凌行為旁觀者的震懾,實現對霸凌行為相對人的侵害。霸凌行為協助人是霸凌行為人實施霸凌行為的輔助者,其存在的意義在于以其對霸凌行為的參與和配合,協助霸凌行為人實現對相對人的侵害、脅迫、侮辱和恐嚇。霸凌行為旁觀者在霸凌行為中的地位較為特殊,其一般不直接參與霸凌行為,但因其不參與和不制止的消極態度成為校園霸凌行為發生的縱容者。而霸凌行為相對人即霸凌行為的受侵害對象。在校園霸凌行為中,霸凌行為人、霸凌行為協助人以積極作為的態度,霸凌行為旁觀者以消極不作為的態度,共同構成對霸凌行為相對人的霸凌行為,進而使霸凌行為相對人的身體權與心理安寧權成為霸凌行為侵害的客體。
從行為表現類型來看,可以將校園霸凌行為分為以下幾種類型:一是肢體霸凌行為。此種霸凌行為表現為行為人借由其身體上的優勢抑或是人員數量優勢,借助肢體暴力行為對相對人實施戕害。[4]此種霸凌行為極易造成相對人的身體創傷以及精神損害,如2015年6月,江西省永新縣的多人圍毆初中女生事件。在該起事件中,共計9名未成年人參與到對受害人黃某的毆打之中。二是言語霸凌行為。此種霸凌行為的特征表現為行為人對相對人的施害過程借由嘲諷(主要針對相對人的身體缺陷等)、惡意散布不利謠言(主要針對相對人的名譽等),使相對人的精神安寧權受到損害,如2016年5月,山東日照五蓮縣中學因某學生被起外號引發的霸凌事件。三是關系霸凌行為。此種霸凌行為同前述霸凌行為的不同之處在于前兩種霸凌行為具有顯性特質,而此種霸凌行為具有隱性特質,在實踐中通常表現為行為人發動周邊人群對相對人實施孤立,造成相對人在班級或校園中處于被漠視的“隱形人”地位,如2016年3月,安徽省黃山市田家炳實驗中學的女生被下春藥事件。在該起事件發生后,該女生受到班級同學的集體孤立。四是網絡霸凌行為。此種霸凌行為表現為行為人依托自媒體、互聯網等向相對人發送恐嚇、侮辱信息,進而造成行為人產生不安全感,如2015年四川樂至的女生被拍裸照上傳視頻事件。五是性霸凌行為。此種霸凌行為與性侵害行為不同,多表現為行為人采取肢體攻擊、言語歧視等方式,對相對人的性別特征、性取向等進行攻擊或威脅。[5]就后兩種行為而言,其與前三種霸凌行為存在交叉的可能,即在后兩種霸凌行為中,前三種行為多以輔助形態存在。
二、現階段我國校園霸凌行為規制現狀
霸凌行為之所以頻發于校園之中,是因為現行的校園霸凌行為規制手段存在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校園管理者對霸凌行為缺乏認知
在面對霸凌行為時,一些學校管理者包括部分教師或出于學校維系聲望的考量,或出于避免自身績效受到影響的考量,均對此行為表現出輕視或者淡化處理的態度,如2016年12月,北京中關村二小發生的 “向廁所內其他同學投擲垃圾筐”事件。在該起事件中,中關村二小給出的官方回應認為當事學生之間關系正常,并不構成校園欺凌或校園暴力。由此可見,校方做出的這一回應表現出國內部分學校管理者在面對校園霸凌行為時的態度,即將此類行為簡單地歸結為未成年人之間慣常出現的嬉鬧、玩笑行為,進而在問題出現后置若罔聞,無法實現對霸凌行為相對人的保護。這種做法是由于學校管理者對發生于未成年人之間的霸凌行為采取習慣性的漠視態度,缺乏認知,無形之中縱容了校園霸凌行為。
(二)針對校園霸凌行為的規制手段多以思政教育為主
此種規制方式注重實現對行為人價值觀與行為范式的重塑與正向引導,從作用屬性層面來看,乃是立足于道德倫理教化層面的調整。[6]盡管此種方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使一部分行為人受到思想觸動,進而有意識地調整自身行為使之合乎規范。然而,現階段我國部分學校在思政教育踐行方面與有效性方面難以盡如人意,如在教育內容方面過于因循守舊,內容同社會發展實踐相脫節,難以真正喚起學生的價值認同;在教育方式上未能實現同新媒體技術的結合,多遵循傳統的教化方式,如主題班會、講座以及個別談話等。這些教育方式對于在信息時代成長起來的未成年人而言缺乏吸引力,因而在教育方式與形式上不足以達成預期的教育目標。
(三)相關政策有待完善
從現行旨在規制霸凌行為的相關政策來看,主要以《關于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和《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為主,從這兩份文件針對校園欺凌與校園暴力行為所提及的相關意見來看,《通知》和《意見》指明了針對校園欺凌與暴力行為應當借助常規化的思想品德教育實現源頭預防,嚴格依法依規實現對校園欺凌與暴力行為的整治。以《通知》為例,其提及了校園專項治理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2016年4月-7月)和第二階段(2016年9月-12月),第一階段以實施組織部署為內容,第二階段以普查各地落實情況為內容。回顧2016年多起已經出現在媒體上的校園霸凌行為發生的時間節點,部分事件發生的時間正是處于《通知》部署階段,而且不包括未被報道的霸凌事件。由此可見,依托政策方式實現對校園霸凌行為的規制,其效果較為有限。同時,依托政策方式實現對校園霸凌行為的規制,難免有“運動式”規制之嫌,一旦輿情過后,公眾關注度下降,便極易出現相關政策關注度被新的政策所取代,先前的政策被擱置一旁的尷尬局面。此外,從《通知》和《意見》的內容來看,缺少細化的操作細則,因而會出現政策執行過程中“走樣”現象。正如《意見》中提到的:“由于在落實主體責任、健全制度措施、實施教育懲戒、形成工作合力等方面還存在薄弱環節”,因此,這亦是政策落實中易于出現執行困難、落實不到位的原因。
(四)現行法律規制方式存在不足
從目前我國的法律體系來看,涉及對霸凌行為規制的法律主要包括《刑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侵權責任法》和《治安管理處罰法》。然而,我國法律對于刑事責任年齡的界定卻成為規制校園霸凌行為的短板,即不滿14周歲的人完全不負刑事責任,而年齡在14周歲以上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只在觸犯“八大重罪”時才承擔刑事責任,這就導致《刑法》本應具有的震懾功能與預防功能在大多數校園霸凌行為面前,因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年齡問題而沒有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從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來看,其旨在保護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因而表現出“重視保護、輕視懲戒”的立法傾向。我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將未成年人的霸凌行為定義為不良行為,并指出不良行為是尚不夠刑事處罰的違法行為,無形中降低了對霸凌行為的震懾性。我國《侵權責任法》作為民事法律之一,對侵權行為調控的操作性均是通過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來實現的,但現實中一些霸凌行為人的家庭狀況較為優越,此種責任擔責方式亦無法實現對極易可能反復發生的校園霸凌行為進行有效規制。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亦存在規制對象年齡的問題,如2016年7月河北省邢臺市隆堯縣初一學生被打事件。家長報警后,當地公安機關以行為人未滿14周歲為由,出具了《不予行政處罰決定書》。從實際情況來看,霸凌行為在國內中小學校園中的發生頻次遠多于高等院校,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中小學學生的心智尚處于不成熟期,其社會規則意識并未形成,同時法律規制方式的失位也為校園霸凌行為提供了土壤。
三、國外校園霸凌行為法律規制現狀
(一)美國對校園霸凌行為的法律規制
目前,美國各州均制定了旨在規制校園霸凌行為的法律,從而在立法層面實現了對霸凌行為的有效預防與震懾。在美國的五十一個州中,第一部反霸凌法在佐治亞州誕生,該州于上世紀90年代末在全美最先通過反霸凌法,而蒙大拿州在制定反霸凌立法方面最晚,該州于2015年通過反霸凌法。作為一個聯邦制國家,美國各州均有著獨立的立法權限,因而從反霸凌法案的內容來看,各州法案具備顯著的異質性,但各州反霸凌法案的共同點在于,均通過法律規則的明確指引,細化了校園霸凌行為類型,同時還規定了對不同霸凌行為的應對處置措施。即便是霸凌行為人僅僅向相對人進行了言語上的侮辱,亦能夠在反霸凌法案中找到與之相應的懲罰性條款。同時,按照各州制定出臺的反霸凌法案的內容,各州的學校(包括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均應當制定明確的、旨在規避校園霸凌行為發生的校規。在所有州中,新澤西州的反霸凌法案最為嚴格。該州法案規定,州內任何一所學校均應當上報任意一起霸凌事件,由上級部門按照霸凌行為的施害程度對學校加以考核。州內任何一所學校都應當制定應對校園霸凌事件的預案,管理者與教師必須對霸凌行為進行干預。同時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大多數州將不滿7周歲界定為無刑事責任能力,7周歲到14周歲之間且無充分證據證明下,亦為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如2012年美國發生的10歲兒童殺人案,被告在事發后被刑拘。由此可見,美國大多數州在刑事責任年齡界定下限方面已經注意到觸及低齡未成年人犯罪問題。[7]
(二)日本對校園霸凌行為的法律規制
2011年,日本滋賀縣大津市13歲男生因遭受校園霸凌行為而自殺,該事件正式被公眾所知悉則是在2012年,之所以在事件發生一年后才遲延報道,是因為當事人學校以及教育部門的刻意隱瞞。這一事件被報道之后,日本社會為之嘩然,日本國會也針對校園霸凌行為積極進行立法。2013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了《霸凌防止對策推進法》,該法案的具體內容包括:政府必須制定規制霸凌政策、各地應當組建“霸凌問題應對與聯絡協議會”、學校應當制定校園霸凌防治方案,在霸凌行為構成犯罪時,學校必須配合警署開展調查工作等。2103年10月,日本政府出臺了《國家霸凌防止基本方針》,明確了霸凌行為的具體應對策略以及其它相關事項。[8]
(三)英國對校園霸凌行為的法律規制
英國在規制校園霸凌行為方面創設了完備的法律體系,如在不同年度制定教育法案以及出臺《學校標準架構法》等法律文件。1993年出臺的教育法案明確地將校園霸凌行為界定為實施霸凌行為的學生所作出的偏差行為。1996年出臺的教育法案則明確了作為實施霸凌行為學生的監護人的法律責任。2002年出臺的教育法案賦予了教師具有對霸凌行為人的管教權限,賦予了校長對一學年內霸凌行為人的停學與退學權限。《學校標準架構法》《教育及監督法》以及《英國教師工作條件及待遇法案》中對校管會、校長、教師在預防和杜絕校園霸凌行為方面的義務作出了明確的界定。此外,從校園霸凌行為的法律規制程序方面來看,相關立法規定了旨在干預校園霸凌行為的各類懲戒措施,同時,為保障受懲戒對象的權益,允許其進行申訴和上訴,并通過邀請專業人士參與的方式,確保了懲戒程序的公正性與中立性。[9]
(四)德國對校園霸凌行為的法律規制
2015年,《同學的夢魘》一文見諸于《南德意志報》,文中主人公——11歲的女孩莎拉在經受了十四周的校園霸凌行為攻擊之后,發生了應激性反應,從而對校園生活產生了恐懼。面對校園霸凌行為,為避免下一個莎拉的出現,德國的部分州政府在州內的各個學校均配備了專職警務人員,由其負責為校園內的學生提供安全保護。同時,各州政府賦予了校方特定的權限,允許校方將被學校記過處分超過兩次的學生移送至“不良少年管教部門”予以管教。另外,各州政府要求州內學校必須安裝警報裝置,在學生遭遇霸凌行為侵害時,可以通過警報裝置進行報警。面對校園霸凌行為的頻發,德國所有的州基本上都開設了旨在防范校園霸凌行為的專業網站,以便為遇到此類侵害行為的受害學生及其家長提供幫助。從立法規制層面來看,德國于1974年制定并出臺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少年法院法》,該法于2000年重新修訂,現已成為規制校園霸凌行為的重要法律依據,如其中針對校園霸凌行為的懲戒措施包括:警告、規定義務、少年禁閉三種類型。而這些懲戒措施旨在使行為人意識到其自身行為的違法性,同時亦無需對其施以刑罰規制時加以采用。
四、對我國校園霸凌行為進行法律規制的構想
筆者認為,主流觀點所認同和倡導的道德倫理教化方式在當前我國校園霸凌行為層出不窮的情況下,難以達到預期的目標。原因在于,道德倫理教化方式是通過對受教育對象長期施加正向價值觀引導,使其在潛移默化中實現對正向價值的認同,進而有意識地約束和規范自身行為。而校園霸凌行為的頻發意味著當前對于此種行為的規制刻不容緩,因此筆者的構想是:立法機關應結合當前校園霸凌行為的特點,對現行法律進行有針對性的修訂,這樣,才能改變我國校園霸凌行為立法規制落后的現狀,進而依托對現行法律的修訂與完善,實現對校園霸凌行為的有效規制,從而最大程度地還未成年人健康的成長環境。
(一)對校園霸凌行為進行明確定性
通過對校園霸凌行為給予法律層面的明確定性,使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以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為例,之所以有人將之戲稱為“未成年人犯罪保護法”,是因為該法在法律規范中存在無法回避的邏輯弊病:在校園霸凌事件中,霸凌行為人與霸凌行為相對人均為未成年人,而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立法本意無形中對霸凌行為人擔責創設了寬松的條件,即該法突出了對作為霸凌行為人的未成年人寬松處理的同時,也造成了對受到侵害的霸凌行為相對人權益保護的無視。有鑒于此,立法機關應當考慮在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以及《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對校園霸凌行為進行嚴格的定義,并結合對霸凌行為的定義,制定與之相匹配的懲治規范。即通過相關法律對校園霸凌行為進行定性,實現對以往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過于注重保護而忽略懲治的立法理念的糾偏。
(二)創設保護處分制度
保護處分制度是少年司法發達國家所創設的一項旨在規制霸凌行為的司法制度,該制度實現了保護性與強制性的結合,即針對霸凌行為人在以保護為前提的基礎上,實施強制性教育矯正,以達到規制目的。從保護處分所涉及的對象范圍來看,其涵蓋了觸犯刑律的未成年人、觸犯刑律但因年齡限制不承擔刑責以及實施違法行為日后可能實施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此種制度的具體擔責方式涵蓋了沒收犯罪工具、沒收違法所得、訓誡、責令監護人管教、罰金、緩刑等措施。立法機關應當參照這一成熟的立法范例,增設強制性的非拘禁校園霸凌行為人擔責方式,具體包括:司法機關負責對霸凌行為人進行訓誡,并責令其向霸凌行為相對人道歉,告誡其日后如有再犯行為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同時,由司法機關進行訓誡,亦能夠凸顯訓誡的權威性和震懾力,使霸凌行為人及其監護人均受到法律威嚴的觸動。基于確保校園霸凌行為規制效果的考量,司法機關應當要求霸凌行為人的監護人繳納保證金;對經告誡后仍實施霸凌行為的未成年人,司法機關應當啟動委托監護,將其移送到教養機構。此外,為避免霸凌行為人日后走上社會受到負面影響,司法機關應當重視對校園霸凌行為人的保護,具體應當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一是立法機關應當出臺相應的法律規范,要求校園霸凌行為人在節假日期間在監護人陪同下前往教養機構參加教育輔導。二是立法機關應當制定適用于霸凌行為人的緩刑措施,以便通過緩刑觀察期實現對其表現的監控。
(三)刑事責任年齡應適當下調
如前文所述,我國現行《刑法》對于刑事責任年齡的界定無形中使不滿14周歲的校園霸凌行為人實現了對刑事責任的規避,考慮到現階段國內校園霸凌行為呈現出低齡化的發展趨勢,因而立法機關應當考慮適當下調刑事責任年齡,可以將刑事責任年齡調整為10周歲以上到不滿16周歲之間,如此能夠依托刑法的震懾力實現對校園霸凌行為的效度化規制。
除前述法律規制措施之外,立法機關亦應當積極探索校園警察制度,以便在學校層面的霸凌行為干預之外,為霸凌行為相對人提供學校之外的行政保護,進而實現保護層級的立體化。
校園霸凌行為在我國部分校園一直長期存在,然而受社會主流認知模式的影響以及現行法律對這一行為規制的缺位,導致此種給受害者身體與精神帶來難以挽回戕害的惡性行為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整治。每一起校園霸凌行為發生且見諸媒體之后,社會各界便會對這一行為大加抨擊,輿論亦會甚囂塵上,然則一俟輿情平息,該次行為造成的悲劇便會被公眾逐漸遺忘,直至下一次校園霸凌事件發生。這一現象之所以發生,在于立法層面對校園霸凌行為的調整缺失與規制失位,因而輿論介入予以外部施壓成為替代性手段。考慮到當下國內校園霸凌行為的頻發,而以往的整治模式收效甚微,立法機關應當借由立法手段實現對此種行為的有效震懾,進而通過法律的規范性調整功能使之得以規制,從而確保校園秩序得以維系,使居于其中的學生的人身權利得以保障。
[1]劉宏森.資源及其整合:霸凌和反霸凌的關鍵[J].青年學報,2015,(04).
[2]干逸曼,朱家明,.杜曼婷,.楊康玲.有效抑制校園霸凌事件發生的分析與對策 [J].齊齊哈爾大學學報 (自然科學版),2017,(02).
[3]劉向寧.校園霸凌未成年行為人的法律責任淺析[J].青年學報,2015,(04).
[4]張國平.校園霸凌的社會學分析[J].當代青年研究,2011,(08).
[5]游曉琳.芻議中職學校校園霸凌[J].職教通訊,2015,(28).
[6]楊立新,陶盈.校園欺凌行為的侵權責任研究[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08).
[7]孫曉冰,柳海民.理性認知校園霸凌:從校園暴力到校園霸凌[J].教育理論與實踐,2015,(31).
[8]王蘇雅.德國:驅散校園霸凌的夢魘[J].上海教育,.2015,(35).
[9]楊軍,王學棟.英國反校園霸凌之經驗與啟示[J].長春教育學院學報,2016,(08).
(責任編輯:苗政軍)
On Legal Regulation Route of Campus Bullying Behavior
Teng Fei
In recent years,the school bullying events are frequently occurred in public view,the body harm and psychological trauma caused by the bullying behaviors on victims has become the center of public attention.In this paper,it takes the definition of bullying connotation and features analysis as the starting point,combined with the situation of campus bullying and bullying behavior regulation at Chinese present stage,proposing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bullying conception,so a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renovating the campus bullying behaviors in the next phase.
campus bullying behavior;legal regulation;regulation means
D922.16
A
1007-8207(2017)08-0075-07
2017-04-10
滕飛 (1979—),男,吉林長春人,吉林省經濟管理干部學院思想政治理論教學部副教授,法學碩士,研究方向為法哲學、法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