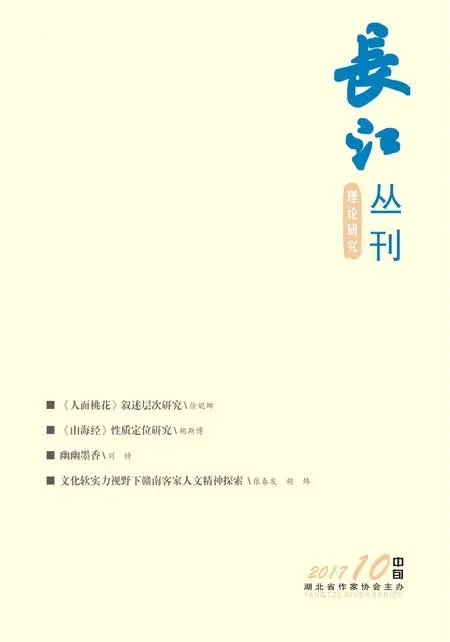淺談修辭意識下的實用文本翻譯
陳舒彥
淺談修辭意識下的實用文本翻譯
陳舒彥
文章從受眾中心,話語建構和美學手段三個方面探討翻譯修辭觀對實用文本翻譯的指導作用,表明了當代西方修辭理論“新修辭”的引入為重新認識和解讀當代翻譯話語和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
實用翻譯 修辭意識 受眾中心 話語建構 美學手段
一、前言
在早期傳統的翻譯理論中,翻譯研究僅局限于實現源語與譯語的等值替換,對語境和文化因素考慮較少。對于此,韋努蒂[1]提出批評,翻譯研究因此淪為建構一般理論和描述文本特征與策略的研究,與當代的文化發展和討論分離開,而這些恰恰賦予了翻譯重要的意義。翻譯不僅僅是將文本從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而是一種交際活動,在這一過程中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碰撞,進而創造出新的視角和價值。因此,翻譯面對的不是單純的文本,而是現實中的受眾,不同的文化群體。如何處理譯者,文本與受眾的關系,將文本中話語的力量有效傳遞,是當今翻譯理論與實踐需要考慮的問題。“而強調言辭以受眾為中心、注重話語修辭力量、注重精心構筑話語以有效影響受眾的新修辭,可以很好地幫助我們提高這方面的認識”。
二、修辭意識對實用翻譯的指導
(一)以受眾為中心
受眾中心是新修辭理論中的一個核心理念,源自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說:“演說者不僅必須考慮如何使他的演說能證明論點,使人信服,還必須顯示他具有某種品質,懂得怎樣使判斷者處于某種心情”。同樣,作為翻譯產品的消費者,受眾也是評價翻譯實踐是否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只有滿足受眾的需求,獲取受眾的認同,翻譯才實現了其交際的目的。“哈提姆從交際理論的角度提出,翻譯策略的選擇受許多因素的制約。其中,讀者及其參與程度就是非常重要的制約因素。受眾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哪種翻譯策略最為合適”。
而受眾也不是一味被動地接收信息,“正如說者(即修辭者)總是根據既定的修辭目的和他所觀察的互動態勢對修辭者和受眾進行想象和構筑,作為自己進行‘修辭發明’的基本出發點,聽者也是一個主動的參與者,也在理解、想象和構筑自己與修辭者的關系,并根據自己對這一變動著的關系的感受,解讀逐步展開的修辭文本,對其做出反應”。因此,我們在翻譯的實踐中要考慮預期受眾的需求,興趣和接受能力。
(二)根據語境建構話語
語境可分為語言性語境和非語言性語境。語言性語境通常指文本自身所處的語言環境,包括搭配、上下文、語義之間的聯系等;非語言性語境指時間、空間、題材、讀者對象及相關的社會文化背景等。語境意識在翻譯研究中并不少見,但在“新修辭”的框架下,“翻譯中的語境研究、語境解讀和語境應對不能僅局限于對文本內外的背景環境進行靜態解析”,而應“認真思考譯文希望在受眾心中產生什么效果,如何根據相關制約因素,決定話語建構方式,實現預期效果”。
翻譯既是一種跨文化交際,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就應考慮譯文在“譯語文化環境中預期達到的一種或幾種交際功能”。交際目的是非語言語境中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由萊斯,費米爾和諾德等人提出的“功能目的論”主張翻譯方法和策略是由譯文預期目的或功能決定的。不同語篇有不同的交際目的,譯者需要根據語篇的交際目的來預期受眾的需求,進而選擇得體的話語建構方式。
信息類的實用語篇,其交際目的在于為受眾提供實質信息。
(三)詩意的表達
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中提出顧及受眾無益的觀點,認為文學作品的本質是“那些深奧難測、神秘難解、充滿‘詩意’的成分”,如果考慮受眾因素,勢必會把翻譯看作傳遞信息的工作。這一觀點雖然有一定的合理性,文學構建的話語或許更多是作者個人的聲音,然而受眾作為修辭話語的主體之一,也在構筑自己對作者,對文本的理解。同時,考慮受眾并不意味著犧牲“詩意”,修辭意識下的翻譯能夠激發受眾的美感,滿足受眾對美感的追求。
此外,并非只有文學語篇才需要建構文學性的話語,實用語篇也可以實現詩意的表達。“在當代西方語境中,修辭手段是修辭研究中事關美學的一部分,與提高話語的美學表達效果有關”。[2]在實用語篇翻譯中根據語境適當運用修辭手段能夠給予受眾形象生動的感受,使譯文更具創造性。
三、結語
從“語言學轉向”,解構主義,功能翻譯理論,文學翻譯理論,描寫規范,再到“文化轉向”,翻譯研究界已經意識到語言和翻譯是體現和推動社會的力量。“而修辭正是語言力量及其運作的體現”。當代西方修辭理論“新修辭”的引入為重新認識和解讀當代翻譯話語和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帶著修辭意識使用語言,則能使語言發揮更大的力量,更有效地對受眾產生修辭者希望產生的預期影響。對語言修辭力量的充分認識,對翻譯和翻譯者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2]“新修辭”指導下的實用翻譯關注受眾中心,根據不同語境考慮受眾的需求建構語篇話語,以實現交際目的。在傳遞信息的同時,適當運用美學手段,可以實現既“實用”又“詩意”的翻譯效果。
[1]陳小慰.翻譯與修辭新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3.
[2]陳小慰.新編實用翻譯教程[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
福州大學)
陳舒彥(1993-),女,漳州人,福州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