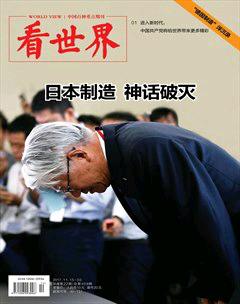美國農(nóng)村也流行“大學無用論”
龔燦
農(nóng)村學生上大學比例最低
當達斯汀·戈登就讀的高中邀請高年級學生參加各大高等院校的招生見面會時,只有少數(shù)學生出席。一些學生對于繼續(xù)深造的前景深感擔憂,戈登說:“我覺得,一些學生來參加見面會只是為了想翹課。”
戈登生活在愛荷華州南部人煙稀少的農(nóng)村地區(qū),在那里,“人們沒有動力去上大學。他們完成高中學業(yè),就認為自己需要上的學已經(jīng)足夠了,反正很快就能在家庭農(nóng)場、雞蛋包裝廠、滑輪傳送帶制造廠或是卡車運輸隊找到一份工作。”
如今這種心態(tài)的變化形成了這樣一個事實,過去對于誰應該去上大學的激烈爭議,常常聚焦在低收入非白人學生身上,如今的現(xiàn)實卻是:美國高中畢業(yè)生上大學比例最低的地區(qū)其實是在白人居多的農(nóng)村。
“理解和解決這個問題對我們未來的發(fā)展至關重要,不僅是關乎就業(yè),更多是為了讓孩子們覺得他們有價值,能獲得成功,而不是讓他們深感失落以及被人遺忘。”肯塔基峽谷教育合作組織的執(zhí)行總監(jiān)杰夫·霍金斯表示。他的工作就是鼓勵和支持那些在煤礦工作的學生繼續(xù)上大學。
農(nóng)村孩子不愿意上大學,并不是說農(nóng)村學生的學習成績不夠好。美國教育部的報告顯示,農(nóng)村學生在全美國教育進展評估方面的成績比城市學生要好,高中畢業(yè)率也高于全美國平均水平。戈登所在的愛荷華萊諾克斯區(qū)域高中,高中畢業(yè)率通常能達到或接近100%。
美國全國學生資料庫顯示,即使是來自農(nóng)村的家庭富裕的白人學生,上大學的比例也會低于富庶的白人城市及郊區(qū)學生。數(shù)據(jù)顯示,農(nóng)村白人學生上大學的比例是61%,城市白人學生是72%,郊區(qū)是74%。
總的來說,農(nóng)村高中畢業(yè)生(不論種族和收入差異)繼續(xù)上大學深造的只有59%,這一比例低于城市62%以及郊區(qū)67%的比例。根據(jù)美國全國教育統(tǒng)計中心的數(shù)據(jù),在18歲至24歲年齡段中,有42%的人接受了大學教育,其中只有29%的學生來自農(nóng)村,相比之下,來自城市的大學生錄取率接近48%。
而且在大學教育中,考慮到教育成本和畢業(yè)前景,47%的農(nóng)村學生會選擇兩年制的高等院校,相比之下城市學生只有38%的人會選擇兩年制院校。那些還在上高中的農(nóng)村學生也沒有很大的意愿去私立大學或是很受歡迎的四年制大學。在四年制的伊利諾伊大學,過去20年來農(nóng)村學生人數(shù)急劇下降。
導致這一情況出現(xiàn)的原因相當復雜,從區(qū)域經(jīng)濟競爭力到不斷擴大的政治分歧等方方面面。愛荷華大學農(nóng)村政策研究所所長查爾斯·弗魯哈特認為很大部分原因與當?shù)貧v史傳統(tǒng)有關,這些農(nóng)村學生從小就生活在一個靠在農(nóng)場、礦場和林場工作就能獲得體面生活的地方,沒有人需要大學教育。“你也可以去上農(nóng)業(yè)學校,但是沒有必要。”弗魯哈特來自俄亥俄州阿巴拉契亞山腳下一個五代都是農(nóng)民的家庭,“你都能找到工作了,為什么還要去上大學?”
但是隨著美國制造業(yè)衰退,農(nóng)業(yè)工作越來越自動化,礦場關門,農(nóng)村地區(qū)的工作機會越來越少了。弗魯哈特表示,當就業(yè)機會減少,隨之而來的絕望感也讓農(nóng)村學生失去了去公立大學或是技術學院實地考察的興趣,對高校招生人員來高中招生也不感興趣。
他們的父母也面臨同樣的困擾。皮尤研究中心的調(diào)查顯示,三分之一的農(nóng)村白人悲觀地認為,他們的孩子將來長大之后的生活水準將比他們還要低,這種焦慮要高于居住在城市(23%)或郊區(qū)(28%)的家長。

達斯汀·戈登
這種不滿情緒廣泛蔓延,在去年總統(tǒng)大選中,農(nóng)村選民支持特朗普的選票占到了62%,相比之下支持希拉里的農(nóng)村選民只有34%。但是在城市,特朗普的支持者則明顯要少于希拉里的支持者。
達斯汀·戈登并沒有隨著這股潮流走。雖然他的父母沒有上過大學,但他們堅持讓戈登繼續(xù)上學。“回想我的高中同學,那些上大學的孩子,他們的父母要么有優(yōu)越的工作,要么都曾上過大學。”
農(nóng)村學生面臨多重挑戰(zhàn)
由于歷史原因,美國農(nóng)村地區(qū)的人口本來就少于城市和郊區(qū)。美國農(nóng)業(yè)部下屬的經(jīng)濟研究局數(shù)據(jù)顯示,在農(nóng)村25歲以上的成年人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擁有大學學歷,而全美平均水平接近50%。
“因為我們沒有多樣化的職業(yè)可以讓年輕人去考察去實踐,在他們生活的社區(qū)也沒有出現(xiàn)能讓他們仰望的榜樣,他們像是被推到了這樣狹隘的境地:‘我能選擇的就是做礦工或者收銀員或醫(yī)療看護。因為他們能了解到的職業(yè)僅限于這些,像律師、醫(yī)生、天體物理學家等精英職業(yè),他們幾乎只能在電視上看到。”霍斯金說。
不管各地農(nóng)村存在多大的差異,它們面臨的挑戰(zhàn)其實是相似的。無論是在人口只有3萬的田納西州馬里恩縣,還是在人口有89萬的加州克恩縣,廣袤的農(nóng)村地區(qū)都面臨著毒品泛濫、心理健康缺陷、貧窮、高速網(wǎng)絡匱乏、教育資源緊缺等問題。
在一些偏遠的農(nóng)村地區(qū),連高中老師都招不滿。馬里恩縣坐落在田納西、阿拉巴馬和佐治亞三州交界地帶,這里的學校招不到足夠的數(shù)學老師,其他科目的老師招聘也成難題。“沒有應聘者愿意來這里。”馬里恩縣學校督導格里菲斯說,“我們縣三所高中只有一名物理老師。”
在農(nóng)村地區(qū)普遍存在這樣一種疑問,上大學究竟值得不值得。皮尤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相比于人口較多的地區(qū),農(nóng)村白人學生中相信大學能提供必要技能的只有71%,在城市這一比例是82%,郊區(qū)學生則是84%。
“這已經(jīng)不單單是一個教育現(xiàn)象,而是成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弗魯哈特認為,去勸說一名農(nóng)村學生一定要上大學,就好比“建議孩子們不要做我做過的那些事,不要去我曾經(jīng)去過的那些地方,不要珍惜那些我給他們的榮譽,無論他們是要去工廠還是要在早上6點起來開拖拉機。”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霍金斯的方案是鼓勵那些即將升入高等院校的中學生與高校大學生加強聯(lián)系。一些學生可以參加多校聯(lián)合舉辦的創(chuàng)業(yè)大賽,在里面擔任志愿者或是評委。這樣的大賽將各個學校即將上大學的孩子聚集在一起,他們借由這種機會結下人緣,然后等到進入大學之后就能彼此幫助扶持。美國國家學生交流中心的報告顯示,類似的互助體系非常重要,因為那些農(nóng)村學生比城市和郊區(qū)學生更容易在大一和大二階段退學。
參與了霍金斯的教育互助體系的派克縣,2015年秋季有618名高中畢業(yè)生升入大學,但是次年春季學期,只有350名學生回到大學校園,到了第二個學年就只剩281人了。“所以基本上我們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孩子。”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是成本問題。對另外一些人而言,可能更多是一種文化的沖擊。“他們高中畢業(yè)時整個畢業(yè)年級也就八九十個孩子,進入大學校園后,他們發(fā)現(xiàn)身邊的同齡人就有2萬。”霍金斯說,農(nóng)村學生從小在一個很熟悉的環(huán)境長大,身邊的鄰居都是熟人,大家可以一起去教堂,一起去逛超市,但是進入大學之后,一切都是陌生的。
戈登最初是在母親工作的社區(qū)學院讀書,后來轉(zhuǎn)學到了愛荷華大學,他震驚地發(fā)現(xiàn)講座課堂上的學生比他家鄉(xiāng)夏普斯堡的人口還要多。夏普斯堡的居民只有89人。在他就讀的當?shù)貙W校,12個年級的學生全部都在一棟教學樓里上課,他畢業(yè)時班上只有29名學生。
“在農(nóng)村小地方,大家都知道你是誰。”戈登說他在高中橄欖球隊擔任四分衛(wèi),打棒球,還玩田徑。來到愛荷華大學后,他發(fā)現(xiàn)“在學校一個人都不認識。那些來自芝加哥和其他大地方的學生自成一派,看著真叫人嫉妒。這所學校33334名學生來自全美50個州以及全球114個國家和地區(qū),一個來自偏遠鄉(xiāng)下的年輕人,想要在這里結識人非常難。”

當達斯汀·戈登走進教室,發(fā)現(xiàn)教室里的學生比他家鄉(xiāng)夏普斯堡的人還要多
從熟悉的小社區(qū)環(huán)境進入一所龐大如城市規(guī)模的大學校園,會讓那些來自小城鎮(zhèn)和農(nóng)村地區(qū)的學生感到恐慌和不適應,那種隱形的刻板印象更是讓他們難以承受。弗魯哈特認為,美國大學校園里對農(nóng)村學生的歧視很常見,“這是美國最后一種可以容忍的偏見。農(nóng)村的孩子并不笨,他們也不缺乏見識。他們心眼亮著呢。”
如何提高農(nóng)村學生上大學的比例?一些州已經(jīng)展開了實踐。包括愛荷華州在內(nèi)的一些以傳統(tǒng)經(jīng)濟為主的州正在進行經(jīng)濟轉(zhuǎn)型,轉(zhuǎn)向信息技術、風電、醫(yī)療保健等需要高等教育求職者的行業(yè)。
在加州,廣袤的農(nóng)村地區(qū)擁有加州27%的高中畢業(yè)生,但只有12%的學生擁有學士學位。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新報告指出,到2030年,加州預期將缺少110萬受過大學教育的工人。該報告的主要作者漢斯·約翰遜指出:“區(qū)域差異非常顯著,提高農(nóng)村地區(qū)大學生的比重對加州來說至關重要。”
回到愛荷華州南部,戈登的一個高中好友如今在農(nóng)場工作,另一個同學在其父親的飼養(yǎng)場干活。而在萊諾克斯的雞蛋包裝車間和施肥機制造廠,還有工作機會。
對戈登來說,他并不認為這些工作就很低賤,“但我不愿意做這些。如此長時間的體力勞動,所得報酬又有限,這不值得干下去。”然而他的大部分高中同學以及校隊的隊員們都將留在愛荷華州,沒有機會真正去世界各地看看。
至于他自己,戈登希望能在明年5月畢業(yè)時成為一名財務規(guī)劃師,他也正準備搬到得梅因市。“自從我去愛荷華大學上學之后,就不怎么喜歡回家了。我可不想最后還是得回到萊諾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