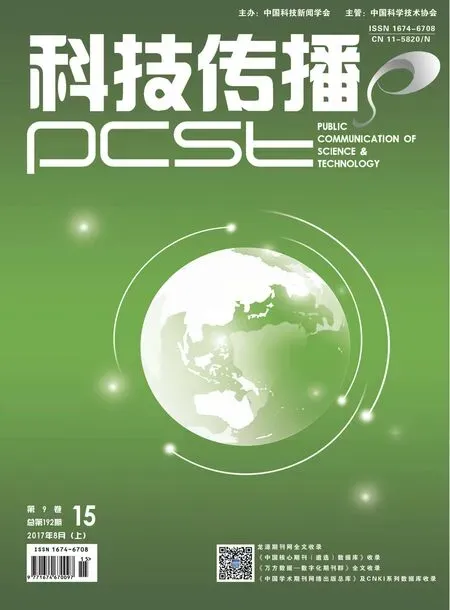信息社會下傳播方式及內(nèi)容變革的思考
——我們?nèi)绾螌Υ齻鞑?/h1>
2017-12-01 00:12:11劉暢
科技傳播 2017年15期
劉 暢
四川音樂學院傳媒學院,四川成都 610050
信息社會下傳播方式及內(nèi)容變革的思考
——我們?nèi)绾螌Υ齻鞑?/p>
劉 暢
四川音樂學院傳媒學院,四川成都 610050
本文從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對傳播載體產(chǎn)生的革命性變革出發(fā),針對現(xiàn)代傳播過程(各類傳播)產(chǎn)生的變革,對信源、受眾及傳播方式及內(nèi)容的影響與變化進行了闡述。討論了自媒體、交互和平臺三者在傳播過程中的實質(zhì)性作用,對傳播變革中的問題進行了分析,提出對數(shù)據(jù)、信息、信源、信息變異等的警示。對未來大數(shù)據(jù)支持下的傳播學的創(chuàng)新和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傳播;自媒體;交互;平臺;大數(shù)據(jù)
信息技術(shù)的飛速發(fā)展給世界帶來的最大影響和促進就是變革。這是全人類和社會進步的彰顯,也是人類對自身生命及生活質(zhì)量的提升。
這種快速的變革是通過科技進步與社會協(xié)定的交合,通過信息技術(shù)與社會的需求,通過人類生活與自我感受的融合而產(chǎn)生了整個世界的變革。其中,信息技術(shù)對傳播的變革產(chǎn)生并給予了極大的促進,突破了傳統(tǒng)傳播學的概念和理念,使傳播媒介(載體)、傳播方式、傳者和受眾在如此巨大的變革中得以升華。
1 媒體技術(shù)與傳播載體的變革
現(xiàn)代傳播學最明顯的變革就是傳播媒介(載體)的變革。
在20世紀,著名傳播學家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提出過“媒介即信息”的相似理論。其含義是: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義的信息,即人類只有在擁有了某種媒介之后,才有可能從事與之相適應(yīng)的傳播和其他社會活動。
傳播媒介的作用可以影響我們理解和思考的習慣,對于社會來說,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信息”不一定是媒體所傳播的內(nèi)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zhì),是它所開創(chuàng)的可能性以及帶來的社會變革。
現(xiàn)代傳播過程的變革具有如下特點:1)數(shù)字技術(shù)促進傳播載體的變革;2)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促進傳播時空的變革;3)自媒體促進傳播方式的變革。
傳統(tǒng)傳播學的理論并沒有(或少有)討論傳播過程的時空問題和時空關(guān)聯(lián)。隨著20世紀后期互聯(lián)網(wǎng)、尤其是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的構(gòu)建和發(fā)展,信息(數(shù)據(jù)及內(nèi)容)的傳播對于傳者和受眾,在時空概念上已經(jīng)感受不到時空的限制,“世界是平的”“信息全球分享”這樣的概念每每出現(xiàn)在傳播學教材和實例中。
信息不再有時間的延遲和空間的局限(除非人為控制),迫使媒體和媒體人感受到激烈的競爭態(tài)勢和傳播壓力。信息的擁有、產(chǎn)生和傳播的優(yōu)勢和主動權(quán)就不僅僅是專業(yè)媒體的獨有權(quán)力,而向整個社會開放了。
自媒體(We Media)的出現(xiàn),以“公民媒體”“公眾媒體”或“個人媒體”的方式,促使傳播者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和自主化,并以數(shù)字化、電子化、網(wǎng)絡(luò)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數(shù)或者特定的單個人傳遞規(guī)范性及非規(guī)范性信息。自媒體的實現(xiàn)借助了信息技術(shù)和工具,如:個人電腦、平板電腦、智能手機等。也借助了互聯(lián)網(wǎng)(含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各類平臺,如:博客、微博、微信、論壇/BBS、貼吧、公眾號等網(wǎng)絡(luò)社區(qū)或群落。自媒體時代顛覆了由傳統(tǒng)專業(yè)媒體機構(gòu)主導的信息傳播,推動并形成了由普通大眾主導的信息傳播活動,信息內(nèi)容擴大到圖文聲像的整個領(lǐng)域,促成了傳播領(lǐng)域的一場革命性變革。
2 傳播過程變革的幾個關(guān)鍵點
信息時代,人人都是傳者,人人也都是受眾,每個人既主動,也是被動。
變革同時引發(fā)了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變革有幾個關(guān)鍵點,也正是現(xiàn)代傳播學要討論、研究和對待的問題。
2.1 傳播與受眾的方向變革:對等
眾所周知,在傳統(tǒng)的傳播過程中,“方向”這個概念在傳者和受眾之間一直、或者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單向”的。無論是平面媒體(如:報刊雜志等),還是電子媒體(如:廣播電視等),都是面向受眾的單向傳播。受眾除了被動地接受(接收)到傳播內(nèi)容,通常無法表達自身的感受、意見和評論。這種“單向性”反映在傳播理論中通常被稱為宣傳,傳者與受眾的關(guān)系也通常是固定的。傳者具有專業(yè)性和主動性,而受眾也就僅僅體現(xiàn)為被動地接受。
自媒體的出現(xiàn),打破了這種不公平的格局,新媒體不再有傳者和受者的界限,每個人都是傳者,也即“人人即媒體”,每個人也是受眾(包括原本的傳者)。這樣,傳統(tǒng)傳播學意義上的“受眾”,在信息時代已經(jīng)被另外一個詞匯“用戶(User)”所代替。這種“對等”關(guān)系,更加期望社會文明和公民素質(zhì)達到一個較高程度,這是國家發(fā)展、社會進步的必然趨勢。
2.2 傳播變革中最大的突破:交互
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促進了“互動”需求,反之也引發(fā)了電子、通信領(lǐng)域中傳輸設(shè)備的“回傳”技術(shù)和裝置的誕生。從早期的電視購物,到后期的視頻電話,從最簡單的“人機交互”一步步進展到“所見即所得”。
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突破并實現(xiàn)了傳播的“交互”過程,既上行下達,又下行上傳。網(wǎng)絡(luò)空間中的“下載(download)”和“上傳(upload)”激發(fā)了“受眾”的廣泛參與,推動了電子郵件(E-mail)的廣泛使用,促進了信息產(chǎn)業(yè)領(lǐng)域人機交互設(shè)備的研發(fā)和推廣。
交互性激發(fā)了大眾傳播的參與性,“交互”這個詞也成為20世紀末最引人入勝和使用最頻繁的詞之一。
2.3 平臺對傳播的重要支撐:共享
當前,人人都擁有且日常攜帶著個人智能終端,如手機和平板電腦等,但它們僅僅還是“終端”,它們所產(chǎn)生和接受的信息仍然需要匯集點和轉(zhuǎn)發(fā)點,這就是我們所談的“平臺(Platform)”。
信息平臺在技術(shù)上是計算機、通信、軟件系統(tǒng)、數(shù)據(jù)庫和應(yīng)用服務(wù)模塊的集成,它支撐著傳播中共享和分享機制的形成。這種基于網(wǎng)絡(luò)(互聯(lián)網(wǎng))、系統(tǒng)(云計算)和信息(大數(shù)據(jù))的平臺形成了信息社會中的“社交網(wǎng)絡(luò)”和“網(wǎng)絡(luò)社區(qū)”。
平臺奠定了交互中的共享與分享,也在調(diào)節(jié)并控制著信息交互。平臺的擁有者具有較大的“權(quán)力”,可以對平臺上交互的內(nèi)容進行管理(監(jiān)控或關(guān)閉)。
共享和分享型的傳播方式促使傳播過程中的傳者和受眾都融合在這個參與、交互、共享、分享的平臺上了。自然,平臺也就承擔了非常重要的責任和支撐。
3 傳播變革中的問題、警示與對策
傳播的方式從單一到多類,從交互到共享,傳播的內(nèi)容及形式從單純文字、語音,拓展到“圖文聲像”“3D融合”、甚至“虛實相間”等,從而導致傳播類別與信息的泛化。在“大眾傳播”的空間世界,傳播者和受眾的關(guān)系也從單一變?yōu)橄鄬Α皩Φ取保蛘弑舜恕叭诤稀薄?/p>
信息的泛化促使傳播工作者對這類傳播學現(xiàn)象和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傳播過程中信息泛化引發(fā)的信息“關(guān)聯(lián)”“延伸”“變異”等對傳播工作者既提出了問題,也給予了警示。
3.1 傳播面臨信源、真實性與法律責任的問題
傳播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傳播內(nèi)容的真實性。
傳播真實原本是依靠傳播者的職業(yè)道德(誠信)和權(quán)威性(公正)來保證的,如果這兩個原則被打破了,或者恣意所為,傳播內(nèi)容就受到極大影響,受眾就處于被欺騙的位置。
在網(wǎng)絡(luò)世界的傳播中,要確定一個“信源”,難度是比較大的,傳播內(nèi)容的真實性也較難得以驗證。那么,“真實”和“信任”的基礎(chǔ)只建立在“私信力”和“公信力”兩者上。前者基于朋友和“熟人”,或者說“信得過”的人,后者則期望政府及公眾媒體的權(quán)威性發(fā)布。由于信息不對稱,故此處公信力的出現(xiàn)對人們確認信源并建立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以自媒體空間的“微信”為例。微信支持的幾種傳播范圍如:1)單一(私聊);2)多維(群聊、朋友圈);3)共享(公眾號)。在這些空間中傳播的信息有“原創(chuàng)”和“轉(zhuǎn)發(fā)”類型,而“轉(zhuǎn)發(fā)”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轉(zhuǎn)發(fā)者對某些傳播內(nèi)容的趨向性或趨同性。轉(zhuǎn)發(fā)過程還可以加上轉(zhuǎn)發(fā)者自身的“評論”,甚至改變“標題”,修改內(nèi)容,增刪文字等。這樣,就會產(chǎn)生信息的變異。更由于轉(zhuǎn)發(fā)產(chǎn)生的循環(huán)效應(yīng),信息變異的可能性會增大,使信源更難以確定,真實性無法追溯。這給那些肆意編造信息的別有用心者提供了一個隱匿的空間。
網(wǎng)絡(luò)世界被稱作“虛擬世界”,網(wǎng)絡(luò)中傳播的信息內(nèi)容也存在真假共存的現(xiàn)象。假信息與謠言的傳播影響,在信息時代其傳播速度、覆蓋空間、受眾范圍、變異程度都是傳統(tǒng)傳播不可比擬的,所造成的影響和結(jié)果也是很難預(yù)料,甚至是不能承受的。加之傳播(轉(zhuǎn)發(fā))中信息的變異(避實就虛、斷章取義、添油加醋、故弄玄虛、肆意篡改等),要達到傳播的真實性,對傳者和受眾(都是“用戶”)的責任要求就更高,而僅靠“文責自負”“謠言止于智者”是不能完全或根本解決問題的,這就必須有法律的制約。
公眾媒體在傳播真實性方面的責任是巨大的。這類媒體的“發(fā)聲”具有導向性,尤其在信息不對稱的時候,是傳播并依賴“公信力”的最佳時候,如果此時“公信力”的“失聲”,無疑會導致信息的混亂,從而放任“變異”信息的泛濫。
3.2 “垃圾”信息引發(fā)社會的強烈關(guān)注
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電子商務(wù)和社交媒體的快速發(fā)展促使數(shù)據(jù)量成指數(shù)增長。據(jù)IDC(國際數(shù)據(jù)集團)的研究報告表明,2020年全球新建和復制的信息量將超過40ZB(40萬億GB)。而目前每天全球互聯(lián)網(wǎng)流量已經(jīng)達到或超過1EB(即10億GB)。人們不知不覺中留下的“數(shù)據(jù)碎片”已經(jīng)滲透到社會經(jīng)濟、大眾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
我們知道,僅僅通過“微信”等社交媒體的“轉(zhuǎn)發(fā)”功能,已不可避免地引發(fā)傳播信息量的巨增,從而導致信息冗余重復,收發(fā)輪番循環(huán)等問題。加上對轉(zhuǎn)發(fā)信息的評論、修改,以及通過傳播“驚爆標簽”、營銷號和“標題黨”等導致的信息變異,使得當前的信息系統(tǒng)、信息存儲和信息分析受到極大壓力,也使網(wǎng)絡(luò)搜索(如Google、百度)引擎承受極大負載。冗余信息大量存在,加上廣告、電商等信息傳播,“垃圾信息”成為信息社會中的另一個大的社會問題。
作為受眾,原本可以有選擇地接收和閱讀,然而,基于交互、共享和推送技術(shù),你不想得到的信息,或者說一些“垃圾信息”也不斷地充斥到個人的信息終端(手機)上,對個人來說不勝其煩,對社會來說資源浪費。
“垃圾信息”的存在和解決給信息工作者和傳播媒體人都提出了新的警示和要求,分別提出了從技術(shù)上、從道德規(guī)范與法律法規(guī)上解決的途徑,新型的智能搜索引擎和智能辨析系統(tǒng)已經(jīng)在網(wǎng)上出現(xiàn),隔離和防范計算機病毒與其他惡意程序的軟件也已經(jīng)日益成熟,“數(shù)據(jù)碎片”的整合和擯棄正日益完善。
3.3 傳播者與受眾“共享”的社會責任與法律責任
基于自媒體的傳播,借助“微信”一類交互和共享平臺,信息會被無限制地放大,其變異也會無限制地放大,成為真正的“廣播”。對于個體而言,涉及的是公民隱私,對于社會而言,涉及的是信息殺手,如:“網(wǎng)絡(luò)暴力”。
在網(wǎng)絡(luò)交互平臺上,朋友圈中的“網(wǎng)曬”是自身生活、工作、家庭、旅游等高興之事、喜愛之物等放到網(wǎng)上與人分享、展示生活,由他人評說,網(wǎng)友之間交流互動,該過程是一個認識自己、聽取意見、學習他人的過程,也已成為一種個人尋找群體的聯(lián)絡(luò)方式。
但如果公民自身沒有或缺乏“公民隱私權(quán)”的意識,個人信息的泄漏會給自身或者社會帶來不少問題,近年來發(fā)生的各類網(wǎng)絡(luò)詐騙幾乎都涉及公民隱私的泄漏,不法分子利用信息的傳播和共享,實施有針對性的犯罪。
“網(wǎng)絡(luò)暴力”是另一種涉及“公民隱私權(quán)”的輿論力量。例如,“網(wǎng)搜”中的所謂“人肉搜索”在網(wǎng)絡(luò)暴力中就顯得尤為畸形。這種針對個人隱私的獵奇、搜索、暴露、宣泄和炒作,通過網(wǎng)絡(luò)傳播的放大和轉(zhuǎn)發(fā),引發(fā)指數(shù)式的信息爆發(fā)。人們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會對當事人進行指責,攻擊,甚至謾罵,最后形成一股“吃人”的力量(心理和社會壓力),殺掉那個輿論中心的受害者。2012年曾經(jīng)上演過陳凱歌拍攝的一部叫《搜索》的電影,講述了一個被網(wǎng)絡(luò)暴力害死的清白姑娘的故事。所以,網(wǎng)絡(luò)暴力完全違背了道德,侵犯了個人隱私權(quán),還違反了法律。
令人欣慰的是,2017年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首次就打擊侵犯個人信息犯罪出臺了司法解釋,對于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嚴打泄露個人信息等社會關(guān)注焦點有了明確規(guī)定,對即將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起到先驅(qū)的作用。
綜上所述,在“共享”平臺上,傳播者與受眾都必須遵守社會道德,共擔共享社會責任與法律責任。沒有約束的自由不是自由。針對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個人隱私、數(shù)據(jù)權(quán)益、新聞傳播等方面的法律的健全是一個法治社會必須建立的規(guī)則。所以,現(xiàn)代傳播學中研究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傳播與法律的關(guān)聯(lián)。(見作者另文,此處不贅述)
4 基于大數(shù)據(jù)的傳播思考
現(xiàn)代傳播學進展到了“大數(shù)據(jù)”時代,大數(shù)據(jù)是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到現(xiàn)今階段的一種表象或特征。傳播離不開數(shù)據(jù)、離不開信息,而隨著各類傳播媒體的發(fā)展和彼此交融,傳播方式所涉及的交互、共享中關(guān)聯(lián)的信息已經(jīng)是海量信息,而這些數(shù)據(jù)每年都按指數(shù)方式在繼續(xù)增長。現(xiàn)代傳播學面對的是一個數(shù)據(jù)科技(DT)時代,數(shù)據(jù)傳播平臺、網(wǎng)絡(luò)平臺也面對的是各類媒體(自媒體意義上的多媒體融合)的融合。那么,現(xiàn)代傳播學如何對待大數(shù)據(jù),如何基于大數(shù)據(jù)進行現(xiàn)代信息社會意義上的傳播,是我們必須考慮和研究的問題。
大數(shù)據(jù)不僅是數(shù)據(jù)量、數(shù)據(jù)流“巨大”,數(shù)據(jù)的處理也無法用傳統(tǒng)的方式進行,需要一些新的處理模式才能通過信息(數(shù)據(jù))處理,形成更強的決策力、洞察發(fā)現(xiàn)力和流程優(yōu)化能力。傳播方式的變革也需要我們改變傳統(tǒng)傳播過程對數(shù)據(jù)的準備、獲取、分析和傳播。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在《大數(shù)據(jù)時代》一書中舉了許多例證,都是為了說明一個道理:在大數(shù)據(jù)時代已經(jīng)到來的時候要用大數(shù)據(jù)思維去發(fā)掘大數(shù)據(jù)的潛在價值。
基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傳播要考慮的是:海量的數(shù)據(jù)在網(wǎng)上,在數(shù)據(jù)庫間流動,數(shù)據(jù)變得在線了。信息的流向是不可控的,在其傳播過程中,泛化產(chǎn)生了,泛化和變異的信息(數(shù)據(jù))會回流到網(wǎng)絡(luò)(媒體),進行下一輪的傳播(轉(zhuǎn)發(fā))。信息(數(shù)據(jù))是把雙刃劍,在傳播過程中,傳者和受眾都會因此受到正面的和負面的影響。
如何面對大數(shù)據(jù)時代,是現(xiàn)代傳播學和傳播工作者不容回避的問題。限于篇幅,此處不再贅述,請參見作者另文:《大數(shù)據(jù)支撐下的信息傳播》。
5 結(jié)論
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促進傳統(tǒng)的傳播載體產(chǎn)生了革命性的變革,這些變革縮短了傳播時空,改變了傳者與受眾的關(guān)系。互聯(lián)網(wǎng)(含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自媒體的強勢介入,改變了傳統(tǒng)傳播的方向和主流。交互、共享和分享在信息技術(shù)支持下的“個人智能終端”和“公共智能平臺”的支撐下,對現(xiàn)代傳播過程中起到了實質(zhì)性的作用。傳播類型和信息的泛化促使我們對傳播變革中的新問題進行思考和分析,提出對數(shù)據(jù)、信息、信源、信息變異等的警示,使我們對現(xiàn)代傳播學中傳播與法律的關(guān)聯(lián)進行深入思考,對未來大數(shù)據(jù)支持下的傳播學的創(chuàng)新和教育給予更密切的重視和研究。
[1]托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M].何帆,等,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shù)出版社,2006.
[2]代玉梅.自媒體的傳播學解讀[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1(5):4-11.
[3]YOKA網(wǎng).微信:自媒體的“少數(shù)派報告”[EB/OL].2013-05-13.
[4]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大數(shù)據(jù)時代[J].周濤,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G2
A
1674-6708(2017)192-0013-04
劉暢,助教,四川音樂學院傳媒學院,研究方向為新媒體與傳播。
猜你喜歡
用創(chuàng)新表達“連接”受眾傳媒評論(2018年6期)2018-08-29 01:14:40 訂閱信息中華手工(2017年2期)2017-06-06 23:00:31 變革開始了中國工程咨詢(2017年12期)2017-01-31 02:56:40 用心感動受眾新聞傳播(2016年11期)2016-07-10 12:04:01 媒體敘事需要受眾認同新聞傳播(2016年14期)2016-07-10 10:22:51 電視節(jié)目如何做才能更好地吸引受眾新聞傳播(2016年20期)2016-07-10 09:33:31 新媒體將帶來六大變革聲屏世界(2015年5期)2015-02-28 15:19:47 展會信息中外會展(2014年4期)2014-11-27 07:46:46 變革中的戶籍制度四川黨的建設(shè)(2014年9期)2014-08-23 01:33:24 創(chuàng)新IT 賦能變革浙江人大(2014年1期)2014-03-20 16:20:01
劉 暢
四川音樂學院傳媒學院,四川成都 610050
信息社會下傳播方式及內(nèi)容變革的思考
——我們?nèi)绾螌Υ齻鞑?/p>
劉 暢
四川音樂學院傳媒學院,四川成都 610050
本文從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對傳播載體產(chǎn)生的革命性變革出發(fā),針對現(xiàn)代傳播過程(各類傳播)產(chǎn)生的變革,對信源、受眾及傳播方式及內(nèi)容的影響與變化進行了闡述。討論了自媒體、交互和平臺三者在傳播過程中的實質(zhì)性作用,對傳播變革中的問題進行了分析,提出對數(shù)據(jù)、信息、信源、信息變異等的警示。對未來大數(shù)據(jù)支持下的傳播學的創(chuàng)新和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傳播;自媒體;交互;平臺;大數(shù)據(jù)
信息技術(shù)的飛速發(fā)展給世界帶來的最大影響和促進就是變革。這是全人類和社會進步的彰顯,也是人類對自身生命及生活質(zhì)量的提升。
這種快速的變革是通過科技進步與社會協(xié)定的交合,通過信息技術(shù)與社會的需求,通過人類生活與自我感受的融合而產(chǎn)生了整個世界的變革。其中,信息技術(shù)對傳播的變革產(chǎn)生并給予了極大的促進,突破了傳統(tǒng)傳播學的概念和理念,使傳播媒介(載體)、傳播方式、傳者和受眾在如此巨大的變革中得以升華。
1 媒體技術(shù)與傳播載體的變革
現(xiàn)代傳播學最明顯的變革就是傳播媒介(載體)的變革。
在20世紀,著名傳播學家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提出過“媒介即信息”的相似理論。其含義是: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義的信息,即人類只有在擁有了某種媒介之后,才有可能從事與之相適應(yīng)的傳播和其他社會活動。
傳播媒介的作用可以影響我們理解和思考的習慣,對于社會來說,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信息”不一定是媒體所傳播的內(nèi)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zhì),是它所開創(chuàng)的可能性以及帶來的社會變革。
現(xiàn)代傳播過程的變革具有如下特點:1)數(shù)字技術(shù)促進傳播載體的變革;2)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促進傳播時空的變革;3)自媒體促進傳播方式的變革。
傳統(tǒng)傳播學的理論并沒有(或少有)討論傳播過程的時空問題和時空關(guān)聯(lián)。隨著20世紀后期互聯(lián)網(wǎng)、尤其是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的構(gòu)建和發(fā)展,信息(數(shù)據(jù)及內(nèi)容)的傳播對于傳者和受眾,在時空概念上已經(jīng)感受不到時空的限制,“世界是平的”“信息全球分享”這樣的概念每每出現(xiàn)在傳播學教材和實例中。
信息不再有時間的延遲和空間的局限(除非人為控制),迫使媒體和媒體人感受到激烈的競爭態(tài)勢和傳播壓力。信息的擁有、產(chǎn)生和傳播的優(yōu)勢和主動權(quán)就不僅僅是專業(yè)媒體的獨有權(quán)力,而向整個社會開放了。
自媒體(We Media)的出現(xiàn),以“公民媒體”“公眾媒體”或“個人媒體”的方式,促使傳播者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和自主化,并以數(shù)字化、電子化、網(wǎng)絡(luò)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數(shù)或者特定的單個人傳遞規(guī)范性及非規(guī)范性信息。自媒體的實現(xiàn)借助了信息技術(shù)和工具,如:個人電腦、平板電腦、智能手機等。也借助了互聯(lián)網(wǎng)(含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各類平臺,如:博客、微博、微信、論壇/BBS、貼吧、公眾號等網(wǎng)絡(luò)社區(qū)或群落。自媒體時代顛覆了由傳統(tǒng)專業(yè)媒體機構(gòu)主導的信息傳播,推動并形成了由普通大眾主導的信息傳播活動,信息內(nèi)容擴大到圖文聲像的整個領(lǐng)域,促成了傳播領(lǐng)域的一場革命性變革。
2 傳播過程變革的幾個關(guān)鍵點
信息時代,人人都是傳者,人人也都是受眾,每個人既主動,也是被動。
變革同時引發(fā)了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變革有幾個關(guān)鍵點,也正是現(xiàn)代傳播學要討論、研究和對待的問題。
2.1 傳播與受眾的方向變革:對等
眾所周知,在傳統(tǒng)的傳播過程中,“方向”這個概念在傳者和受眾之間一直、或者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單向”的。無論是平面媒體(如:報刊雜志等),還是電子媒體(如:廣播電視等),都是面向受眾的單向傳播。受眾除了被動地接受(接收)到傳播內(nèi)容,通常無法表達自身的感受、意見和評論。這種“單向性”反映在傳播理論中通常被稱為宣傳,傳者與受眾的關(guān)系也通常是固定的。傳者具有專業(yè)性和主動性,而受眾也就僅僅體現(xiàn)為被動地接受。
自媒體的出現(xiàn),打破了這種不公平的格局,新媒體不再有傳者和受者的界限,每個人都是傳者,也即“人人即媒體”,每個人也是受眾(包括原本的傳者)。這樣,傳統(tǒng)傳播學意義上的“受眾”,在信息時代已經(jīng)被另外一個詞匯“用戶(User)”所代替。這種“對等”關(guān)系,更加期望社會文明和公民素質(zhì)達到一個較高程度,這是國家發(fā)展、社會進步的必然趨勢。
2.2 傳播變革中最大的突破:交互
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促進了“互動”需求,反之也引發(fā)了電子、通信領(lǐng)域中傳輸設(shè)備的“回傳”技術(shù)和裝置的誕生。從早期的電視購物,到后期的視頻電話,從最簡單的“人機交互”一步步進展到“所見即所得”。
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突破并實現(xiàn)了傳播的“交互”過程,既上行下達,又下行上傳。網(wǎng)絡(luò)空間中的“下載(download)”和“上傳(upload)”激發(fā)了“受眾”的廣泛參與,推動了電子郵件(E-mail)的廣泛使用,促進了信息產(chǎn)業(yè)領(lǐng)域人機交互設(shè)備的研發(fā)和推廣。
交互性激發(fā)了大眾傳播的參與性,“交互”這個詞也成為20世紀末最引人入勝和使用最頻繁的詞之一。
2.3 平臺對傳播的重要支撐:共享
當前,人人都擁有且日常攜帶著個人智能終端,如手機和平板電腦等,但它們僅僅還是“終端”,它們所產(chǎn)生和接受的信息仍然需要匯集點和轉(zhuǎn)發(fā)點,這就是我們所談的“平臺(Platform)”。
信息平臺在技術(shù)上是計算機、通信、軟件系統(tǒng)、數(shù)據(jù)庫和應(yīng)用服務(wù)模塊的集成,它支撐著傳播中共享和分享機制的形成。這種基于網(wǎng)絡(luò)(互聯(lián)網(wǎng))、系統(tǒng)(云計算)和信息(大數(shù)據(jù))的平臺形成了信息社會中的“社交網(wǎng)絡(luò)”和“網(wǎng)絡(luò)社區(qū)”。
平臺奠定了交互中的共享與分享,也在調(diào)節(jié)并控制著信息交互。平臺的擁有者具有較大的“權(quán)力”,可以對平臺上交互的內(nèi)容進行管理(監(jiān)控或關(guān)閉)。
共享和分享型的傳播方式促使傳播過程中的傳者和受眾都融合在這個參與、交互、共享、分享的平臺上了。自然,平臺也就承擔了非常重要的責任和支撐。
3 傳播變革中的問題、警示與對策
傳播的方式從單一到多類,從交互到共享,傳播的內(nèi)容及形式從單純文字、語音,拓展到“圖文聲像”“3D融合”、甚至“虛實相間”等,從而導致傳播類別與信息的泛化。在“大眾傳播”的空間世界,傳播者和受眾的關(guān)系也從單一變?yōu)橄鄬Α皩Φ取保蛘弑舜恕叭诤稀薄?/p>
信息的泛化促使傳播工作者對這類傳播學現(xiàn)象和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傳播過程中信息泛化引發(fā)的信息“關(guān)聯(lián)”“延伸”“變異”等對傳播工作者既提出了問題,也給予了警示。
3.1 傳播面臨信源、真實性與法律責任的問題
傳播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傳播內(nèi)容的真實性。
傳播真實原本是依靠傳播者的職業(yè)道德(誠信)和權(quán)威性(公正)來保證的,如果這兩個原則被打破了,或者恣意所為,傳播內(nèi)容就受到極大影響,受眾就處于被欺騙的位置。
在網(wǎng)絡(luò)世界的傳播中,要確定一個“信源”,難度是比較大的,傳播內(nèi)容的真實性也較難得以驗證。那么,“真實”和“信任”的基礎(chǔ)只建立在“私信力”和“公信力”兩者上。前者基于朋友和“熟人”,或者說“信得過”的人,后者則期望政府及公眾媒體的權(quán)威性發(fā)布。由于信息不對稱,故此處公信力的出現(xiàn)對人們確認信源并建立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以自媒體空間的“微信”為例。微信支持的幾種傳播范圍如:1)單一(私聊);2)多維(群聊、朋友圈);3)共享(公眾號)。在這些空間中傳播的信息有“原創(chuàng)”和“轉(zhuǎn)發(fā)”類型,而“轉(zhuǎn)發(fā)”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轉(zhuǎn)發(fā)者對某些傳播內(nèi)容的趨向性或趨同性。轉(zhuǎn)發(fā)過程還可以加上轉(zhuǎn)發(fā)者自身的“評論”,甚至改變“標題”,修改內(nèi)容,增刪文字等。這樣,就會產(chǎn)生信息的變異。更由于轉(zhuǎn)發(fā)產(chǎn)生的循環(huán)效應(yīng),信息變異的可能性會增大,使信源更難以確定,真實性無法追溯。這給那些肆意編造信息的別有用心者提供了一個隱匿的空間。
網(wǎng)絡(luò)世界被稱作“虛擬世界”,網(wǎng)絡(luò)中傳播的信息內(nèi)容也存在真假共存的現(xiàn)象。假信息與謠言的傳播影響,在信息時代其傳播速度、覆蓋空間、受眾范圍、變異程度都是傳統(tǒng)傳播不可比擬的,所造成的影響和結(jié)果也是很難預(yù)料,甚至是不能承受的。加之傳播(轉(zhuǎn)發(fā))中信息的變異(避實就虛、斷章取義、添油加醋、故弄玄虛、肆意篡改等),要達到傳播的真實性,對傳者和受眾(都是“用戶”)的責任要求就更高,而僅靠“文責自負”“謠言止于智者”是不能完全或根本解決問題的,這就必須有法律的制約。
公眾媒體在傳播真實性方面的責任是巨大的。這類媒體的“發(fā)聲”具有導向性,尤其在信息不對稱的時候,是傳播并依賴“公信力”的最佳時候,如果此時“公信力”的“失聲”,無疑會導致信息的混亂,從而放任“變異”信息的泛濫。
3.2 “垃圾”信息引發(fā)社會的強烈關(guān)注
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電子商務(wù)和社交媒體的快速發(fā)展促使數(shù)據(jù)量成指數(shù)增長。據(jù)IDC(國際數(shù)據(jù)集團)的研究報告表明,2020年全球新建和復制的信息量將超過40ZB(40萬億GB)。而目前每天全球互聯(lián)網(wǎng)流量已經(jīng)達到或超過1EB(即10億GB)。人們不知不覺中留下的“數(shù)據(jù)碎片”已經(jīng)滲透到社會經(jīng)濟、大眾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
我們知道,僅僅通過“微信”等社交媒體的“轉(zhuǎn)發(fā)”功能,已不可避免地引發(fā)傳播信息量的巨增,從而導致信息冗余重復,收發(fā)輪番循環(huán)等問題。加上對轉(zhuǎn)發(fā)信息的評論、修改,以及通過傳播“驚爆標簽”、營銷號和“標題黨”等導致的信息變異,使得當前的信息系統(tǒng)、信息存儲和信息分析受到極大壓力,也使網(wǎng)絡(luò)搜索(如Google、百度)引擎承受極大負載。冗余信息大量存在,加上廣告、電商等信息傳播,“垃圾信息”成為信息社會中的另一個大的社會問題。
作為受眾,原本可以有選擇地接收和閱讀,然而,基于交互、共享和推送技術(shù),你不想得到的信息,或者說一些“垃圾信息”也不斷地充斥到個人的信息終端(手機)上,對個人來說不勝其煩,對社會來說資源浪費。
“垃圾信息”的存在和解決給信息工作者和傳播媒體人都提出了新的警示和要求,分別提出了從技術(shù)上、從道德規(guī)范與法律法規(guī)上解決的途徑,新型的智能搜索引擎和智能辨析系統(tǒng)已經(jīng)在網(wǎng)上出現(xiàn),隔離和防范計算機病毒與其他惡意程序的軟件也已經(jīng)日益成熟,“數(shù)據(jù)碎片”的整合和擯棄正日益完善。
3.3 傳播者與受眾“共享”的社會責任與法律責任
基于自媒體的傳播,借助“微信”一類交互和共享平臺,信息會被無限制地放大,其變異也會無限制地放大,成為真正的“廣播”。對于個體而言,涉及的是公民隱私,對于社會而言,涉及的是信息殺手,如:“網(wǎng)絡(luò)暴力”。
在網(wǎng)絡(luò)交互平臺上,朋友圈中的“網(wǎng)曬”是自身生活、工作、家庭、旅游等高興之事、喜愛之物等放到網(wǎng)上與人分享、展示生活,由他人評說,網(wǎng)友之間交流互動,該過程是一個認識自己、聽取意見、學習他人的過程,也已成為一種個人尋找群體的聯(lián)絡(luò)方式。
但如果公民自身沒有或缺乏“公民隱私權(quán)”的意識,個人信息的泄漏會給自身或者社會帶來不少問題,近年來發(fā)生的各類網(wǎng)絡(luò)詐騙幾乎都涉及公民隱私的泄漏,不法分子利用信息的傳播和共享,實施有針對性的犯罪。
“網(wǎng)絡(luò)暴力”是另一種涉及“公民隱私權(quán)”的輿論力量。例如,“網(wǎng)搜”中的所謂“人肉搜索”在網(wǎng)絡(luò)暴力中就顯得尤為畸形。這種針對個人隱私的獵奇、搜索、暴露、宣泄和炒作,通過網(wǎng)絡(luò)傳播的放大和轉(zhuǎn)發(fā),引發(fā)指數(shù)式的信息爆發(fā)。人們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會對當事人進行指責,攻擊,甚至謾罵,最后形成一股“吃人”的力量(心理和社會壓力),殺掉那個輿論中心的受害者。2012年曾經(jīng)上演過陳凱歌拍攝的一部叫《搜索》的電影,講述了一個被網(wǎng)絡(luò)暴力害死的清白姑娘的故事。所以,網(wǎng)絡(luò)暴力完全違背了道德,侵犯了個人隱私權(quán),還違反了法律。
令人欣慰的是,2017年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首次就打擊侵犯個人信息犯罪出臺了司法解釋,對于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嚴打泄露個人信息等社會關(guān)注焦點有了明確規(guī)定,對即將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起到先驅(qū)的作用。
綜上所述,在“共享”平臺上,傳播者與受眾都必須遵守社會道德,共擔共享社會責任與法律責任。沒有約束的自由不是自由。針對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個人隱私、數(shù)據(jù)權(quán)益、新聞傳播等方面的法律的健全是一個法治社會必須建立的規(guī)則。所以,現(xiàn)代傳播學中研究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傳播與法律的關(guān)聯(lián)。(見作者另文,此處不贅述)
4 基于大數(shù)據(jù)的傳播思考
現(xiàn)代傳播學進展到了“大數(shù)據(jù)”時代,大數(shù)據(jù)是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到現(xiàn)今階段的一種表象或特征。傳播離不開數(shù)據(jù)、離不開信息,而隨著各類傳播媒體的發(fā)展和彼此交融,傳播方式所涉及的交互、共享中關(guān)聯(lián)的信息已經(jīng)是海量信息,而這些數(shù)據(jù)每年都按指數(shù)方式在繼續(xù)增長。現(xiàn)代傳播學面對的是一個數(shù)據(jù)科技(DT)時代,數(shù)據(jù)傳播平臺、網(wǎng)絡(luò)平臺也面對的是各類媒體(自媒體意義上的多媒體融合)的融合。那么,現(xiàn)代傳播學如何對待大數(shù)據(jù),如何基于大數(shù)據(jù)進行現(xiàn)代信息社會意義上的傳播,是我們必須考慮和研究的問題。
大數(shù)據(jù)不僅是數(shù)據(jù)量、數(shù)據(jù)流“巨大”,數(shù)據(jù)的處理也無法用傳統(tǒng)的方式進行,需要一些新的處理模式才能通過信息(數(shù)據(jù))處理,形成更強的決策力、洞察發(fā)現(xiàn)力和流程優(yōu)化能力。傳播方式的變革也需要我們改變傳統(tǒng)傳播過程對數(shù)據(jù)的準備、獲取、分析和傳播。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在《大數(shù)據(jù)時代》一書中舉了許多例證,都是為了說明一個道理:在大數(shù)據(jù)時代已經(jīng)到來的時候要用大數(shù)據(jù)思維去發(fā)掘大數(shù)據(jù)的潛在價值。
基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傳播要考慮的是:海量的數(shù)據(jù)在網(wǎng)上,在數(shù)據(jù)庫間流動,數(shù)據(jù)變得在線了。信息的流向是不可控的,在其傳播過程中,泛化產(chǎn)生了,泛化和變異的信息(數(shù)據(jù))會回流到網(wǎng)絡(luò)(媒體),進行下一輪的傳播(轉(zhuǎn)發(fā))。信息(數(shù)據(jù))是把雙刃劍,在傳播過程中,傳者和受眾都會因此受到正面的和負面的影響。
如何面對大數(shù)據(jù)時代,是現(xiàn)代傳播學和傳播工作者不容回避的問題。限于篇幅,此處不再贅述,請參見作者另文:《大數(shù)據(jù)支撐下的信息傳播》。
5 結(jié)論
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促進傳統(tǒng)的傳播載體產(chǎn)生了革命性的變革,這些變革縮短了傳播時空,改變了傳者與受眾的關(guān)系。互聯(lián)網(wǎng)(含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自媒體的強勢介入,改變了傳統(tǒng)傳播的方向和主流。交互、共享和分享在信息技術(shù)支持下的“個人智能終端”和“公共智能平臺”的支撐下,對現(xiàn)代傳播過程中起到了實質(zhì)性的作用。傳播類型和信息的泛化促使我們對傳播變革中的新問題進行思考和分析,提出對數(shù)據(jù)、信息、信源、信息變異等的警示,使我們對現(xiàn)代傳播學中傳播與法律的關(guān)聯(lián)進行深入思考,對未來大數(shù)據(jù)支持下的傳播學的創(chuàng)新和教育給予更密切的重視和研究。
[1]托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M].何帆,等,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shù)出版社,2006.
[2]代玉梅.自媒體的傳播學解讀[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1(5):4-11.
[3]YOKA網(wǎng).微信:自媒體的“少數(shù)派報告”[EB/OL].2013-05-13.
[4]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大數(shù)據(jù)時代[J].周濤,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G2
A
1674-6708(2017)192-0013-04
劉暢,助教,四川音樂學院傳媒學院,研究方向為新媒體與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