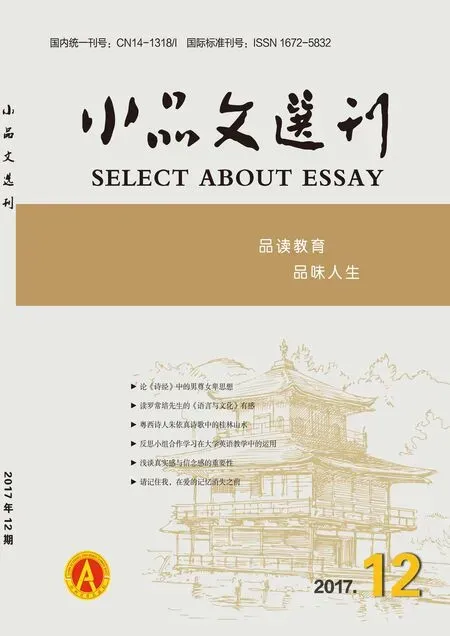粵西詩人朱依真詩歌中的桂林山水
吳名茜
(西南民族大學文新學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粵西詩人朱依真詩歌中的桂林山水
吳名茜
(西南民族大學文新學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乾嘉年間的朱依真,雖終身未仕、一介布衣,卻是這一時期粵西的重要詩人。清代的文學批評家袁枚稱其為“粵西第一詩人”,這也是肯定了他在詩歌創作上的成就和詩壇上的地位。作為當時臨桂(今桂林)人的朱依真,在詩歌中多有涉及周邊的山水名勝。本文通過解讀朱依真相關的詩歌,來還原這一時期的桂林山水。
朱依真;桂林;山水
桂林自秦代秦始皇修建靈渠、開發以來,距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且桂林所處的喀斯特地貌地區,使得桂林多奇山秀水,向來為人們所稱道“山水甲天下”。朱依真作為乾嘉時期在粵西地區較為活躍的一位詩人,他的詩中多有涉及桂林的山水和古跡,有的仍是今天桂林市的重要景點,有的或找不到蹤跡或毀于災禍。朱依真流傳的作品經后人整理,存有《九芝草堂詩存校注》一卷,共有存詩二百五十八首,其中涉及桂林山水及桂林地區的詩作有二十九首。
1 奇山碧水
桂林山水最大的特點莫過于山之奇、水之碧,山與水的結合在桂林組成了一幅絕妙的畫卷。所以桂林的山水,自然也就成為了朱依真筆下必不可少的元素。在朱依真的詩中,提到的桂林諸山有普陀山、駱駝山、伏波山、疊彩山、獨秀峰、寶積山、虞山、南溪山和中隱山,基本涵蓋了今天桂林市及周邊地區較為著名的景點。從詩中也可以看出,這些地方風景秀美,也是詩人在生活中時常游歷和與志趣相投的文人們唱和集會的地方。
在朱依真的筆下,桂林的山表現出最為直接的特點就是山勢“奇險”:
振衣直上層巖巔,谽呀洞壑相勾連。①
聳身登春臺,象緯逼難仰。郁嵯百雉堞,佻眺僅容掌。②
此二句都是詩人登上山后發出的感慨,第一句寫七星山之勢用了“洞壑相勾連”,可見此處山高谷深,連綿延伸。而次句是詩人登上寶積山的孔明臺所見之景,對于寶積山的高聳,詩人寫下“象緯逼難仰”。“象緯”指日月五星,寶積山之高竟是日月都難以仰望的程度,郁郁蔥蔥的的高山看似有百丈城墻這般高。杜甫當年游龍門山時,曾作《游龍門奉先寺》云:“天闕象緯逼,云臥衣裳冷。”,朱依真句亦用“象緯逼”,大有學杜之意。在另一首詩中,詩人對于七星山的描寫,還做出了進一步更大膽的想象:
七星初隕時,遼邈無前聞。即今化為石,氣象猶捆缊。燦燦隔河渚,蓬蓬多白云。③
七星山因有七個山峰似北斗七星而得名,故詩人在這句中將七星山的形成歸為于遠古時七星的隕落。今日七星已化為此地的高山,燦然而立在江河之上,向上高聳足以直插入云。且七星山延綿伸展,宛如天然屏障,故詩人又云:
攢攢啟青嶂,轉側忽成峰。迤邐彈丸溪,循環麋鹿蹤。彈巖頗窱,乳石垂如鐘。④
詩中的“彈丸溪”是彈子巖洞內向外流向漓江的溪水,山勢沿著溪水走,山腹內的彈子巖石筍倒垂,如懸掛的編鐘般。《甲午十月既望,同南溪、春岑、秋岑游樓霞寺,徧訪彈子省春諸巖之勝,返飲此山亭,月出始歸,約賦五首七首,以口云峰缺處涌冰輪口為韻》這組詩是朱依真較多直接描寫桂林山水景色的作品,在這五首詩中,朱依真由高山到蒼翠,由奇洞到碧水,將桂林山水在自然的造化下呈現出的秀美景象表現得淋漓盡致,同時朱依真也將自己的追求和志趣與山水相融合,情景一體。
而桂林的“碧水”在朱依真的詩中多于“奇山”相呼應:
一山枕江流,光艷奪雄翡。圑圞削瑤甗,宛轉通地肺。水洞生冰棱,陽巖暄老卉。⑤
“一山枕江流”寫的是位于漓江西側的雉山,與它南面著名的象山遙遙相對。詩人在寫雉山坐落在漓江邊時用了“枕”字,生動地勾勒出山水相依的景色,山光水色堪比一塊巨大的翡翠。在另一首作者登疊彩山寫的詩中,提及漓江也是如此:
湘天北望無多闊,漓水分流到此深。桑柘盈川猶滯綠,柳楊連岸不成陰。⑥
“漓水分流”是指漓江流到了桂林時,因此處的諸多山峰而產生分支,是作者“坐山看水”之景。此處雖不言山僅言水,其實呈現的是一派山水融合之景。這也側面表現出,在桂林正是有奇山與碧水的結合才會有這“甲天下”的風景展現于世人面前。
2 歷史文化悠久
從朱依真的詩里,除了讀出桂林山水得天獨厚的奇險秀美外,還可以從他記載游歷、游歷的詩中發現,在桂林山水之中古跡頗多,有的至今尚存,有的已消失在歷史的變遷中。
七星山,即今天桂林市的七星公園,這片區域也是在朱依真筆下涉及較多的一個地方。朱依真關于此處的詩作有六首,提及龍隱巖、普陀山、棲霞寺、碧虛亭、彈子巖幾處景致。其中的龍隱巖和彈子巖都是在七星山腹內的巖洞。彈子巖即今天的七星巖,以洞內天然形成的形狀奇特的鐘乳石而聞名。而龍隱巖則以自唐以來、古人留下的碑記而著稱,距今統計共有石刻碑記220余方。朱依真的《七月七日游龍隱巖觀宋人碑記》一詩,就是詩人游龍隱巖洞內碑記時的有感而作。在此詩中,朱依真提及了北宋初年名將狄青平定嶺南叛亂和元祐黨爭之事:
摩挲古壁苔花紫,壁上題名半天水。平蠻一碑尤偉奇,想見襄武熊羆資。
胡為刊此元祐籍,青蠅居然間黑白。為臣不種戒何人,萬世存留禠丑魄。
第一句的“平蠻一碑”即北宋皇祐五年狄青、孫沔、余靖等平定儂智高起義后班師經桂林所刻的“平蠻三將題名”,而“襄武”則是狄青的謚號。但此處疑是作者有誤,按《宋史·狄青傳》⑦載:“帝發哀,贈中書令謚武襄”,故狄青的謚號應該是“武襄”。而在第二句言“元祐籍”,則是指北宋徽宗時蔡京專權,把元佑年間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司馬光、蘇軾、黃庭堅三百零九人列為奸黨,并將姓名刻石頒布于天下,但后來徽宗又下詔毀掉這些碑記。龍隱巖現存的這塊碑刻為是被列為“元祐奸黨”的梁濤的曾孫梁律,在南宋慶元四年根據家藏舊本而重刻的。
七星山上的棲霞寺也是詩人在詩中提及較多的一個地方。棲霞寺最早始建于唐代,在歷朝歷代的變遷中,幾經毀壞和重修。到朱依真所處的年代,他看到的棲霞寺是清順治、康熙年間再次重建的。詩人共有五首詩的題名提到了棲霞寺,從題目中的“集棲霞寺”、“在棲霞口分韻”、“遂至棲霞寺小集”、“遂至棲霞寺晏集”這些語句來看,棲霞寺是詩人與友人們游覽山水后,集會的常去之處。詩人在詩作中對棲霞寺周邊的景物有較多描繪:
梵宮托林麓,鐘鼓聲殷殷。危壁出蒼髓,古藤纏綠筋。結契松竹歡,忘機魚鳥欣⑧
山周翠玦環,寺聳鉅鼇戴。萬綠森在眼,杰石擁其背。相與結凈緣,不必衷禪鎧。清酒陶匏陳,高歌弦筑配。⑨
在朱依真的筆下,他以“梵宮托林麓”突出棲霞寺四周綠林環繞的自然環境,在此處僅能聽到屬于寺院的殷殷鐘聲,表現出寺院周圍的有著那種遠離喧囂的清幽。又言“相與結凈緣,不必衷禪鎧”,可以看出在棲霞寺讓作者感受到內心的寧靜與釋家濃厚的禪意。還值得注意的是,在離棲霞寺不遠的地方有一碧虛亭,這也是朱依真常與友人相聚的地方。關于碧虛亭的詩句,詩人如下寫到:
擬將梯青屐,上謁日華君。⑩
洞中仙子不可見,金堂玉室行恐迷。
石湖有遺口,放浪亦可慨。
前兩句言“日華君”、“洞中仙子”,引的便是南宋尹穡所寫的《仙跡記》中關于彈子巖的傳說,講述了唐人鄭冠卿在棲霞洞遇日華、月華二仙的故事。而“石湖”則是范成大晚年的自號“石湖居士”,此處即代指范成大。南宋乾道七年(1171),范成大出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在桂林為官期間,他游覽在游覽桂林秀美的山水后,命人在彈子巖外修建碧虛亭,并根據《仙跡記》的傳說在彈子巖旁邊刻下《碧虛銘》,寫下了關于以“碧虛”命名的依據。當時范成大碧虛亭時曾為彈子巖題名“碧虛洞”,后當地人誤將此名冠于七星山北麓的普陀巖,故今天提及碧虛洞則多指普陀巖。
桂林另一處遺留較多歷史遺跡而引得詩人去游覽的,是矗立在漓江之濱的伏波山。伏波山的腹內有一還珠洞,洞內留存了大量唐時佛教徒們在洞中雕刻的佛像,還有當年曾出任臨桂縣尉的米芾在洞中留下了《米芾還珠洞題名》一文。米芾死后,時任廣西轉運判官的方信孺把米芾的自畫像刻到了此文的旁邊,構成了現在還珠洞內的景致。朱依真在《冬至后一日,同南春岑泛舟游環珠洞,訪襄陽像》中記錄下了他到還珠洞游覽:
米老沉淪煙水境,古裝仿佛來相迎。儼然衣帶法吳生,自道骨髗本天性。昔來題識頗分明,強記深慚禰正平。
此處作者云“法吳生”,表明還珠洞內的米芾自畫像甚是逼真,猶如出自吳道子之手。同時,畫的米芾身著宋時的服裝,長帶寬袖,詩人猶能從此畫中感知到米芾性本愛山水的志趣。詩人在看到畫像旁米芾的題名后,只恨自己沒有彌衡那樣“目所一見,輒誦于口”的好記性,能記下米芾的好字。另從“米老沉淪煙水境”此句可看出,當時還珠洞還只有臨江的一面有洞口,要坐船方能進入,后來人們在西面和南面開了兩個口,現在才可以從陸地步行入洞游覽。
從朱依真留下的這些詩篇中,還可以找尋到一些今人看不到的桂林景致。如詩人有《松圃招游寶積寺集,酒酣賦比,時歐陽礀(澗)東、陶季壽章溈在坐》,此篇提到的“寶積寺”今已不存;另有《冬日同黃大登冷然閣》,詩題中的“冷然閣”,據《廣西通志》載:“冷然閣在劉仙巖上”,而劉仙巖位于桂林南溪山腹內,但在今天桂林的南溪山公園已經沒有這個建筑了。
3 詩人對桂林山水的情懷
除上文提及的篇目之外,詩人在詩中在游覽其他古跡時的詩作較為零散,本文不多做分析。但是從整體來看,朱依真寫桂林山水的這些作品占其作品總數并不多,詩人還有許多在其他地方游歷時所寫的作品。但是對于桂林的山水,一則桂林是作者的故鄉,二則桂林山水確是秀美非凡,故朱依真對于桂林山水是有著非同一般的情懷的:
惜我游端州,星巖號奇絕。洞壑雖勾連,竦秀寧此垺。
“端州”大致相當于今天廣東省肇慶市及其周邊區域,星巖指的是肇慶市的七星巖,與桂林的七星山同名,同樣是由七座石灰巖山峰組成,自晉代就已有文字記載。在朱依真看來,星巖雖山峰眾多,號稱奇絕,但是飄逸出眾又怎能與桂林的七星山相比,字里行間洋溢著詩人內心自豪與喜愛的情感。還有一些朱依真離開桂林外出游歷的詩作,雖然本就有離別之情包含其中,但詩人卻將這種感情融入桂林的群山中:
群山相遮留,戢戢篷窗前。
閑云擬相送,故故出山遲。
“群山”留、“出山遲”,從詩中可以想象出,當時詩人乘船沿江北上離開桂林,望著桂林重重山峰一座座經過,流露出分離時的不舍和留戀都寄托在桂林的群峰之中。此情此景下的桂林山水已不止是游歷的勝地,更變成朱依真對家鄉的一種牽掛。
注釋:
① 《七月七日游龍隱巖觀宋人碑記》
② 《二日挈兒輩游孔明臺,擬等獨秀,遇雪不果,因過菜圃中市芥辣歸,小飲竟醉,陶然賦此》
③ 《甲午十月既望,同南溪、春岑、秋岑游棲霞寺,徧訪彈子省春諸巖之勝,返飲此山亭,月出始歸,約賦五首七首,以口云峰缺處涌冰輪口為韻》
④ 同注③
⑤ 《同南溪游雉山巖》
⑥ 《同松圃游定粵寺,因登疊彩山,用昔人題壁韻》
⑦ 《宋史·卷二百九十》,中華書局,2010年,第9721頁。
⑧ 《甲午十月既望,同南溪、春岑、秋岑游棲霞寺,徧訪彈子省春諸巖之勝,返飲此山亭,月出始歸,約賦五首七首,以口云峰缺處涌冰輪口為韻》
⑨ 《李少鶴明府招同楊石墟祖貴茂才、許密齋異行明府、王若農尚玨贊府、浦柳愚明經、李松圃郎中集補陀巖,用口七人姓字在棲霞口分韻,蓋石湖屏風巖題壁句也,余得在字》
⑩ 同①
[1] 〔元〕脫脫等撰.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2010.2
[2] 〔宋〕范曄撰.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2010.2
[3] 〔清〕朱依真著 周永忠 梁揚校注.九芝草堂詩存校注[M]成都:巴蜀書社,2014.4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研究類項目《清代廣西詩人朱依真詩歌研究》;項目編號:2017ZYXS164
I209.9
A
1672-5832(2017)12-004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