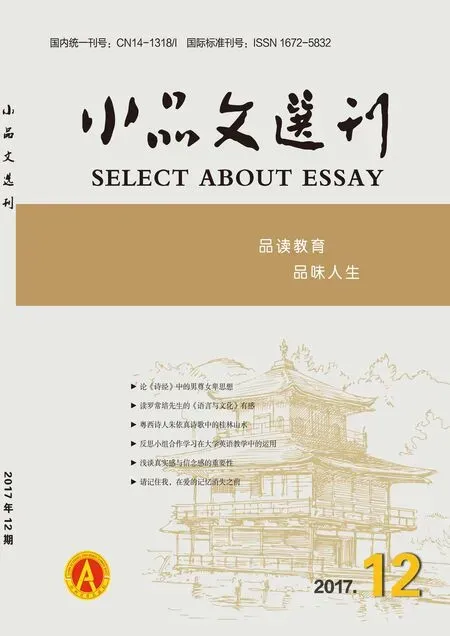商談論視角下的法治國原則
——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解讀
周 鈺 包曉娟
(山東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山東 淄博 255000)
商談論視角下的法治國原則
——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解讀
周 鈺 包曉娟
(山東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山東 淄博 255000)
哈貝馬斯認為,經濟危機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仍然存在,但是它已經不是社會的主要危機了。因為國家應用行政手段過多的干預私人領域,所以促使其行政決策的合法性也遭到了人們的普遍質疑。哈貝馬斯從商談論的視角出發,重新定義法律合法性的來源。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中提出的商談論應用于法治國和社會運行治理的諸方面,本文試圖通過討論商談論視域下的社會運行與治理,反思其不足之處,分析其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哈貝馬斯;商談論;法治國
哈貝馬斯作為一名成長于納粹德國時期的思想家,他與同時期的其他思想家一樣,對納粹德國的統治心有余悸。并且他們對產生了康德、黑格爾、馬克思、萊辛、席勒、歌德等思想大家的民族竟然出現了納粹的殘暴統治這一怪異現象深感詫異。[1]這些都自然而然的影響到這些思想家的理論思考,哈貝馬斯當然也不例外。哈貝馬斯在《在事實與規范之間》一書中,從商談論的視角出發,結合自身感悟理解和當代學術思想對法治國原則的內涵提出新的界定:人民主權原則、確保每個個人都能的到全面的法律保護原則、行政合法規性原則、國家與社會相分離原則。
1 商談論視野中的人民主權原則
二戰之后,人們反思戰爭,對人本身給與了更多關注,對人的價值給與更多重視。人民主權原則也得到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認可,無論實行什么制度的國家紛紛將人民主權原則寫進自己的憲法中,以體現對其重視。人民主權原則的含義是一切國家權利來自人民。起初,人民主權原則是對君主特權的限制,它的性質是人民與君主或者政府之間的契約。
在哈貝馬斯對法治國原則的內涵體系中,人民主權原則居于基礎地位。哈貝馬斯沒有從社會契約角度對人民主權原則進行討論,而是從商談論角度對人民主權進行了定義。哈貝馬斯認為:“根據其商談論理解,人民主權原則的意義是一切政治權利都來自公民的交往權利”。[2]哈貝馬斯從交互主體性的立場出發,認為沒有人能真正占有這種交往權力。他認為交往權利并不能直接產生產生政治權利,通過交往權利的行使只能產生法律。法律進而對政治權利產生影響,政治權利依靠法律獲得其合法性。這些法律是公民通過商談得出的商談性意見的形成過程中制定的。
哈貝馬斯從商談論的角度出發,對人民主權原則的具體內容進行了新的探索,使人民主權的法治原則不僅可以為法律和權力提供合法化論證,而且還為人民主權的真正實現規定了具體的方式與步驟,為交往權力的形成并進而為人民主權的實現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3]
2 商談論視野中的全面保護個人權利原則
人民主權原則即要求每個公民可以平等的參與公共決策,同時也要求每個公民參與決策多表現出的意志上升為法律的可能性。因此,法治原則不但要求人民主權,還要求確保每個個人全面的法律保護。商談論的角度來討論確保每個個人全面的法律保護原則,哈貝馬斯采取的思路是:從公民這邊來看,公民的權利只有通過法律才能得到詮釋和展開;從國家這邊來看,有組織的國家權力只有通過法律才能得到控制。[4]確保每個個人全面的法律保護原則是哈貝馬斯商談理論必然到處的結果。
交往形式可以分為論證性商談和運用性商談。法律的運用性商談是指法律具體運用到具體案例的過程,即針對特定具體的案例運用合適具體的法律規范。強調各個參與人積極公平參與,法官居中裁判,其他訴訟主體可以針對案件,發表各種爭議性的意見,以此展開對話與商談,并且法官要給出自己的裁判理由。論證性商談中,原則上只存在參與者,沒有裁決者,這是與運用性商談的主要區別。這兩種類型的商談也是立法與司法的劃分。立法對應于法治原則中的人民主權原則,著眼于運用性商談的司法職能則要求確保每個個人全面的法律保護的原則。
3 商談論視野中的行政合法原則
在商談論中,行政過程是法律具體運用得過程,行政活動必須遵循法律。行政合法原則反映的是權力分立。行政過程遵循的法律是每個公民參與決策多表現出的意志上升為的法律,這樣就確保了行政權力產生于公民共同地形成的交往權力。
這樣就使行政行為有了一個大前提——法規。這樣的話,任何違背這個前提的行政行為都是無效的,所以說行政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和抽象行政行為都是可以被撤銷的。另一層不言而喻的意思是:行政行為絕不可干涉立法和司法行為。
4 從商談理論看國家與社會相分離原則
從商談理論的角度來看,強調國家與社會的分離,這樣做的目的也是可以理解的:防止國家權利或者社會權利不經商談,不經交往權利的轉換,而直接轉化為行政權利。
哈貝馬斯并不認同國家僅僅作為守夜人,把其他事物交給與政府無關的、自我調控的經濟社會。他認為國家不是一種中立的政治力量,那種認為國家可以作為一種中立力量超越其他社會力量的觀點是不可取的。
5 結語
上述法治原則總結起來,就構成了一個體系。哈貝馬斯認為,在這個體系的背后,是這樣一個單一觀念:法治國家的目的,是一個自由、平等的公民聯合體,通過權利體系而構成的共同體或政治上自主的自我組織。法治國家的各種制度,應當確保具有社會自主的公民可以有效地運用其政治自主:一方面,法治國家的制度,必須使一種合理形成意志所具有的交往權力能夠存在,并在法律中獲得有約束力的表達;另一方面,它們必須允許這種交往權力通過對法律的合理運用和實施而在整個社會中流通,從而通過穩定相互預期和實現集體目標而發揮出社會整合力量。“我想強調的是這樣兩個方面:一方面,法治國賦予交往自由之公共運用以建制形式,另一方面,法治國給與交往權力向行政權力之轉化以規范指導。”[5]
[1] 陸玉勝.商談、法律和社會公正[D].復旦大學,2012.
[2]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97.
[3] 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M].童世駿譯.三聯書店,2004.
[4] 喻中.商談理論視野中的法治國原則[J].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07.
[5] 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M].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4.
[6] 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M].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
DF01
A
1672-5832(2017)12-015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