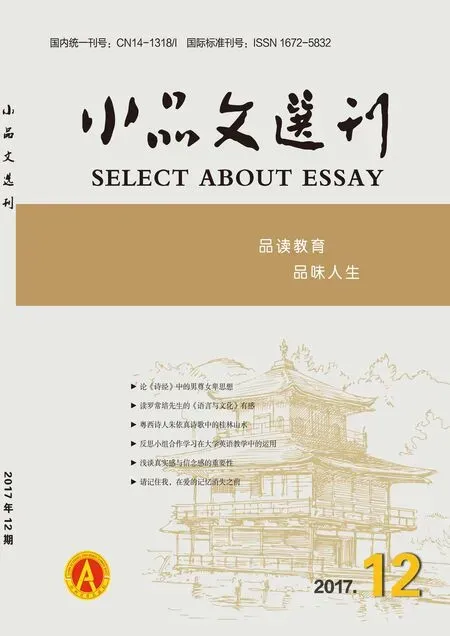中庸“誠”觀念的思想意蘊分析
高 欣
(四川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中庸“誠”觀念的思想意蘊分析
高 欣
(四川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誠”是《中庸》之中重要的核心觀念,對其思想意蘊進行分析有助于更為深入地了解《中庸》所蘊含的心性修養思想,體會其文化精神。“誠”觀念脫胎于早期的鬼神祭祀活動,后確定成為人生修養的一項重要品質。經過眾多學者發揮和詮釋,“誠”觀念具有了十分豐富的意蘊和內涵,成為儒家修身思想中重要的部分。并且伴隨儒家文化的發展,不斷充實和深化。
中庸;誠;修養;誠觀念
先秦各家學說中,儒家以其積極用世的精神、剛毅直健的人格得到了后世眾多的褒揚和認同。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儒者合于道義的行為和態度,并非憑空浮想,亦非外來強加,而是來自自身修養的覺悟。君子堅持“仁”的理念,不是一時興起,而是有其修養作為其思想行動的指導。
這種內在自省色彩對于儒家后來產生了重要影響。如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儒家談及自身修養,首重自己內心。以此為基,儒家修身思想主張“誠于中,形于外”,進而將修養境界概括為“內圣外王”。就此可以知道,“誠”的觀念在儒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它既是內在修養的首要條件,也是成就修養的必然要求。
1 中庸思想中的亮點——“誠”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①
——《論語·雍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②
——《論語·先進》
《論語》中關于“中庸”觀念提到,孔子在其教育活動中已經引入。孔子將之視為完美的品德,是人生修養重要部分,只是很難將之堅持。正是由于此,孔子開始以“中庸”的修養進行教學嘗試。并且依“中庸”之義,提出了“過猶不及”的教育觀點。
根據朱熹《中庸章句集注》,《中庸》的作者是子思,這種觀點十分廣泛,也存在爭議,但關于《中庸》思想的看法卻是可以參見的。《中庸》全書的思想繼承了孔子的“中庸”觀念,是為了昭明祖德而作。至于朱熹將此加以確定,把《中庸》與儒家道統思想結合,從而闡釋出了“十六字傳心訣”。這反映了中庸思想自我確立和完善的過程。其間有對于儒道傳統的繼承,也有對于現實當世適時的改造。
正是如此,《中庸》一書的思想內容,反映了儒家對于內在心性修養的看法,同時也給予后來學者諸多啟示。著名理學家程顥程頤更是對于中庸思想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中庸》內容“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熟讀《中庸》,必然“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③。
《中庸》豐富的歷史內涵,加之眾多學者深刻的發揮,賦予其獨樹一幟的文化品格。這是儒家傳統思想的智慧結晶,絕非是“折中主義”和“調和主義”。最直接和鮮明的證據就是《中庸》之中對于“誠”觀念的重視。
通觀《中庸》,其中關于修養的眾多問題,都涉及到了一個核心觀念——“誠”的觀念。“誠”觀念在《中庸》之中反復提及。《中庸》之中的“誠”觀念有著十分豐富的內涵,它既是個人修養的內在驅動,又是修養境界的完美總結。誠,既是進德修業的初心,又是“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的境界,貫穿于個人修養始終。
“誠”觀念是中庸思想的一大亮點,其豐富的文化意蘊,反映了中庸思想的深邃與精微。
2 “誠”觀念之他說
“誠”,從字源上講,可以看到元初的含義。“誠”字,最早出現是在金文之中,其解釋為“實現諾言”。而在更早的甲骨文之中,雖沒有本字對應,但可以在“戊”字部中找到一些線索。“戊”通指斧子一類武器,帶有“不可變易”“確定”等性狀。同時,“成”雖然也是武器,但引申為“就”的意思,表示已經發生、變為現實。而“誠”的言字旁則表示已經確證為現實的言語。這與金文之中對于“誠”的解釋是一致的。④
這是對于“誠”最初的解釋。“誠,信也”。《說文解字》則將“誠”解釋為“信”,側重表示其“言行若一”。⑤《孟子字義疏證》則將之釋為“實”,注重發揮其“確實”的含義,并將之與“仁”“義”“禮”等倫理思想相結合。⑥通過“誠”在字源字義上的演變,我們可以知道,誠最初的含義之中就包含了“真”“確實”等基本意涵。
有關“誠”的觀念,還可見于《尚書》等經典之中。
“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⑦
——《尚書·太甲》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⑧
——《尚書·大禹謨》
《尚書》之中所提到的“誠”觀念,與鬼神觀念相聯系。按照《尚書》的說法,人的內心之中必須要有誠,因為只有誠才可以與鬼神相交感。誠作為人與鬼神之間溝通的媒介,恰是二者的共通之處。于人,誠是人身最崇高的德行;于神,則賦予了自然鬼神以人格化的色彩。為此,《尚書》認為人神是可以交感的,同時鬼神也只會選擇內心有誠的人加以庇佑。這與《春秋左傳》之中的思想十分接近。
公曰:“吾享祀豐髫,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繁物。’……神其吐之乎?”⑨
——《左傳·僖公五年》
《左傳》也認為鬼神只會選擇有德的人加以庇護。但還有一點表達更為明確,那就是人神之間溝通的關鍵不在于神,而在于人,只有人的德行才是作為憑借的唯一依據。只是關于這種德行,《左傳》籠統概括為“德”,而《尚書》則更為具體的解釋為“誠”。
“誠”在較早的觀念里,存在著兩重屬性。誠,是本植于人心的,是人內在重要的德行,但是同時,誠又具有對人自身的超越性,可以與自然鬼神相交感,是人外在行為的一大指南。
對于誠的記載,還可見于《易傳》。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君德也。”
……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雖危無咎矣。”⑩
——《易傳·乾卦》
《易傳·乾卦》在“九二”爻中,我們上面的論點得到了印證,在這里“誠”與“德”是對舉的,可見,《左傳》和《尚書》之中關于人神的思想是可以共通的。
《易傳》認為誠德,對于人心的邪念有化解和抵抗作用,這對于“龍”的發展是十分有利,所以“九二”象為“利見大人”。進而《易傳》把誠德稱為“君德”,此處對于“誠”的事用,已經有了認知,對于人的言行提出了規范和要求,那就是“言善信,行必謹”。
在“九三”爻中,“誠”已經觸及到了更深的層面。“誠”已經開始與個人修養相結合,只是還比較粗糙。一方面,《易傳》認為誠德的建立要靠對言辭的修養,要靠對言的踐行;另一方面,認為“誠”的修養,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需要自始至終堅持。
此時,有關于“誠”的觀念的內涵,已有新的擴展。誠,不但是靜態的品德,更是動態的修養,修養中要加強自身的言與行的要求,這樣才能不斷修正自我,提升自我。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大學章句集注》
《大學》將“誠”提升到更重要的地位,提出“誠意”,將之作為修身進業的八條目。其對于“誠”觀念的發揮,是與“慎獨”的觀念相聯系的,主張君子的修養在于能夠關照己心己念,排除不善,真誠審視自我。《大學》認為,這種狀態便是意念的真誠,是“正心修身”的前提和起點。“誠”的觀念在此和其他的修養觀念已然組成了有機的統一體。
綜上可以知道,先民關于“誠”的認知,起源很早。而對于“誠”觀念的重視和崇尚也是一個由來已久的過程。《中庸》將“誠”作為個人修養的核心,也正是得益于此。
3 《中庸》之中有關“誠”的思想
“誠”觀念在《中庸》之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發揮。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中庸章句》
《中庸》首次提到“誠”是在此。“誠”依然是與祭祀鬼神相聯系,正是通過這種祭祀的儀式來體現。《中庸》認為祭祀活動中的虔誠與莊重就是“誠”的形象體現。這種細節盡管不容易把握,但卻肯定了“誠”是存在于人心的。并且,“誠”的特征就是流露于細微之處。這是《中庸》對于“誠”觀念的基本立場。正是如此,《中庸》認為誠是無法掩蓋的事實。朱熹有鑒于此,認為為學也應該注重對于心境的要求,將這種“誠”的心境轉化為“敬”的態度。他在《答胡廣仲書》中提到:“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圣學始終之要。”他認識到“誠”乃是人的求學的心境,必須加以重視。只有做到“持守堅定,涵養純熟”,才能知求學之真趣。
此處,誠雖然也是和鬼神祭祀相聯系,但已不同先前。《中庸》之“誠”是細節的形象顯現,透過細節,從而將“誠”從玄虛的理念落實到很具體的心境。這反映了“中庸之誠”在人性認知上的突破,也透露了“誠”觀念轉向內在心性自身的探究。
在下位不獲乎上,……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庸章句》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于上,……反身不誠,不悅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離婁》
《中庸》此章與《孟子》對“誠”觀念的表述相近,但有同有異。兩者皆認為誠是天之道,誠是自然賦予人的天性。正如《中庸》一個重要特征便是主張“性自命出,命受于天”。這里“中庸之誠”是對于儒家思想傳統的繼承和確認。但同時也存在損益,突出表現為“人道”的理解。《中庸》認為“誠之者,人之道也”,人是誠的踐行者;而《孟子》認為“思誠者,人之道也”,人是有志于誠。區別在于,“中庸之誠”帶有明顯的實踐傾向,不是停留于對“誠”的認識,而是要把“誠”落實到實踐中去。兩者相較,“中庸之誠”是明顯的突破。正是如此,兩者在“誠”的思想上也有了區別。《孟子》只做了簡單的結論,誠可以驅動人性修養。而《中庸》則更為深刻:“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從天性上講,誠能夠發育人的自覺、自我體認;從后天上講,人在實踐中能夠“擇善固執”,從而完善自我修養。
“中庸之誠”在承續儒家傳統的前提下,對于“誠”觀念進行深化,使得“誠”的含義擴展到“誠”的認知和“誠”的實踐。從中發現了人性中“自覺”“自知”等要素,這對于儒家的心性論和修養論可說是一大貢獻。
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中庸章句》
“誠者,理之實然,致一而不可易也。天道無勉無思,然其中其得,自然而已。”
——《二程集》
“中庸之誠”在涉及到天人關系的時候,又有新的創新。在早期,誠觀念伴隨鬼神觀念而生,天是人格化的天。而在《中庸》之中,此時的“天地”,已轉變為自然萬物。更確切的說,當之和人性修養相對舉的時候,則已然成為了“義理之天”,即天道的法則。正是這種轉變,“誠”觀念下的修養,才能實現天人關系的合一,完成從“盡己天性”到“與天地相參”的修身理想。后來程頤直接就認為“誠”是天理實際內容的體現,是“理之實然”。這預示了在“中庸之誠”已然擺脫了原始神秘外衣,轉向對于義理之學的演繹。
“誠”觀念下的天人關系,脫胎于遠古祭祀活動,只是其所闡發出的義理賦予了人性修養更為龐大的格局,也賦予“誠”觀念更深一層的靈魂。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中庸章句》
君子養心莫善于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
——《荀子·不茍》
“中庸之誠”對于“誠”觀念進行了細化和分類。這主要體現在《中庸》中的“曲誠”思想。《中庸》認為,誠的修養是一個階段化的過程,經歷“形”“著”“明”“動”“變”“化”的六個階段,最終達到至誠。這為誠的修養劃分出了不同的層次,也使得誠的踐行變得更加明晰。這與荀子的看法異曲同工。荀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帶有強烈社會責任感,所以荀子的“誠”觀念包含了“守仁”“行義”的具體對應,進而以形(存意)和理(求思)作為個人修養的途徑。這種具體事用的考量,也是對于“誠”之修養的重要補充。誠的本質是一致,然而誠的修養卻必然要經歷一個由不完善到完善的過程。
“中庸之誠”可以劃分為三個維度,從對象上講,“誠”開始關注于人具體行止的剖析和認知;從傳承上講,“誠”是因于儒道傳統之上的突破和創新;從功用上講,“誠”是心性修養實踐上的總結和確證。
4 后代對中庸“誠”觀念的發展
通過前文分析,誠是中庸思想的核心。那么后世“誠”觀念又有怎樣變化呢?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
——《毛詩序》
詩之道所以能有此三事者,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精誠之至,以類相感。
——《毛詩注疏·卷一》
《毛詩》認為,詩是人情濃烈的升華,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又《毛詩注疏》所說“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情即是誠,“精誠”乃是人感性的情感體驗。透過此,又看到“誠”觀念蛻變的又一方向。
唐代李翱十分推崇《中庸》,他關注到誠的感性因素,對中庸思想作出了性情之辨。李翱在《復性書》中認為性是天命所生,包含圣人之品,但常常因為“情”的遮蔽,迷失大本。據此,李翱提出了“性善情惡”學說。但李翱對于性情的看待又是辯證的,認為兩者不能截然分開,“情不能自生,乃是由性生發,性不能自顯,需要有情而表達”,所以圣人善于修斂自身情感,從而導情歸性,回復天性中的“至誠”。這種對于情感因素的引入,是對于內在心性更為深入的解析,也是對于中庸思想思辨的探索。這也讓誠的觀念汲取到了新的生機和活力。
北宋蘇軾對于情感因素又有其獨特視角。這與《毛詩》非常一致。
蘇軾在其著作《中庸論》中認為,圣人之道,其本是人感性的情感內容。因此君子要追求自身修養(君子欲誠),那就必然要重視此本源,否則,只知道勉強自身,而不知投入自身情感,那就是“雖欲誠之,其道無由”。
在此,“誠”觀念被賦予更多感性內容,與情感密切聯系。對情感內容的關注,使誠觀念更加鮮活貼近人心。至此,誠觀念的內涵意蘊已然較為立體和豐滿。
蘇軾的這種觀點,也為中庸思想的解讀帶來了新見,這表現在誠明關系的認知問題上。
歷來學者肯定“自明誠”,認為明白了道理,然后自身才能夠修養。誠身有道,這符合日常的認知。朱熹就認為“先明乎善,而后能實其善”;但有關于“自誠明”,則多認為沒有現實操作性。朱熹將之歸于“圣人之德”,僅僅是一種可能性的感嘆。
蘇軾對此著重發揮情感在認知中的作用。對于“自誠明”有了一番全新解釋。蘇軾認為《論語》中“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之”是因為心中有誠。求學之所以有先后之別,就是感情對于人自身積極性的調動,“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自身有誠,就必然傾注更多感情。關于此,《孟子·弈秋》有其例證,兩個人學習對弈,結果天壤之別,其原因便是“一人專心致志”,“一人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個人主動性在學習認知中的作用彰顯無遺。這種情感對于認知的促進作用,一方面更能調動人的主動性,另一方面讓人在認知探索上走得更遠更深。
通過蘇軾的觀點,可以看到“自誠明”與“自明誠”之間并不沖突,而是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對認知過程進行分析。兩者之間相輔相成、互為表里。
《中庸》是記載儒家修養之道的重要經典。而“誠”的觀念更是其精神的內在核心。只有對于“誠”的思想內蘊仔細分析和探究,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庸”之中深邃而高遠的心性修養之道。
注釋:
① 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9,第63頁。
② 同上,第113頁。
③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2,第17頁。
④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6.6,第1552-1553頁
⑤ (漢)許慎,《說文解字新訂》(藏克和、王平校訂),北京:中華書局,2002,第145頁。
⑥ (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50頁;
⑦ (漢)鄭玄,《十三經古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5,第103頁。
⑧ 同上,第89頁。
⑨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10,第309-310頁。
⑩ 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7,第8-9頁。
[1] 彭婷.《中庸》誠學研究[D].湖南:湖南師范大學,2013.
[2] 趙興余.蘇軾與司馬光《中庸》診釋比較研究[D].陜西:陜西師范大學,2011.
[3] 向帥.儒家“誠明”之學的源與流[J].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14,30(7):27-33.
[4] 向楠.《中庸》心性修養論淺述[D].湖北:華中科技大學,2011.
[5] 韓麗華.回歸誠明——李翱《復性書》研究[D].江蘇:蘇州大學,2012.
[6] 陳來.朱熹《中庸章句》及其儒學思想[J].中國文化研究,2007:1-11.
[7] 鄭熊.宋儒對《中庸》的研究[D].陜西:西北大學,2007.
[8] 李冉.由《復性書》淺析李翱的心性論思想[J].中共太原市委黨校學報,2012,5:67-69.
[9] 米文科.“自誠明”何以可能——張載思想中的“自誠明”與“自明誠”問題[J].唐都學刊,2014,30(2):36-40.
[10] 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5.
[11] 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5.
[12]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
[13] 程頤程顥.二程集[M].北京:中華書局,2016.
[14]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7.
[15]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十三經注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16]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8.
高欣(1989-),男,漢族,四川天全人,四川師范大學中國哲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哲學佛教哲學。
B244
A
1672-5832(2017)12-017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