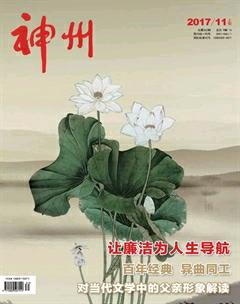以蘇黃詩中煎茶詩句試品江西詩派蘇黃熱愛生活的細節
丁翱林
在江西詩派中當屬黃庭堅的詩最具有文人氣和書卷氣,在他現存的一千九百多首詩中約三分之二是思親懷友、感時抒懷、描摹山水、題詠書畫且人文意象和自然意象都格外密集,使得他的詩更加充滿人文色彩。如茶,茶是文人雅致生活不可或缺的,黃詩的《以小龍團及半挺贈無咎并詩用前韻》關于對煎茶聲有著這樣的描寫:“曲幾團蒲聽煮湯,煎成車聲繞羊腸。”意思是:跪坐在團蒲上聽煮茶,煮茶的聲音啊就像車繞羊腸小道的聲音。這份閑適和悠然,細品之,便會體會到其中的樂趣和黃對生活的熱愛和觀察入微,車過羊腸小路的聲音是日常大部分的人都聽過的,而與常人不同的是,黃在參與文人活動——煎茶時竟然可以聯想到此等妙語,不由讓人拍案叫絕。
黃庭堅所在的江西是南宗禪的圣地,,所謂“一盞一葉有禪思”,其對茶和茶事之道皆是較為熟悉的,他在《寄新茶與南禪師》中有著“筠焙熟香茶,能醫病眼花。因甘野夫食,聊寄法王家。石缽收云液,銅缾煮露華。一甌資舌本,吾欲問三車”。先說茶有提神明目的功效,并用謙遜的語氣表達自己對佛門以及高僧的尊敬和仰慕之情,意在說明唯有以茶為趣的清雅才堪堪配得上佛門的清幽。詩中“三車”是經典的佛門術語,以三車喻三乘,意為以羊車喻聲聞乘,以鹿車喻緣覺乘,以牛車喻菩薩乘。禪與詩都極為重視內心的體驗和對生活的感悟,重視妙語,啟示和象喻。試問如若不是一個十分熱愛生活又對人生有著積極向上的人,何以創作出絕句,如何保持清明的禪心呢?黃庭堅將飲茶的愜意妙覺和習禪的妙思奇想自然的融會貫通,做到無處不禪意,何處無茶。如此,茶事便是佛事,佛事亦為人事,一盞一壺,一葉一水皆可人禪。
說起黃庭堅便不得不提的一位詩人,他既是黃的友人、知己、老師,又是黃的勁敵、對手,他們并稱‘蘇黃。蘇軾也愛在閑暇時煎茶,也對煎茶有過細致的描寫,在《汲江煎茶》中:“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汲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處腳,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碗,坐聽荒城長短更。”這首詩寫于 北宋哲宗元符三年(一一OO)的春天,蘇軾被貶在儋州(今海南島儋縣);詩中描寫了作者月夜江邊汲水煎茶的細節,具體地反映了被貶遠方的寂寞心情。“此詩甚奇,道盡烹茶之要。且茶水非活水則不能鮮馥。東坡深知此理矣。”[1]
第一句說,煮茶最好用流動的江水(活水),并用猛火(活火)來煎。所謂 “茶須緩火炙,活火烹”,緩火就是炆火(微火),活火是指猛火。因為煎茶要用活水,詩人只好到自己提著通,帶著大瓢到江邊釣魚石上汲取深江的清水。
第二句寫月夜汲水的情景,他去汲水的時候,月影倒映在江水之中;用大瓢取水就好像把水中的明月也貯藏到瓢里了,一起提著回來倒在水缸(甕)里;再用小水杓將江水(江)舀入煎茶的陶瓶里。這是煎茶前的準備活動,寫得很細致、很形象,很有韻味。
第三句寫煎茶:煮開了,雪白的茶乳(白沫)隨著煎得翻轉的茶腳漂了上來。(據會品茶的人說,好茶沏了呈白色,這里翻“雪乳”,說明他沏的是好茶。)斟茶時,茶水瀉到茶碗里,颼颼作響,像風吹過松林所發出的松濤聲。(他在《試院煎茶》詩里說“颼颼欲作松風聲”,也是用“松風”來形容茶聲。)此處雖略帶夸張,卻十分生動形象,同時更能從側面反映他在貶所的小屋里,夜間十分孤獨、寂靜,所以斟茶的聲音也顯得特別響。
第四句寫喝茶,說要搜“枯腸”只限三碗恐怕不易做到。這句話是有來歷的。唐代詩人盧仝《謝孟諫議寄新茶》詩說:“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七碗吃不得,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寫詩文思路不靈,常用“枯腸”來比喻。搜索枯腸,就是冥思苦索。盧仝詩說喝三碗可以治“枯腸”,作者表示懷疑,說只限三碗,未必能治“枯腸”,使文思流暢。看來他的茶量要超過“三碗”,或許喝到盧仝詩中所說的“七碗”。他在另一首詩中就說,“且盡盧仝七碗茶”。喝完茶干什么?沒事。所以最后一句說,喝完茶,就在這春夜里,靜坐著挨時光,只聽海南島邊荒城里傳來那報更(夜間報時)的長短不齊的鼓聲。
這首詩對煎茶活動的描寫細膩生動。從汲水、舀水、煮茶、斟茶、喝茶到聽更,全部過程仔仔細細、繪影繪聲,修辭更是出奇制勝。通過這些細節的描寫,詩人被貶后寂寞無聊的心理,很生動地表現出來了。
蘇軾極為嗜好飲茶,茶與他而言是助其詩意暢流的靈藥,是他忙里偷閑的益友,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他對茶就似李白嗜酒一般無可救藥。他作詩歌時要喝茶“皓色生甌面,堪稱雪見羞;東坡調詩腹,今夜睡應休”《贈包靜安先生茶二首》;睡前要喝茶“沐罷巾冠快晚涼,睡余齒頰帶茶香”《留別金山寶覺圓通二長老》:;睡醒了也要喝茶“春濃睡足午窗明,想見新茶如潑乳”《越州張中舍壽樂堂》。他夜晚辦事還要喝茶:“簿書鞭撲晝填委,煮茗燒栗宜宵征”《次韻僧潛見贈》;可謂是視茶如命了。更為了他心愛的茶寫下一首《水調歌頭》,詞云:“已過幾番雨,前夜一聲雷。旗槍爭戰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枝頭雀舌,帶露和煙搗碎,結就紫云堆。 輕動黃金碾,飛起綠塵埃。 老龍團,真鳳髓,點將來。兔毫盞里,霎時滋味舌頭回。 喚醒青州從事,戰退睡魔百萬,夢不到陽臺。兩腋清風起,我欲上蓬萊。”詞中詳細記詠了采茶、制茶、點茶、品茶,對茶烹制過程可謂是繪聲繪色,情趣盎然。蘇軾愛茶至深,在《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烙新茶》詩里,將茶比作“佳人”。詩云:“仙山靈草濕行云,洗溫香肌粉末勻。 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林春。要知冰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勿笑,從來佳茗似佳人。”因而對于烹茶之事更是精到,好茶必須配好水即“精品厭凡泉”,活水須用活火烹,對水溫也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不能有些許差池。對煮水的器具和飲茶用具,蘇軾也有講究。“銅腥鐵澀不宜泉”,“定州花瓷琢紅玉”。甚至在宜興時,還設計了一種提梁式紫砂壺。后人為紀念他,把此種壺式命名為 “東坡壺”。“松風竹爐,提壺相呼”,即是蘇軾用此壺烹茗獨飲時的生動寫照。
這一對摯友,雖然一生磕磕絆絆,但是他們都坦然面對,泰然處之,對于生活依舊充滿了熱情和期盼。同是一代文豪,對于挫折和坎坷的無懼,對于每一日的珍惜和對生活的熱愛令人折服。在宋代江西詩派中多得是文人騷客,對茶表達喜愛之情的詩句更是不絕于耳,在煮茶的名家的影響下,茶的文化將會更加源遠流長、博大精深。
參考文獻:
[1]出自胡仔的《?溪漁隱叢話》卷十一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