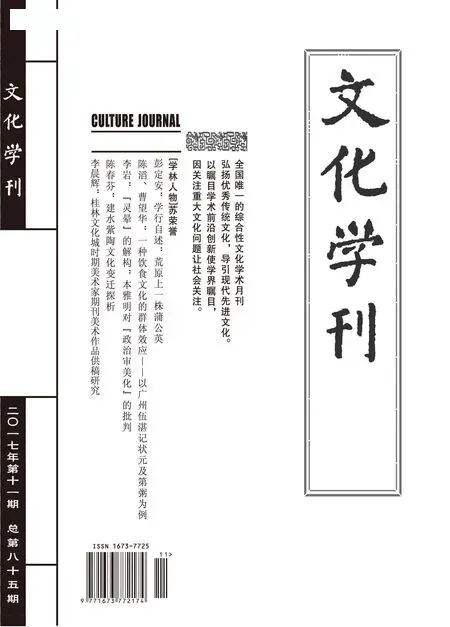敘事視角下《慈悲》中麗貝卡女性話語(yǔ)權(quán)的建構(gòu)
武少
(山西工程技術(shù)學(xué)院基礎(chǔ)部,山西 陽(yáng)泉 045000)
敘事視角下《慈悲》中麗貝卡女性話語(yǔ)權(quán)的建構(gòu)
武少燚
(山西工程技術(shù)學(xué)院基礎(chǔ)部,山西 陽(yáng)泉 045000)
本文借助申丹教授提出的敘事視角理論,以選擇性全知視角為切入點(diǎn),分析《慈悲》中麗貝卡為顛覆男權(quán)制和建構(gòu)女性話語(yǔ)權(quán)所做的掙扎和努力,進(jìn)而解讀敘事視角對(duì)建構(gòu)女性話語(yǔ)權(quán)的作用,彰顯莫里森普適的女性主義觀。
敘事視角;《慈悲》;麗貝卡;女性話語(yǔ)權(quán);建構(gòu)
一、敘事視角及《慈悲》
敘事視角是后經(jīng)典敘事學(xué)中文本闡釋的一種重要方法,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對(duì)其進(jìn)行了不同的分類(lèi)。在《小說(shuō)的敘事視角》一文中,諾爾曼·弗里德曼提出了敘事視角“八分法”:兩類(lèi)有無(wú)“作者介入”的全知敘述;兩類(lèi)“第一人稱(chēng)”敘述;兩類(lèi)“選擇性全知”敘述和兩類(lèi)客觀敘述。熱奈特在《敘述話語(yǔ)》一書(shū)中將敘事視角分為三類(lèi),即零聚焦(敘述者>人物)、內(nèi)聚焦(敘述者=人物)和外聚焦(敘述者<人物)。
在弗里德曼和熱奈特的基礎(chǔ)上,國(guó)內(nèi)敘事學(xué)領(lǐng)域的權(quán)威申丹教授進(jìn)行了新的分類(lèi):觀察者處于故事之外的外視角和觀察者處于故事之內(nèi)的內(nèi)視角。選擇性全知視角是指“全知敘述者選擇限制自己的觀察范圍,往往僅揭示一位主要人物的內(nèi)心活動(dòng)”[1],因此,這種敘事視角屬于外視角。
在莫里森的大部分作品中,黑人女性一直是其塑造的經(jīng)典形象,但《慈悲》,莫里森將敘事視角轉(zhuǎn)向殖民地初期生活在黑人文化圈中的白人女性——農(nóng)場(chǎng)女主人麗貝卡。《慈悲》中體現(xiàn)的是蓄奴制形成之前,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遭受的創(chuàng)傷。在這部作品中,莫里森表現(xiàn)了對(duì)女性生存的普適性關(guān)懷,將筆鋒直指下層白人女性,以麗貝卡為代表的白人“他者”不但因?yàn)殡A級(jí)地位的懸殊,而且因?yàn)樾詣e原因處于他者地位。“《慈悲》描寫(xiě)了各色人等扛著靈與肉的枷鎖和他們的解脫之道。”[2]種族不再是他者產(chǎn)生的原因,白人女性需要跨越性別政治進(jìn)行自我救贖,而麗貝卡的救贖之道是顛覆宗教傳統(tǒng)。
長(zhǎng)期以來(lái),女性在男權(quán)社會(huì)中處于他者地位,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說(shuō):“他是主體,是絕對(duì),她是他者”[3]。這種無(wú)法言說(shuō)的精神創(chuàng)傷使女性不得不內(nèi)化這種他者地位,因此逐漸失去了話語(yǔ)權(quán)。麗貝卡出生于英國(guó)下層階級(jí)家庭,父親急于讓女兒出嫁來(lái)減輕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而雅各布恰好在尋求這樣一位妻子,因此,在父權(quán)制的迫害下,麗貝卡獨(dú)自坐船從英國(guó)來(lái)到弗吉尼亞,成了名副其實(shí)的“郵購(gòu)新娘”。盡管她是一名白人女性,但其生活在黑人文化圈中同樣遭受著種種壓迫,她的失聲亦即她話語(yǔ)權(quán)的缺失。婚后,她成為了以雅各布為代表的男權(quán)文化的附屬品,更加劇了她話語(yǔ)權(quán)缺失的窘境,因此,對(duì)麗貝卡來(lái)說(shuō),建構(gòu)女性話語(yǔ)權(quán)就顯得尤為重要。
本文以申丹教授的敘事視角為理論框架,以選擇性全知視角為切入點(diǎn),對(duì)小說(shuō)中刻畫(huà)麗貝卡形象的敘事視角進(jìn)行分析,進(jìn)而詮釋麗貝卡為建構(gòu)女性話語(yǔ)權(quán)做出的掙扎和努力。
二、選擇性全知視角下的麗貝卡
敘述者采用選擇性全知視角來(lái)展現(xiàn)麗貝卡對(duì)雅各布的內(nèi)心情感。選擇性全知視角是指“全知敘述者選擇限制自己的觀察范圍,往往僅揭示一位主要人物的內(nèi)心活動(dòng)”。[4]敘述者選擇限制自己的觀察范圍,將麗貝卡作為全知敘事的見(jiàn)證人,僅僅從麗貝卡的角度揭示雅各布所代表的男權(quán)給她帶來(lái)的創(chuàng)傷。
“雅各布大概認(rèn)為,給她一個(gè)與帕特麗仙年齡相仿的女孩,會(huì)讓他開(kāi)心。可事實(shí)是,這侮辱了她。什么都無(wú)法取代,亦不應(yīng)取代最初的那一個(gè)。”[5]雅各布試圖用弗洛倫斯來(lái)醫(yī)治麗貝卡失去女兒后受傷的心靈,可他未曾想到,麗貝卡的創(chuàng)傷更多的是由父權(quán)制下的男權(quán)社會(huì)所帶來(lái)的,她的生命軌跡中一直充斥著像雅各布或她父親式的人物。作者在表現(xiàn)貝利卡同雅各布關(guān)系惡化的同時(shí),也表達(dá)了貝利卡對(duì)父權(quán)制的厭惡。麗貝卡關(guān)于郵輪的回憶同樣表現(xiàn)了這一點(diǎn)。在前往弗吉尼亞的郵輪上,麗貝卡和她的船友們被束縛在黑暗中,看不到天空,承受著男性權(quán)力的空間規(guī)訓(xùn),話語(yǔ)權(quán)的缺失剝奪了她們的女性立場(chǎng),一群社會(huì)棄兒相互鼓勵(lì)著來(lái)抗?fàn)帯八摺薄T邴愗惪磥?lái),“女人是屬于男人并為男人而存在的,但在那些短暫的時(shí)刻,她們二者皆非”[6]。
在雅各布的農(nóng)場(chǎng)上,已“升級(jí)”為女主人的麗貝卡依然沒(méi)有獲得認(rèn)同感。她的白皮膚帶給她的不是好運(yùn),而同樣遭受著同農(nóng)場(chǎng)上其他奴隸一樣的歧視和壓迫。在失去四個(gè)孩子和丈夫之后,無(wú)兒無(wú)女的陰云與孤獨(dú)的襲擊使麗貝卡未能禁得起撒旦的誘惑,開(kāi)始信仰基督教。“作為白人文化的內(nèi)在基石,基督教是統(tǒng)治階級(jí)用來(lái)束縛被統(tǒng)治者的精神手段,固化了信仰者的思想觀念,是實(shí)行精神殖民的必要形式。”[7]麗貝卡找到了自己精神上可依賴(lài)的另一個(gè)“男性主體”。對(duì)于自己受到的折磨和精神的絕望,她聯(lián)想到了約伯的故事,但是在麗貝卡眼中,約伯的痛苦只是想引起上帝的注意。獨(dú)在異鄉(xiāng)的她同樣也需要上帝的關(guān)心和憐憫,但上帝卻讓她失望了,對(duì)于她們這些女約伯來(lái)說(shuō),“救贖是被拒絕的”[8]。上帝虛假的安慰并沒(méi)有讓她走出創(chuàng)傷,“我認(rèn)為上帝并不知道我們是誰(shuí)。要是他知道,我覺(jué)得他會(huì)喜歡我們的,不過(guò),就我看,他并不了解我們”[9]。麗貝卡對(duì)上帝的失望衍射了小說(shuō)主題“慈悲”的含義。莫里森的大部分作品和《圣經(jīng)》中的愛(ài)和關(guān)懷有關(guān),例如《寵兒》和《所羅門(mén)之歌》,但這部小說(shuō)中提及的上帝卻沒(méi)那么的和藹、友善,正如弗洛倫斯的媽媽所說(shuō),“這是人類(lèi)施與的慈悲”[10]。
小說(shuō)中,敘述者通過(guò)顛覆基督教傳統(tǒng)來(lái)表達(dá)麗貝卡的女性主義立場(chǎng)。麗貝卡的父母無(wú)論對(duì)待彼此還是子女都表現(xiàn)得麻木而冷漠,卻把火一般的熱情全都留給了宗教事務(wù),但諷刺的是,她對(duì)上帝的理解卻十分模糊,認(rèn)為“那是由某種奇妙的憎惡點(diǎn)燃并維持的一團(tuán)火焰,對(duì)陌生人的點(diǎn)滴寬容都威脅著要澆滅那團(tuán)火焰”[11]。所以當(dāng)她和另外七個(gè)“白人他者”被分配到“祈禱”號(hào)輪船的船艙底層時(shí),她并沒(méi)有因?yàn)橐簧磉h(yuǎn)赴外國(guó)去嫁給一個(gè)陌生人的害怕和恐懼而向上帝祈禱,而是和她們湊在一起,談笑風(fēng)生,并且慷慨地把自己的奶酪和餅干與她們分享,短暫的“姐妹情誼”為旅途平添了不少輕松和愉悅。共同的他者命運(yùn)使這些女性之間產(chǎn)生了一種無(wú)形的凝聚力,因此在麗貝卡病重時(shí)仍然在夢(mèng)境里見(jiàn)到了當(dāng)年與她同舟共渡的那份“姐妹情誼”。
敘述者選擇從全知敘述者的角度透視麗貝卡的內(nèi)心活動(dòng),彰顯了莫里森高超的敘事技巧,同時(shí)表現(xiàn)了麗貝卡艱難并堅(jiān)定的女性主義立場(chǎng)。
三、結(jié)語(yǔ)
女性話語(yǔ)權(quán)的建構(gòu)是莫里森作品的普遍主題,她筆下的女性隱忍而堅(jiān)強(qiáng),在黑暗中找尋自我之路,建構(gòu)自我主體。莫里森在《慈悲》中表現(xiàn)了她在種族書(shū)寫(xiě)上的協(xié)商意識(shí),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從底層黑人女性轉(zhuǎn)向底層白人女性,直接描寫(xiě)了白人女性的他者空間,更突出地表現(xiàn)了她普適的女性主義觀。由于麗貝卡的解脫之道建立在性別政治束縛的基礎(chǔ)上,因此,存在著一定的局限,關(guān)于女性話語(yǔ)權(quán)建構(gòu)的方式還有更多的思考空間。
[1][4]申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xué):經(jīng)典與后經(jīng)典[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95.95.
[2]王守仁,吳新云.超越種族:莫里森新作《慈悲》中的“奴役”解析[J].當(dāng)代外國(guó)文學(xué),2009,(2):43.
[3]西蒙娜·徳·波伏娃.第二性[M].鄭克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9.
[5][6][8][9][10][11]Toni Morrison.A Mercy[M].New York:Vintage Books,2008.96.85.92.80.167.74.
[7]王麗麗.走出創(chuàng)傷的陰霾——托妮·莫里森小說(shuō)的黑人女性創(chuàng)傷研究[M].黑龍江:黑龍江大學(xué)出版社,2014.97.
【責(zé)任編輯:王崇】
I712.074
A
1673-7725(2017)11-0011-03
2017-09-05
本文系山西工程技術(shù)學(xué)院校級(jí)基金課題“托尼·莫里森近期作品中女性話語(yǔ)權(quán)的建構(gòu)”(項(xiàng)目編號(hào):201706001)的研究成果。
武少燚(1989-),女,山西太原人,助教,主要從事英美文學(xué)研究。

漢 長(zhǎng)生無(wú)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