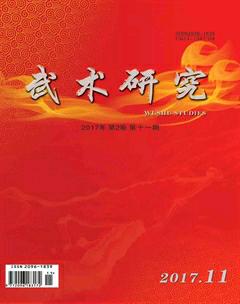蒙古族傳統(tǒng)體育文化尋繹
田帥+劉繼武
摘 要:蒙古族是我國(guó)歷史悠久而又擁有燦爛文化的民族。文章運(yùn)用文獻(xiàn)資料法、邏輯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從歷史學(xué)的視角對(duì)蒙古族傳統(tǒng)體育的文化起源進(jìn)行梳理和分析。得出:蒙古族傳統(tǒng)體育文化是蒙古族燦爛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民族的草原游牧文化、宗教文化、節(jié)慶民俗文化和娛樂(lè)游戲文化是蒙古族傳統(tǒng)體育文化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基礎(chǔ)和源泉,反映了蒙古族為適應(yīng)自然環(huán)境而創(chuàng)造出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
關(guān)鍵詞:蒙古族 傳統(tǒng)體育 游牧文化 宗教文化
中圖分類號(hào):G85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2096—1839(2017)11—0113—03
1 草原游牧文化
蒙古族是我國(guó)最為著名的游牧民族。據(jù)史書記載:游牧部族鮮卑人的一支,稱為“室韋”,通常被認(rèn)為與蒙古族有關(guān),直到13世紀(jì)“蒙古族“才真正形成了一個(gè)民族共同體。 [1]早期的蒙古人沿著額爾古納河,從呼倫貝爾草原,渡過(guò)呼倫河,向西進(jìn)到了斡難河的源頭,這一地域后來(lái)一直成為蒙古族的中心活動(dòng)區(qū),深刻地影響著其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在許多的歷史文獻(xiàn)中都有對(duì)“游牧文化”的記載,南北朝時(shí)期的民歌《敕勒歌》中寫道:“刺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fēng)吹草低現(xiàn)牛羊。”又如《黑龍江志》中記載:“蒙人專賴畜牧為生計(jì),問(wèn)起貧富,則數(shù)畜以對(duì)。”自古以來(lái),蒙古族就是游牧于蒙古高原的眾多少數(shù)民族之一,他們過(guò)著“逐水草而牧,冬夏遷徙不定”的生活,草原畜牧業(yè)是蒙古族人民最主要的生產(chǎn)方式。長(zhǎng)期以“車馬為家“的遷徙生活,加上嚴(yán)酷的自然環(huán)境,蒙古族人必須具備強(qiáng)健的體魄、頑強(qiáng)的毅力以及高超的技藝才能滿足游牧生產(chǎn)生活的需要。
蒙古族人在長(zhǎng)期的游牧生產(chǎn)生活中創(chuàng)造出了許多有益于增強(qiáng)體魄和提高技術(shù)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運(yùn)動(dòng)項(xiàng)目,如賽馬、賽駱駝、套馬、馬上騎射等。據(jù)《清稗類鈔·技勇類》記載:蒙古族人“不論男女老幼,未有不能騎馬者,其男女孩童自五六歲即能騎馬,馳驅(qū)于野”。[2]蒙古族人從孩童時(shí)期就開始練習(xí)騎馬,騎馬是蒙族人的傳統(tǒng),演繹出了獨(dú)特的“馬文化”,素有“馬上行國(guó)”之美稱。賽馬比賽是具有濃郁草原風(fēng)情的比賽項(xiàng)目,比賽一般分為走馬和跑馬兩種。走馬主要比賽穩(wěn)健、速度、耐力、和美觀。跑馬與走馬不同,比馬的速度和耐力,以先到達(dá)終點(diǎn)者為勝。比賽前乘馬要做好裝飾,馬身上要刷洗干凈,馬的鬃尾要梳理幾條辮子,馬鬃馬尾都要系上彩帶,騎手要穿戴輕便,頭上要纏彩綢或戴紅纓帽。賽手們?nèi)雸?chǎng),由祝頌人致祝詞,彩旗一搖,眾駿馬猶如出弦之箭,奮蹄騰飛,騎手們則躍馬揚(yáng)鞭,各顯神通。頓時(shí)出現(xiàn)萬(wàn)馬奔騰,大地顫動(dòng),觀眾歡呼雀躍,聲震田野的動(dòng)人景象。按照蒙古族的傳統(tǒng),比賽結(jié)束時(shí),取得名次的馬匹在大會(huì)主席臺(tái)前依次排好,由德高望重的長(zhǎng)者給獲獎(jiǎng)的騎手獻(xiàn)哈達(dá),給乘馬掛彩帶,并往馬頭或者馬身上潑灑奶酒以示祝福,還要由蒙古族歌手高聲朗誦《贊馬詞》,然后給獲獎(jiǎng)馬匹賞予稱號(hào),給獲獎(jiǎng)騎手授予獎(jiǎng)品。[3]除了賽馬以外,賽駱駝也是蒙古族在草原游牧生活中形成的傳統(tǒng)體育項(xiàng)目。
2 宗教文化
蒙古族人從遠(yuǎn)古就生活在廣袤的北方高原上,由于當(dāng)時(shí)人們生活條件艱苦,智力和生產(chǎn)力均處在很低的水平,加之人們對(duì)于種種自然現(xiàn)象的不解,如打雷、閃電、自然災(zāi)害、牲畜死亡以及人的生老病死等。這些自然現(xiàn)象使得古代蒙古族人倍感恐懼,不得不相信命運(yùn),認(rèn)為“萬(wàn)物有靈”,從而把自然現(xiàn)象、自然力和自然物當(dāng)成有意志、有能力支配自己的某種神秘力量和神圣事物去依賴和崇拜[4],希望能得到神靈的幫助和庇佑。
2.1 自然崇拜文化
在蒙古族薩滿教的宗教信仰中幾乎所有的自然現(xiàn)象和自然物都是人們崇拜的對(duì)象,其中天神和地神最受崇拜。據(jù)《蒙韃備錄》記載:“蒙古人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敬天。”對(duì)自然的崇拜是蒙古族人的內(nèi)心情感,而這種內(nèi)心情感的外化形式就是祭祀。
“ 祭敖包”是草原蒙古民族最隆重的祭祀,敖包是薩滿教神靈所居和享祭之地。[5]祭敖包每年按季節(jié)定期供祭,祭祀的神有天神、地神、雨神、河神、風(fēng)神、牛神、馬神等,祈求族人們平安幸福和生產(chǎn)豐收。祭祀時(shí),正南方向擺木桌設(shè)貢品,大喇嘛在正中間誦經(jīng),小喇嘛分坐兩旁敲奏古樂(lè),誦經(jīng)完畢,所有人跟隨大喇嘛繞敖包由東向西繞三圈,然后由大喇嘛將貢品拋給眾人分食。祭祀活動(dòng)結(jié)束后,人們開始舉行摔跤、射箭、賽馬、棋類、唱歌、跳舞、投布魯?shù)任捏w娛樂(lè)活動(dòng)。蒙古族的摔跤也叫博克,是蒙古族人民最喜愛的傳統(tǒng)體育項(xiàng)目之一。每逢比賽時(shí)選手們身穿“罩得戈”“套呼”,腳蹬高幫蒙古靴,有名望的摔跤手脖子上還佩戴著“江嘎”,穿上全套摔跤服的運(yùn)動(dòng)員跳著獅子舞步上場(chǎng),顯得威風(fēng)凜凜,氣勢(shì)十足,比賽獲勝的博克手將會(huì)獲得豐厚獎(jiǎng)勵(lì)。所有這些豐富的體育文化活動(dòng),作為蒙古族對(duì)大自然神靈的崇拜,人們?cè)趨⒓蛹漓牖顒?dòng)時(shí)、進(jìn)行比賽時(shí)心理上都有一種神圣感,希望在這個(gè)活動(dòng)中盡情歡愉,以取悅神靈,獲得好運(yùn)。至今,蒙古族摔跤深受蒙古族人的喜愛,有著良好的群眾基礎(chǔ)。
2.2 圖騰崇拜文化
在《蒙古秘史》中開篇就寫到:“成吉思汗的根祖是蒼天降生的孛兒帖赤納(蒼色狼)和他的妻子豁埃馬闌勒(白色鹿)。狼鹿相配孕育了蒙古族人,是蒙古民族的古老的起源傳說(shuō)之一。蒙古族古老的狼、鹿圖騰神話傳說(shuō)雖然難以尋覓,但是從北方民族史、蒙古歷史典籍中的有關(guān)記載來(lái)看,它更有可能反映的是一個(gè)存在過(guò)狼圖騰與鹿圖騰的民族。
狼圖騰崇拜現(xiàn)象幾乎為所有生息在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共有,蒙古族選擇狼作為本民族的圖騰,與蒙古族的生活環(huán)境、生活方式息息相關(guān)。蒙古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他們生活在大草原上,草原上的狼對(duì)于蒙古族人來(lái)說(shuō)是非常可怕的,狼生性機(jī)制敏捷、動(dòng)作迅速,它們往往團(tuán)隊(duì)作戰(zhàn)、協(xié)同搏斗,共同對(duì)抗進(jìn)犯的敵人,人們因恐懼而敬奉。“打布魯”運(yùn)動(dòng)就產(chǎn)生于蒙古族早期的狩獵生活中,“布魯”是投擲的意思,作為一種狩獵工具,它是用彎曲的小木棒制成,狀似鐮刀,用鋁、銅、鐵等金屬包扎或用鋁熔化后澆筑在木棒花紋處,居住在草原上的牧民常用布魯打低空飛鳥,擊地上走獸,后來(lái)才漸漸演變成了一項(xiàng)單純的體育娛樂(lè)活動(dòng)。因此,可以看出蒙古族人民在長(zhǎng)期與狼的斗爭(zhēng)及相處中,它們對(duì)狼的生活習(xí)性越來(lái)越了解,越來(lái)越親近,便選擇了狼作為自己民族的圖騰。狼圖騰不僅僅是一種圖騰的崇拜,也是一種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和發(fā)揚(yáng)。狼的崇拜使得蒙古族人的性格中具有狼的智慧和勇猛,也使得蒙古族人重視武力和崇尚勇武,狼圖騰文化也給蒙古族帶來(lái)了豐富的民族體育文化內(nèi)容。endprint
2.3 祖先崇拜文化
由自然崇拜到祖先偶像崇拜的轉(zhuǎn)化,是蒙古族草原游牧民在原始宗教信仰方面的一次變革。[6]古代的蒙古族人認(rèn)為:人有靈魂,人死而靈魂不亡,死去的人其靈魂以某種形式存在于宇宙間,它能夠給活著的人們以啟示,于是就產(chǎn)生了祖先崇拜。因此,人們會(huì)為死去的祖先舉行隆重的葬禮,并會(huì)按時(shí)祭奉供養(yǎng),表達(dá)對(duì)祖先亡靈的崇拜。祭成陵是蒙古族最隆重莊嚴(yán)的的祭祀活動(dòng),充分體現(xiàn)了蒙古蒙族對(duì)祖先的崇拜。祭成陵就是祭祀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是蒙古族人們崇敬的大英雄,被稱為“一代天驕”。祭祀分為日祭、月祭和季祭三種。一般只實(shí)行春祭。每逢祭日,蒙古族人便帶上牛、羊、酒、奶油、哈達(dá)等祭品,前往伊克昭盟境內(nèi)的成吉思汗陵祭祀。蒙古族經(jīng)典的民間舞蹈,如珠嵐舞、筷子舞、盅子舞、頂碗舞等就是成吉思汗祭祀活動(dòng)中的重要民俗體育文化內(nèi)容。這些習(xí)俗,在長(zhǎng)期的生產(chǎn)生活過(guò)程中,逐漸形成如今色彩鮮明的蒙古族傳統(tǒng)體育文化。
蒙古族人的祖先崇拜還表現(xiàn)在對(duì)民族英雄的崇拜,在蒙古人當(dāng)中關(guān)于民族著名射手、騎手、博克手的故事、傳說(shuō)和民歌非常之多,而且是人盡皆知。例如哲里木民歌《巴拉吉尼瑪扎那》里唱到:“巴拉吉尼瑪是英雄好漢,兩個(gè)扎撒克里他的英名橫貫,他們弟兄所到過(guò)的地方,頂帶花翎的王爺諾顏都提心吊膽。扎那是個(gè)孤膽英雄,他的英名威震扎撒克衙門,他們弟兄所到過(guò)的地方,頂帶花翎的王爺諾顏膽顫心驚。”這些民間文藝作品其實(shí)也都彰顯著人們對(duì)祖先的崇敬,對(duì)于熏陶蒙古族人,激勵(lì)他們成為草原英雄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蒙古民族的搏克、射箭等傳統(tǒng)體育運(yùn)動(dòng)都體現(xiàn)了蒙古族人先祖崇拜的文化心理,同樣也表現(xiàn)了蒙古族人民崇尚勇敢、堅(jiān)強(qiáng)、彪悍、尚武的民族風(fēng)貌。
3 節(jié)日習(xí)俗文化
3.1 節(jié)日文化
節(jié)日文化是民族傳統(tǒng)文化構(gòu)成諸要素中具有普遍性、廣泛性、豐富性的要素,其內(nèi)容幾乎包括了民族生活和人類文化的方方面面。[7]節(jié)日是蒙古族表現(xiàn)民族傳統(tǒng)體育文化的窗口,每逢節(jié)日到來(lái),各種各樣的體育活動(dòng)紛紛開展。“那達(dá)慕”大會(huì)是蒙古族最盛大的傳統(tǒng)節(jié)日,帶有濃郁的游牧民族特色,它在蒙古族人民心中古老而又神圣。“那達(dá)慕”一詞是蒙語(yǔ),為“娛樂(lè)”或“游戲”的意思。最早記載“那達(dá)慕”活動(dòng)的是1225年用畏兀兒蒙文銘刻在石崖上的《成吉思汗》。在石刻中說(shuō):成吉思汗為了慶祝征服花剌子模的勝利,在布哈蘇齊海舉行了一次盛大的“那達(dá)慕”大會(huì)。會(huì)上舉行了射箭比賽,他的侄子也孫哥打出了335庹的好成績(jī)。從元明兩代開始,射箭、賽馬和摔跤結(jié)合在一起,從此形成男子三項(xiàng)“那達(dá)慕”大會(huì)比賽的固定形式。每年的農(nóng)歷七、八、九月間,藍(lán)天白云下的遼闊草原,綠草如茵,水草豐美,正是牛肥馬壯的黃金時(shí)節(jié),牧民們不分男女老少,都穿上節(jié)日的盛裝,騎著駿馬從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按照習(xí)俗,大會(huì)上要舉行射箭、摔跤、賽馬等傳統(tǒng)體育比賽。此外,還有各種棋藝比賽和各式各樣的歌舞表演以及民族樂(lè)器的演奏等文娛活動(dòng)。“那達(dá)慕”一般要進(jìn)行五天至七天,賽馬和摔跤是最受人們關(guān)注的比賽項(xiàng)目,最先到達(dá)終點(diǎn)的騎手成為草原上最受人贊譽(yù)的健兒,奪冠的摔跤手被譽(yù)為雄鷹受到人們的尊敬。由此可見,在喧天的鑼鼓聲中,在萬(wàn)眾歡騰、載歌載舞的節(jié)日氛圍中,無(wú)不顯示出人與自然、社會(huì)的和諧融洽,無(wú)不展示著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無(wú)窮魅力。
3.2 民族習(xí)俗文化
蒙古族傳統(tǒng)體育文化與當(dāng)?shù)氐牧?xí)俗是密不可分的,傳統(tǒng)的勞動(dòng)生產(chǎn)習(xí)俗和日常生活習(xí)俗是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最重要起源之一。[8]例如,在蒙古族人的婚嫁習(xí)俗中,新郎要身著盛,裝佩戴弓箭,跨駿馬去迎接新娘。到了女方家門口,要先圍繞女方家走一圈,然后送上聘禮;到了第二天早上,新娘才由其家人抱到彩車上,新郎騎馬繞彩車三圈之后才能出發(fā)去新郎家,按照習(xí)俗,從新娘家回新郎家的路上,迎親的隊(duì)伍和送親的隊(duì)伍要進(jìn)行競(jìng)賽,開展“刁帽子”的友誼比賽。[9]這種傳統(tǒng)體育活動(dòng)不僅能夠抒發(fā)人們?cè)诨槎Y時(shí)幸福、喜悅的情感,也能夠增添婚慶的氣氛。
4 娛樂(lè)游戲文化
人們的生存不僅需要物質(zhì)生活,同樣需要精神生活。古代蒙古人生活在自然純樸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中,生產(chǎn)勞作之余、喜慶豐收之時(shí),需要體力與精神的豐富和調(diào)節(jié),以此滿足他們的生活需求。蒙古族的娛樂(lè)游戲活動(dòng)形式多樣具有廣泛的群眾性和鮮明的民族風(fēng)格。在蒙古族內(nèi),廣泛流傳著一種叫做“鹿棋”的娛樂(lè)項(xiàng)目,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境內(nèi)的牧民稱鹿棋為“鮑格因吉勒格”,而在杜爾伯特草原上稱其為“卑根吉拉嘎”。1948年至1949年期間,在蒙古人民共和國(guó)境內(nèi)的窩闊臺(tái)汗宮遺址總出土了一幅鹿棋棋盤,證明鹿棋是當(dāng)時(shí)宮中的娛樂(lè)項(xiàng)目,距今已有六七百年的歷史。鹿棋棋盤由五條縱橫線和六條斜線交叉,顯得縱橫交錯(cuò),斜線和中經(jīng)線直通到兩座山山頂,共三十五個(gè)布點(diǎn)兩端還有兩座山為鹿提供活動(dòng)區(qū)域;棋子分為鹿和狗兩種,鹿棋由兩人對(duì)弈,各執(zhí)2個(gè)鹿或24條狗,鹿和狗均都可以進(jìn)入兩端的山林中互相展開角逐拼殺。鹿把狗基本殺光或狗把鹿圈得無(wú)路可走決定勝負(fù)。[10]鹿棋是蒙古族民族典型的體育娛樂(lè)游戲之一,豐富了蒙古族人的精神生活,調(diào)節(jié)了人們的心理需求,也為蒙古族傳統(tǒng)體育的萌生鑄造了不可或缺的元素。
參考文獻(xiàn):
[1]段立穎.蒙古族傳統(tǒng)體育文化簡(jiǎn)論—以體育觀念的文化屬性為中心[C].第九屆.全國(guó)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體育運(yùn)動(dòng)會(huì)民族體育科學(xué)論文評(píng)選獲獎(jiǎng)?wù)撐募?011:352.
[2]黃 聰.中國(guó)古代北方民族體育史考[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2009:157.
[3]布和朝魯.蒙古包文化[M].呼和浩特: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2013:136-139.
[4]孟慧英.論原始信仰與薩滿文化[M].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14:81.
[5]巴雅爾晉格樂(lè),包達(dá)古拉,包呼格吉樂(lè)圖.論蒙古族傳統(tǒng)體育的起源及其沿革[J].南京體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9(5):51-54.
[6]孛·蒙赫達(dá)賚,阿 敏.呼倫貝爾薩滿教與喇嘛教史略[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38.endprint
[7]布仁巴圖.蒙古族傳統(tǒng)節(jié)日體育發(fā)展現(xiàn)狀與對(duì)策研究[J].內(nèi)蒙古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8(6):134.
[8]張選惠,李傳國(guó),文善恬.民族傳統(tǒng)體育概論[M].成都:電子科技大學(xué)出版社,2013:43.
[9]道日娜.蒙古族傳統(tǒng)民俗文化特色及其對(duì)當(dāng)代的啟示[J].學(xué)理論,2015:77.
[10]高 娃.論蒙古族傳統(tǒng)體育的起源[J].內(nèi)蒙古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8 (1):12.
An Analysis of Mongolian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Tian Shuai Liu Jiwu
(Wushu College,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84,China)
Abstract:Mongolian is a country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a splendid culture. In this pap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Mongolian traditional sports are sorted out and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logical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Main conclusion: Mongolian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ngolian splendid culture, its national grassland nomadic culture, religious culture, festival folk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game culture, are the foundation and source the Mongolian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Mongolian adapted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reated a production lifestyle.
Keywords:Mongolian traditional sports nomadic culture religious culture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