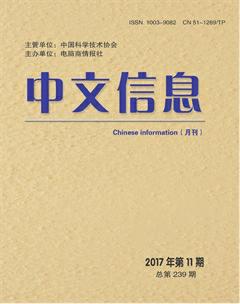說“戎”
張笑辰
摘 要:古代中國中原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的交流和交往起源很早,不同時代二者的關系也有不同的特點。本文以“戎”字為例,梳理了其字形演變和字義內涵的發展歷程,進而探究古代中原王朝對于周邊族群的認知和民族關系的變化與發展過程。認識古代對少數族群的交往與政策的發展演變,對于處理當下的民族關系等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關鍵詞:戎 中原王朝 族群關系
中圖分類號:G2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7)11-0-02
現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國的發展與周邊各國關系密切,民族關系是國際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論是“絲綢之路”的戰略,還是“命運共同體”的提議,都需要良好的國際關系作為支撐,歷史的民族關系也尤為重要。我國中原王朝和周邊民族的關系經歷了數千年的變化,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特點。中原王朝如何處理與周邊少數族群的關系,對政權的穩定、社會的發展等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東夷、南蠻、西戎、北狄”是中國古代對于周邊族群(本文所述民族指中國古代周邊族群)最典型的稱謂,其稱謂的選字也頗為重要。限于文章篇幅,此處僅以“戎”字的發展演變為例,來探討古代中原王朝與周邊族群的認知與交往歷程,窺一斑而知全豹。
一、“戎”字字形的發展和演變過程
現代《新華字典》中,“戎”有三個意思:武器;軍隊,軍事;我國古代西部的民族。系統總結先秦至晚清古今文獻的訓詁專著《故訓匯篡》中,“戎”有更多釋義,但歸納起來大致有與戰爭、軍事有關,與邊邑少數民族有關,與大、美盛有關這三個方面。許慎《說文解字》有:“戎,兵也,從戈,從甲。”是許慎認為戎的本意是兵器。從“戎”字古文字字形來看,“戎”的本意是兵器應該是可信的,但“從甲”可能不確。
商代“戎”字的寫法有多種,但基本均是從戈從“”,“”學者普遍認為是盾牌之形。從字形來看,戈與盾可以分開,如、,也可以疊加在一起,如、,還可以是人一手持戈,一手拿盾,如。值得注意的是,商代“戎”所從之盾牌的字形有時候可以簡省成“十”形,后人或將此看作是“甲”字,可見盾牌之形與“甲”字字形相混在商代就有了。
西周時期周天子以天下共主的形式管轄全國,青銅鑄造發展。“戎”字字形繼承了商代金文戈與盾分離的寫法,但盾牌之形較商代更為簡省,很多與“十”或“甲”字字形相混,這樣的字形演變更便于青銅器中文字的鑄造。在出土的西周早期大盂鼎,西周中期班簋,西周晚期虢季子白盤等器物中,“戎”字以“左邊一個清晰的十字,右邊一個戈”的字形留存了下來,如、等。西周金文中“戎”字的寫法依據鑄造的需要進行線條化,也與現今的字形相似許多。字形的清晰也暗示了表示盾和戈的字義,“戎”字便是表示武器,士兵和戰爭。
春秋戰國時期,分封制宗法制逐漸瓦解,各諸侯國先后進行爭霸兼并戰爭,全國陷入分裂割據的局面。各諸侯國在不同的地域開始了自己的統治,文字的發展也像經過地域隔離的同類物種一樣開始了不同的變化。齊系的文字中的“戎”左邊仍是一個十字形,而右邊的戈明顯根據實物有很強的象形化,“撇”拉的很長,“斜勾”幾乎彎成了“橫折”,作形。晉系文字的“戎”顯得剛健有力,字的結構變化不大,但每個筆畫都幾乎筆直,如。而燕系文字中的“戎”字,左邊的戈演變成了兩個像“戈”這種武器實物的十字。楚文字中“戈”的左上部有時候會增加一小短橫作裝飾,如。由此可見,春秋戰國時期分裂割據時期的時間之長,影響之大,是各諸侯國掌握地域實權,爭奪城池百姓的證明。
到了秦漢時期,秦統一天下之后秦始皇書同文字,我國歷史上第一次運用行政手段大規模地規范文字,形成了小篆。小篆中“戎”的字形變化不大,只是多了些規整和美化之感。秦時小篆象形意味消弱文字更加符號化,實用性大大增強,自此中國文字基本定型。后世的晉唐宋元明清等時期,雖然書法藝術逐漸發展,各家形成不同風格的書體,但不論是清秀高雅的歐體,還是厚重飽滿的魏碑,亦或是飄逸瀟灑的草書,“戎”的字形都幾乎沒有變化。準此,“戎”字字形的演變軌跡可以入下表所示:
二、“戎”字字義的演變過程
從上舉“戎”字的古文字字形來看,“戎”的本意是指兵器,由于兵器常用于戰爭,故“戎”同時也表示戰爭之意。從甲骨文的文意我們還可以知道,“戎”也可以表示某一類特定的人群,如甲骨文有:
癸巳卜,賓貞:多馬冓(遘)戎。(合集05715)
“貞”有卜問之意,“多馬”是指商王朝的軍隊,“遘”的意思是遇見,整個卜辭文意是貞人賓卜問商王朝的軍隊會不會遇上戎。此處之“戎”應該是指不屬于商王朝的部族。
甲骨文還有:
王其呼敦戎…王有佑,翦。(花東02286)
“敦”古代有逼迫的意思,常見“敦伐”連用, “敦戎”的意思是討伐戎人。整句話的意思是王命令軍隊去討伐戎人,王會受到保佑,能夠翦滅戎人。
由此可以看出,在商代,“戎”所表示的人群,多是指與商王朝敵對的部族。商王與其多有戰爭。“戎”既可表示兵器,也可指戰爭,還可以表示與之戰爭的部族,三個義項逐步引申,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傳世文獻有所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是“戎”指中原王朝西邊的少數民族。但從商周時期的傳世文獻與出土文字材料來看,最初的“戎”并沒有特定的方位內涵,如《尚書·費誓》:有“公曰:嗟!人無嘩,聽命!徂茲淮夷徐戎并興。”“徐戎”又稱作“徐夷”,是位于東南方的少數民族。出土金文材料也可證明西周至春秋時期“戎”的地域色彩卻并不單一。如冬方鼎(集成2824)有“率虎臣御淮戎”,淮戎即淮河流域的戎,即南方之戎;班簋(集成4341)有“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徒御、戜人伐東國肙戎”,是東方之戎;臣諫簋(集成4237)有“唯戎大出于軝”,現在一般認為軝是河北元氏縣境的汦水流域,則此戎為北方之戎。由此可知,在西周時期“戎”還不是指特定哪個區域的民族,而是對于與中央王朝周朝敵對民族的泛稱。
春秋以來,諸侯力征,東周的疆域較西周有了很大的擴展,各諸侯國在向域外開疆拓土的時候遇到了更多的,并且文化面貌與自身差別更大的族群。自然而然,“戎”的概念便安在了這些族群之上。因為這些族群多在周朝疆域范圍之外,“戎”便開始有了地域概念。隨著對這些族群認識的加深,逐漸意識到東西南北之“戎夷”有較大差別,便開始區別稱呼,春秋戰國時期“戎”的范圍漸漸明確,“西戎”的稱呼出現,主要指氐姓諸侯和姜姓諸侯。他們是春秋戰國時期西部比較強盛的諸侯力量。于是也就有了“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稱呼。
縱觀先秦時期作為少數族群之“戎”的概念,其內涵有一個逐漸變遷的過程。最開始有兵器和戰爭引申而來,表示不屬于商王朝的族群,轉變到逐漸附加方位地域概念,用以指稱周朝疆域之外的土著族群,最終又具體為西方少數民族的過程。
三、由“戎”字引發的思考
1.中原王朝對于周邊族群認知
中國古代對于少數民族的稱謂中,最廣為流傳的便是“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然而這只是古代少數民族最籠統的稱謂。實際上,早在原始社會時期,中國疆域內的不同地域就出現了各具特色的族群,經過不斷發展融合,形成文化樣貌大體相似的民族。例如,發源于黃河流域在族群逐漸形成的中原地區的漢族;東北地區生活著胡、烏桓等民族;西北部地區有匈奴、鮮卑、狄、戎、羌、大月氏等民族;南部的苗族、百越、武陵蠻等民族都屬于南蠻;海南島有黎族生根發芽,臺灣的高山族也不甘落后......若再細分,東北地區,賀蘭山以西地區,新疆地區,長江中下游平原地區,珠江流域等等都有不同的少數民族分支,并且在中原王朝更替的同時,各少數民族也歷經部族戰爭,部落遷移。
隨著中原王朝與周邊族群交往聯系的增多,對于他們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及內部關系等的認識也逐漸加深,在稱謂上對于戎夷蠻狄也有了更細致的劃分。《爾雅·釋地》中記載:“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其中,“夷”指我國古代東方各民族,《后漢書·東夷傳》中說明,夷有九種,為“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狄”指我國古代北方各民族,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還有白狄,赤狄和長狄,此為八狄;“戎”在古代泛稱我國西部各民族,《墨子·節葬下》中記載:“舜西教乎七戎”,戎分別有茅津,陸渾,義渠,大荔,烏氏,句衍,綿諸;“蠻”指我國古代南方各民族,《史記·吳太伯世家》中《史記索隱》記載:“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庸、濮、蜀、髳、微、越”屬于六蠻。
2.中原王朝與周邊族群的互動交往
歷觀古代中國中原王朝與周邊族群的聯系,其交往的方式是多樣的,而影響也是相互的。從上面所引材料可以看出,先秦時期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的交往多以戰爭為主。直到漢代,中原王朝與少數民族的關系開始發生了巨大變化。漢武帝治國有宏圖大志,他統治前期,北方匈奴是危險漢朝統治權的最大威脅。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想要聯合月氏部族夾擊匈奴。雖然此計未成,但張騫在出使西域途中被匈奴軟禁的經歷,使漢王朝了解到匈奴的生活習性和作戰方式,在戰略性進攻的漠北之戰中殲滅匈奴主力之后,漢王朝奪取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權。張騫隨后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打通了西方族群與中原王朝交往的通道,延續至今。漢代的中原王朝與少數民族,通過維護統治為初始目標的戰爭,打通了經濟文化交流的通道,奠定了中原王朝對新疆地區等等管轄和開發基礎。絲綢之路自漢代張騫出使西域開始,在唐代發展了陸路和海路,宋代商品經濟發展使海路繁榮,使漢族與周邊民族的特色物產,生產技術,宗教文化等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的強盛和統治者開明的政策下,中原王朝與少數族群關系的大趨勢,由以戰爭為主的敵對狀態轉為以經濟文化為主的友好交流。
隨著交流的增多和關系的密切,對于中原王朝與少數族群關系的政策也逐漸成熟。漢高祖劉邦首創和親政策,從漢代昭君出塞到《步輦圖》中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的結合,都鞏固了中原王朝和周邊各少數民族和平友好的關系。隨著中央政權的逐步完善,漢族在征服周邊民族之后確立了管轄關系。漢代的漠北之戰之后,西漢在西域設立了西域都護,標志著新疆地區正式歸屬中央政權的管轄。公元629年,唐代唐太宗李世民武力征服東突厥,在當地設立羈縻府州,冊封突厥貴族,并允許少數民族內遷中原,甚至可擔任重要官職,西北各部首領尊稱唐太宗為“天可汗”。公元640年,李世民攻滅西突厥,設安西都護府,唐王朝經營西域。唐太宗開明的民族政策,為少數民族完全融入中原漢族的生活開辟了途徑,為現今中國少數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狀態奠定了基礎,表明中原王朝對于少數民族從敵對排斥,到交流融合的趨勢。元代中央對地方實行行省制度,在臺灣設“澎湖巡檢司”,管轄澎湖列島和琉球,隸屬福建泉州,此外還開發了云南行省,加強中原對西南民族的管轄,促進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到了清代,清圣祖康熙派福建水師提督施瑯收復臺灣,公元1684年在臺灣設一府三縣,派兵駐守,臺灣正式隸屬清朝中央政權的行政管轄之下;康熙還三次征漠西蒙古準噶爾部噶爾丹叛亂,經烏蘭布統戰役和昭莫多戰役,在蒙古設烏里雅蘇臺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直接掌管軍政大權。之后,清代雍正帝設置駐藏大臣,標志清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正式管轄。中原王朝對少數民族的管轄一步步規范化,制度化,為我國成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打下了牢固的歷史基礎。
族群之間的交往和關系的發展是相互的。通過絲綢之路,在漢代的絲綢、茶葉、生產技術、制作工藝等中國特色物產傳播到西域的同時,西域的佛教文化、繪畫顏料、雕塑、葡萄、駱駝等等西域結晶由此傳入中原。在歷史進程中,戰略計劃和派出使者等等都是中原王朝對于改善與周邊族群關系作出的努力,而少數民族的物產輸出和漢化也推動了不同族群文化生活友好交流以及和諧相處乃至民族融合的進程。
在公元386至公元534的南北朝時期,中國古代北方的鮮卑族建立了北魏政權。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從小由出身漢族的祖母馮太后撫養,他對祖母十分孝敬,也深受漢族的文化的熏陶,對中原民族的文化積淀和農耕技術有著強烈的興趣。拓跋宏年幼親政,他在位初期,馮太后主要在政治、經濟方面學習漢族制度實行了前期漢化改革,政治上整頓吏治實行俸祿制并考核官員,經濟上廢除宗主督護制頒布了三長制、均田制和租調制。而后孝文帝以發兵為借口遷都洛陽,擺脫舊貴族勢力的阻礙,進一步實行漢化改革,主要變革社會風俗并力主民族融合。他從語言,姓氏,服飾,官職,祭祀,婚姻等方面,鞏固了鮮卑族與漢族的友好關系,使人民適應漢化的生活方式,北魏逐漸形成以定居務農為主的王朝。孝文帝遷都洛陽后,既出現了胡人說漢話的現象,也出現了漢人穿胡服的現象,表明中原族群與周邊族群在相互作用下的有機融合。
四、結論
本文以“戎”字字形字義的演變為例,力圖探討中國古代中原王朝與周邊族群關系的發展歷程。統觀中原王朝對于周邊族群稱謂的變化,可知古代中國中原王朝對周邊少數民族的認知是一個逐步加深的過程,二者的交往與聯系也從最初的以戰爭為主轉變到和平相處,少數民族從不屬于中央王朝的管轄到逐漸成為中央政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歷史上中原與少數民族的各種交往的發展延續,基于雙方相互的包容接納和友好輸出,在此過程中逐漸成熟的部分政策對于處理當下的現今仍有借鑒作用,順應了時代發展的趨勢,促進了民族大融合的歷史進程,也奠定了今天民族大團結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