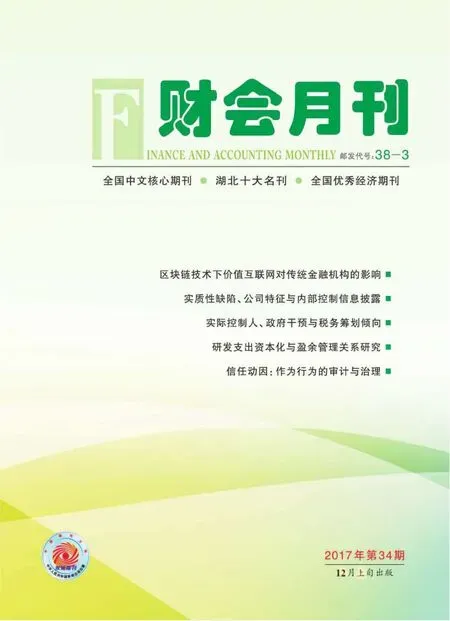信任、控制與合作在信任產生過程中的關系探討
(教授),(教授)
信任、控制與合作在信任產生過程中的關系探討
萬濤1(教授),大月博司2(教授)
信任并不是一個靜態穩定的現象,對信任的研究需考慮時間的要素,將信任看作一個動態的過程。信任分為兩個階段——初級階段和成熟階段,在不同的階段,信任、控制與合作之間存在不同的關系。研究發現:隨著組織環境的復雜化、多樣化以及層級結構的扁平化,僅僅依靠控制和監督對組織進行有效管理已變得比較困難。信任則可以有效地促進合作,從而削減組織和環境的不確定性,使組織達到“和”的狀態,提高組織績效。
信任;組織;控制;合作;和諧理論
一、前言
對于信任問題,很多學者都認為信任是一個靜態穩定的現象,因為標準(normal)的科學往往關注的是靜態穩定的現象,以此更好地評價精確性和可控性。而在經濟學領域,尋求均衡是一個基本的假定。因而,學者們將信任看作是靜態的現象就不足為奇了。社會心理學家則認為信任是一個人完全相信或完全不相信他人(Gabarro,1990)。這種觀點源于早期對信任的實驗研究,該研究關注的是諸如囚徒困境之類的游戲。這種情況下,信任水平僅僅反映的是一個時點的狀態,而不是一個反映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連續統一過程。然而,信任是隨著時間而發生改變的(Rousseau等,1998),我們研究信任時,必須還要將時間作為一個重要因素加以考慮。
二、信任的構成因素
信任被認為是有效整合多樣化和整體結構的“社會粘合劑”(social glue)或者“社會潤滑劑”(social lubricant)。大多數學者認為信任包含以下三個不可或缺的因素:①對他人的正面期望(positive expectation)。信任他人意味著對他人的行為懷著樂觀的判斷,保持一種正面積極的態度。②脆弱性(vulnerability)。Mc Knight等認為信任是一方信賴另一方的一種信念和意愿。Jones和George將脆弱性和一系列行為期望相聯系,以使個體能夠控制其行為的不確定性或風險性。③風險性(risk)。如果行為具有完全的確定性,就不會有產生信任的必要。信任的產生是與不確定性相聯系的,它是人們應對不確定性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并不能帶來人們所需要的全部確定性。信任他人往往意味著將自己置諸劣勢。
人們信任他人,其一是愿意顯示其脆弱性,其二是相信他人的行為將會有利于,或者至少不會損害他們之間的關系。信任是在一定條件和環境下發生的,不僅基于個人信息,還基于非個人(情景)信息。信任處于理性與非理性之間,既有理性的因素,又有情感的因素。
三、信任的產生和發展過程
以往學者對信任的過程也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如Roussear等在回顧以往文獻后,將信任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①構建階段(信任的形成或革新階段);②穩定階段(信任已經存在);③分解階段(信任下降)。Becerra和Gupta(2003)也對信任強度由弱到強的發展過程做了研究。本文所討論的信任過程主要是信任雙方從最初的陌生人之間的信任發展到成熟的信任的過程。
根據經濟學的理論,由于人自身能力的局限性,和組織內外部資源的有限性以及環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人們往往難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實現預期的目標。因此,為了實現自身目標,獲得期望的利益,人或組織不得不借助他人的能力或組織的資源來達到其目標。有人認為不用借助信任也可以產生合作,即通過一種集中力量對約束和利益(客觀誘因)進行操縱(劉少杰,2006)。但是作為合作雙方的單方或一方,即使其可以通過對約束和利益的操縱來影響人們的態度和行為,我們也不能完全確定對方必然會產生合作的行為。信息不對稱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原因是行為的不可察覺性。因此,對約束和利益的操縱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它并不能取代信任本身(韓魏,2001)。合作可以通過兩種方式產生:一是通過對約束和利益的操縱,即控制與監督,來達成合作;二是通過對他人或其他組織的信任。
由信任的定義我們不難看出,信任是一種手段和方式,通過這個方式合作的雙方實現自身的利益,取得預期的績效。如果進行合作的一方認為另一方的行為將有利于己,或至少不損害自身的利益,前者才會決定去信任后者,反之,則不信任。因此,我們可以將人或組織的自身利益看作是一只“無形的手”,來促使人或組織產生信任。通過這只“無形的手”,我們就能夠在特定的環境和條件下,自主演化出信任,而不是依靠一種強制的力量——約束和控制,來實現信任。同時,被信任者的能力、正直、誠實等因素——可以看作是“有形的手”,決定了合作者中的一方是否信任另一方,或者說,合作者中的一方可以選擇誰將成為被信任者。“無形的手”和“有形的手”共同構建信任。
信任可以認為是這樣一個過程:
第一,在未相互進行溝通合作時,欲進行合作的雙方已有足夠的動機產生信任來進行合作,但這時的信任由于還沒有確認被信任者,因此只與信任者自己相關。此時,信任者會根據自己信任的門檻(不信任轉化為信任的臨界點)來決定被信任者所應具備的各方面條件和要求。
第二,信任者開始選擇被信任者。信任者按照先前所設定的被信任者的要求和條件,逐步篩選可能與之合作的人或組織。根據以往的歷史和第二手資料,信任者對即將成為合作者的人或組織進行判斷、衡量,如果某個人或組織達到了這些要求和標準,那么信任者就會信任他,反之則不信任。隨后,信任者會與自己所選定的被信任者合作來完成某項工作或任務,如果雙方成功地完成了工作或任務,信任者實現了自身的利益,那么在下一次合作當中,信任者就會根據上次成功合作的經歷而直接選擇信任。反之,合作不成功,信任者在下次合作當中,就很難考慮繼續信任。這時,再建立信任者對被信任者的信任是非常困難的。當然,信任若是單方面的,也可能不會出現合作(劉少杰,2006)。信任者在選擇被信任者的同時,被信任者也在選擇信任者,只有雙方都達到對方的要求和條件,信任才有可能建立。因此,信任可以看作是一個循環過程,如圖1所示。

圖1 信任的循環過程分析
基于信任雙方可以產生合作(信任是合作的必要條件),但是擁有信任,就一定會導致合作的結果嗎?當我們認為誰可以信任的時候,只是表明我們相信這個人的行為不會損害我們的利益,卻不一定意味著我們一定會與其合作。我們可以信任某一個人,卻不信任他的能力;我們信任一個人連同他的能力,卻無法找到適宜的合作方式。因此,信任并非合作的充分條件(韓魏,2001)。
四、信任的兩個階段
信任可以根據信任雙方的了解程度分為初始信任(initial trust)與成熟信任(mature trust)。以往的文獻對這兩種不同的信任也做了明確的區分。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陌生人之間的初始信任(initial trust)在性質和強度上都與成熟信任(mature trust)存在不同(Barney,1994;Dyer,2000)。
初始信任往往在陌生人之間產生,成熟信任則是雙方對對方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之后產生的。初始信任可以轉化為成熟信任。本文所分析的就是陌生人之間的初始信任轉化為成熟信任的過程。為了便于說明,根據信任的過程我們將信任分為兩個階段:初級階段和成熟階段。
在信任的初級階段,雖然雙方沒有直接的交流、溝通,但信任者仍會產生對被信任者的信任傾向,隨后信任者根據被信任者的可信度因素衡量被信任者是否能達到他的信任門檻。同時,被信任者也根據信任者的可信度因素衡量信任者能否達到他的信任門檻。如果雙方都認為對方達到各自的信任門檻,那么雙方之間產生信任。雙方建立信任后,會產生一系列的行為,這些行為會影響對對方可信度的判斷。如果這些行為有利于雙方的利益,或至少不損害雙方的利益,那么雙方都會認為對方是值得信任的。如果這些行為損害了至少一方的利益,那么受損害的一方會認為對方不可信,并且很難在下一次合作中信任對方。在經過一次或多次的基于信任的合作并成功后,雙方會認為對方是可信的,從而在以后的合作中,直接選擇信任對方,由此進入信任的成熟階段。
五、信任、合作與控制
合作中,一方往往根據另一方的歷史或者二手資料對其信任水平進行判斷,但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及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虛假信息的存在,合作雙方中的一方要做出合理正確的判斷是非常困難的,特別是在合作雙方初次合作時。而此時也是構建信任非常關鍵但也非常困難的時機。這時我們需要引入控制系統來達到建立信任的目的。
以往研究表明,控制與信任是不兼容的,控制的存在會抑制組織中信任的產生。組織中信任越多,控制就越少,反之亦然(Inkpen等,1997;Leifer,1996)。信任是控制的替代品(Aulakh等,1997;Zaheer等,1995),只有當不存在足夠的信任時,控制才會發揮作用。例如,如果一個管理者相信他的員工能夠依靠自我激勵來盡力做好工作,那么就不需要對其行為或者結果進行控制。在此我們并不認為控制會減少信任,高的信任水平并不能自動對應一個低的控制水平,反之亦然(Das等,1998)。高信任水平的組織仍然會存在控制措施。這時的控制與過去用于控制的方法,比如正式的等級制度、嚴格的政策和程序、受限制的信息流動和嚴格的專業分工等是不同的。現在所需要的控制是一種能夠自我完善并進行集體管理的控制方法(羅伯特·布魯斯·蕭,2013)。
在信任初級階段,合作的雙方不能獲取對方足夠的信息來進行正確判斷,因而此時的信任相對于成熟階段的信任具有更大的風險性。合作雙方中的單方或雙方更容易采取投機行為來破壞合作。控制機制可以促進信任度較低的雙方進行合作,通過事后反饋,合作雙方會認為對方的可信賴性(trustworthiness)較高,從而產生較高的信任度。控制與信任是一種互補的關系,信任水平和控制水平共同但又獨立地促進合作(Das等,1998)。如圖2所示:

圖2 信任水平和控制水平關系研究
合作雙方達到信任成熟階段,信任水平隨著對對方的了解程度增加而提高,控制的作用下降。但這并不表明信任可以完全替代控制。高信任水平的組織中依然會存在控制。因為完全的信任是不可能的,將會存在太大的風險(羅伯特·布魯斯·蕭,2013)。控制在高信任度的環境下比在低信任度的環境下更為重要。高信任度的組織依賴于更少但具有戰略和關鍵性質的控制。同時,控制在高信任度氛圍下的形式與“命令和控制”氛圍下的形式是不同的。因為高信任度組織重視人際關系,控制通常是非正式的,并且以支持其他維持高信任度環境的必要因素的方式,比如所有權和責任感而得到貫徹(羅伯特·布魯斯·蕭,2013)。
從成本的角度看,控制機制和信任的構建都需要花費一定的組織成本。控制機制的選擇、產生以及實施,例如預算、計劃系統、成本-會計系統,都需要高昂的成本。同樣,信任的構建也是一個計劃行為,需要足夠的組織資源(Das等,1998)。Creed和Miles曾明確提出我們必須同時考慮控制機制的成本、未能達到最低信任水平的成本以及信任構建的成本。因此,有學者認為一個組織并不應該追求過高的信任水平。但是,由于并不存在一個共同的信任水平標準可以被所有個人或組織接受,因此,這種基于成本的觀點并不具有普遍性意義。在本文中,我們引入基于成本的觀點只是為了說明一個組織在不同的情境下,需要不同的信任水平,而不是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存在高信任度。同時,不要忽略控制機制的作用,雖然有人認為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合作是雙方或者多方一起參與一個項目或任務,綜合了各方的能力和資源,有利于任務的完成。但同時,合作也是非常不穩定的。合作存在雙重風險:①合作并不一定能夠順利完成任務;②機會主義的存在使合作者不能真心合作,達到合作目標。前者由于會受到外部環境的復雜性的影響,不在本文討論范圍內,我們主要討論后一種風險。
人們選擇合作是因為合作能夠帶來利益。然而,在合作當中,由于多方參與,單方對合作成果的貢獻很難衡量,這樣會促使合作者產生機會主義行為,即“搭便車”,從而破壞合作行為,降低信任水平。組織中的控制系統則可以很好地防止機會主義行為的發生。以往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一觀點。
韓魏(2011)認為,在剛開始時,合作可能只是由于一系列幸運的實踐促成,而不是由于信任作為必要條件促成的。隨后,當人們發現合作能夠帶來明顯的利益后,更傾向于對人的合作產生信任。迪戈·甘姆貝塔也認為,信任可以存在于那些有能力合作而成功的社會和群體中,它本身只是對于以前合作成功的信任。由此可以看出,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能夠促進信任,即信任也可以看作是合作的結果。
六、結語
席酉民教授提出的和諧理論認為,“和”描述的是組織中的人及人群與組織的關系狀態。人的有限理性導致人在面對他人及環境的不確定性時,產生大量的人與組織矛盾和沖突,這種現象即“不和”。“不和”的本質是因為一方在特定過程中沒有實現或損害了另一方的利益,或者雙方同時受到對方的損害。以往的研究認為控制和監督可以有效減少組織中的矛盾和沖突現象,然而隨著組織環境的復雜化、多樣化以及層級結構的扁平化,僅僅依靠控制和監督對組織進行有效管理已變得愈發困難。信任則可以有效地促進合作,從而降低組織和環境的不確定性,使組織達到“和”的狀態,提高組織績效。
信任是在暴露個人脆弱性的情況下發生的對一個事件或個人行為的正面期望。它是一種自愿而非強迫的合作行為,并且個人在合作中能夠得到相關利益。當組織中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時,雙方都相信對方會產生有利于己的行為,或至少不會損害自己的利益,同時雙方會盡力滿足對方的利益以維持現有信任(信任一旦失去,就難以再次建立,失去信任的代價是巨大的)。如上所述,“不和”的本質是因為一方在特定過程中沒有實現或損害了另一方的利益,或者雙方同時受到對方的損害,信任的產生則使一方難以損害另一方的利益,因而減少了矛盾和沖突,達成合作,使人和組織逐步向“和”的方向演化。
Rousseau D.,Sitkin S.,Burt R.,Camerer C..Not so different after all:A cross discipline view of trus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
Becerra M.,Gupta A.K..Perceived trustworthines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The moderating impact of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on trustor and trustee effects[J].Organization Science,2003(14).
劉少杰.國外社會學理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韓魏.信任、合作、創新——基于文化的中國企業管理行為研究[D].西安:西安交通大學,2001.
Barney J.B.,Hansen M.H..Trustworthiness:Can it be a source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4(15).
Leifer R.,Mills P.K..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 for deciding upon control strategies and reducing control loss in emerging organizations[J].Journal of Management,1996(22).
Aulakh P.S.,Kotabe M.,Sahay A..Trust and performance in cross-border marketing partnerships[J].New Lexington Press,1997(1).
Zaheer A.,Venkatraman N..Ralational governance asan interorganizationalstrategy: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role of trust in economic exchang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5(16).
T.K.Das,Bing-sheng Teng.Between trust and control:Developing confidence in partner cooperation in allianc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biew,1998(3).
羅伯特·布魯斯·蕭.信任的力量[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13.
F243.2
A
1004-0994(2017)34-0034-4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科技創新團隊基于沖突機理的創新促進效應及其創新管理機制研究”(項目編號:71572137);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創新的價值捕捉機制研究:產業鏈上價值遷移的視角”(項目編號:71772145)
1.西安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西安710021;2.日本早稲田大學商學學術院,日本東京169-8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