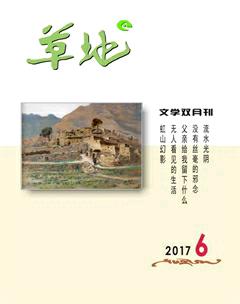父親給我留下什么
遠泰
父親,就是在老家一位普普通通的鄉紳。這個鄉紳,是過去的稱謂,今天,可以稱作知識分子。以我的理解,就是一個有點知識的一份子。
父親出生的年代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比較動蕩的年份。人煙稀少的老家,僅有一座私塾供人們就讀。父親是他們那一代之中最小的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齡,便被送到私塾去了。也正是這個時候,饑餓與災難在這塊土地上橫行,并不富裕的家庭因此而很快貧窮下來。聰慧的父親在私塾堂的成績很讓老師賞識,便在老師的慫恿下,年滿十歲的父親便只身去往成都,在一個皇城邊的洋學堂從初級中學讀到高級中學。成都解放的那一年,他又轉到汶川威州師范就讀,隨后便回到老家當了名老師。
或許是父親自身的成長經歷時常觸動著他的內心,他選擇了教師這一職業,自此無怨無悔。教書期間,父親在縣的小學、鄉的小學、甚至在村的小學,都會贏得家長和孩子們的感佩。在老家,有一半的居住民是土著漢族,這些土著漢民一些是十八世紀中葉乾隆皇帝征戰大小金川時留下的。戰亂平息后,有功之臣都得到了皇帝的冊封,就地分得土地,于是,便一代一代的生息下來。一部分是近現代時期,經商、經營茶馬互市留下的。另一部分,則是藏緬語系嘉絨支的藏族,這一支藏民族,是有著輝煌家族史的一支。他們的祖先叫做木塔爾,木塔爾是為大清帝國立下過赫赫戰功、智勇雙全的朝廷將軍。曾多次在廓爾丹之戰中屢建奇功的朝廷要員。至今,在故宮博物院的皇墻之上,懸掛著不下四張他的畫像。父親就是受政府派遣,去教育木塔爾的后裔。在當時,這是一群不懂漢語,也不會說漢話的學齡兒童,他們的交流全部是用的本民族的母語,這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年輕的父親開始嘗試著用嘉絨方言傳教孩子們。漸漸地,送孩子上學的家長多了起來,沉靜了千年的空谷有了關于讀書的聲音,本樸的孩子有了快樂的笑聲。把自己的歌唱給別人聽,把自己的鍋莊跳給別人看。父親讓孩子們在自己的歌舞中尋找幸福,又把扭秧歌、打腰鼓教給孩子們。在快樂中學習,在學習中成長。
有一年的夏天,正是胡豆、青稞成熟的季節,也是野豬、老熊等野獸活動頻繁的季節。夏天的陽光照在大地上,感覺一陣陣的悶熱,學生們擠在一間四十多平米的教室里,腥臭的汗味彌漫在空氣之中。下課放學的鈴聲響起,父親用嘉絨方言說,孩子們,今天回家大家都要洗個澡,也把你們的老熊掌掌(手掌)洗得干干凈凈的,明天我要看誰最乖!第二天,絕大多數孩子都干干凈凈、高高興興地來到教室,只有一兩個學生怯生生地站在教室外。正待上課的父親,看著他們害怕的樣子,便問道,怎么啦,為什么不進教室呢?一位學生難過地說道,老師,我們沒有找到老熊掌掌。看著孩子們干凈的手,父親感到些許的感慨。自此,他除了教學,還不斷地加緊民族語言的學習,以盡快適應特殊的教學。完全不懂漢語的孩子們,在父親的教育下,很快地成長起來。當時的老家,新政府剛剛建立,需要熟悉當地風土人情的各類人才,以適應百廢待興的事業發展。父親所教的學生,紛紛考上了民族中學,有的當了舞蹈演員,有的做了聲樂演員,有的成了醫生,有的從事首批駕駛人員。然而,新生的政權并不是一帆風順,舊制度下的反動殘余在老家時有活動,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到清匪反霸的斗爭中。不久,征兵工作在父親所在的地方展開。父親班上的學生年齡參差不齊,有一個學生小學畢業時已到了十八歲,他家里不算富裕,父母年過四十,膝下只有一個獨子,本以為小學畢業后,回家敬孝雙親,讓父母頤養天年。恰逢參軍之際,父親便主動上門動員孩子參軍,經過嚴格的體檢和政審,孩子光榮地參加了人民解放軍。喜悅和自豪洋溢在這個普通的家庭,寨子里的鄉親們都為之高興。沒想到,孩子在黑水剿匪戰役中光榮犧牲。那是一個黃昏,一對人從林間的彎彎山路上走來,剛吃過晚飯的父親,聽到遠處隱隱約約的說話聲,說話聲由遠及近,父親從房間里出來,看著幾個人在山路上正朝學校而來,前面一位穿著一身綠軍裝,中間一位手上捧著一個紅紅的東西,后面一位穿著中山服。遠遠地看著父親,便站著,氣喘吁吁地問道,是范老師嗎?得到父親肯定的回答之后,便加快了步伐。最前那位走到父親面前,雙腳并定,抬頭挺胸,舉起右手行個軍禮。老師,這是您培養的學生,他在一次戰斗中英勇犧牲了,我們不懂藏語,特請您一起前往烈士家中,安撫家屬。此刻的父親,腦子一片空白,這不是那家的獨子嗎?去時七尺男兒,回來一把塵土。還沒有來得及過多思量,父親的眼淚就滾淌而下。
其實,在老家這片土地上,曾經有過令人驕傲的歷史。在中國近代史上,那一場震驚中外的鴉片戰爭中,這塊土地上的青年男子們枕戈待旦,千里馳援,數千男兒星夜兼程,在寧波保衛戰上,以驍勇善戰,猱身而上,無所畏懼的英雄主義氣慨,演繹了一場共赴國難的壯歌。至今,在浙江寧波的大寶山朱貴廟里,附祀著民族英雄阿木穰和哈克里這群英靈。而今天,面對英年早逝的學生,還有行將老去的學生的父母,父親心潮難平。從此以后的許多年,每至年節之時,父親總是搭乘客車到學生家去看望學生父母,直到他行動不方便后,還托人幫帶東西,以求心中的慰藉。
由于父親的杰出表現,在藏區成為第一個使用藏語方言教學的老師。是在上個世紀的一九五七年,父親的事跡被刊載到了《人民教育》上,雜志用了一頁版面介紹了父親的特別教育方式。從此,父親就成了老家的紅人,三街十二溝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也正是這樣,這位民族教育的拓荒者,在一次運動中,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遣返回家務農。
父親回來時,我還沒有出生。當我懂事之后,父親已是一個右腿殘疾的人。據說,是在一次修水溝的勞動中從山崖上摔下來致殘的。那時的老家,有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豬圈,父親總是在我熟睡時掌燈進入,然后從圈梁上懸吊的書中取出一兩本,在油燈下閱讀。開始我并不知道父親讀的什么書。小學時,才似懂非懂的知道他讀的是中醫書籍。自小,父親就有一個夢想,要做一名醫生。這個夢想,還是他幼小時深埋于靈魂深處的。那年,老家瘟疫盛行,在這一場流行瘟疫中,父親險些夭折。漸漸長大以后,身邊的左鄰右舍時不時有人因疾病奪去了生命,看著一個個鮮活的生命被病痛折磨,甚至走到人生的盡頭,父親便立志治病救人。可事與愿違,他卻當了一名塑造靈魂的教師。遣返回家后,勞動之余,他有充分的時間撿起他曾經的夢想。于是,他成了老家遠近聞名、卻沒有取得許可的醫生,有好多人的疑難雜癥、頭暈目眩、腰肌勞損都被他醫治過。也是在這時,我才開始真正地走近父親。在他的熏染下,我開始喜歡中醫,放學玩耍之后,便拿著醫藥書讀一讀。不經意間,我能背誦《藥性簡要》、《醫宗經卷》、《金匱要略》。但那時,更多的是看他藏在圈梁上的四大名著和《子夜》、《屈原》。其實,那時的我,閱讀這些書籍是很困難的,繁體字只能邊猜邊讀,每每讀到好的作品時,總要回味一番。或許,正是在那段艱難的歲月里,埋下了要當一個作家的夢的種子。想想這一段經歷,因為父親的陪伴,讓我愉快地成長。也因為我的陪伴,讓父親熬過了那段悲苦的日子。也是在這段日子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父親的正直善良與一絲不茍,并影響我至今。
小學快要畢業時,父親開始焦慮起來,他深知,因為他的原因,可能影響到我升學的問題。在一個深秋的夜晚,當我從熟睡中醒來,看見父親在燈影中來回地踱步,手中握著那支與之相伴的鋼筆,愁容滿面。我抬起頭說,您還不睡?這時,他才注意到我已醒來。桌上的煤油燈火在微風中輕輕地晃動,黑色的煙霧彌漫了整個房間。他說,有人告訴他,如果寫一封狀告別人的舉報信,就會摘掉他右派的帽子,這樣,他的普通人的身份就會恢復,對我們全家、特別是我的升學有很大的好處。但是,被告的那個人就會戴上叛徒的帽子。我說,那人是不是叛徒呢?父親說,不是。我說,那不是您就別寫。父親說,不寫就要影響你。我說,沒得事。父親驚訝地看著我,眼睛里充滿了疑惑、欣賞、感動。這時,窗外投進一絲微白的晨光,父親的臉色轉瞬變得紅潤起來,慢慢地放下握在手中的筆,吹滅了煤油燈,翻身睡在床上,長長的出了一口大氣:不寫就不寫,這種昧著良心的事不做。又過了許久,我在父親的鼾聲中醒來,太陽已照到窗外的半山上。我的躁動,驚醒了父親,他翻身下床,把昨天的剩菜剩饃放在鍋里蒸熱,父子倆分而食之。然后,背著他的背簍,杵著他的拐杖勞動去了。臨走時,回頭一笑。父親是我們這個山溝里最有文化的農民,能寫得一手好的毛筆字。每到臨近春節時,遠親近鄰都要去買一些紅紙來,請父親給各自的大門寫幾幅對聯,寫的人多了,不免出些差錯。記得有一年,民兵連長請父親寫了一幅對聯,寫完之后發現下聯少寫了一個字。民兵連長并沒有發現,便拿著走了。那時的紅紙很貴,只有勞動力相對多一點的人家才能分得更多的錢,我們家是很難拿出錢去買紅紙寫對聯的。那一年,父親破天荒地給我了五角錢,讓我去買了一張紅紙,然后,先裁了一個單幅,把寫錯了的下聯重新寫了一道,讓我給送去。當我送到別人家時,剛好是大年三十早上,連長家的對聯已經貼上門框。我說明原委后,連長一看,才發覺真的少了一個字,好在字少了,意思還沒有變,不然,破壞的罪名安在父親頭上一點也不過分。其實,我小學畢業后,正是因為父親的原因沒能上成初中。那幾年,我在父親的身邊如影隨形,雖然,物質上顯得拮據和貧困,但是,我們的精神卻格外的充實和飽滿。
父親從來都顯得謙恭。恢復工作時,他感覺到知識的更新替換日新月異,便不再選擇回到教室,回到學生當中。在我參加工作后的某一天,我隨父親在老家的馬路上散步,迎面駛來一輛貨車。車到我們身邊時,停了下來。從駕駛室跳下一位中年男子,走到父親面前,親切地喊了一聲,老師!父親擲地有聲地應答,我卻從他的眼神中讀到了此刻的迷茫。老師,您不認識我啦?我叫楊根思。喔,是你啊,沒有找到老熊腳板的孩子呀,你都當汽車師傅了。父親笑著說。楊根思紅著臉說,老師您還記得呀,我都跑了十幾年長途汽車了。楊根思邊說邊把父親攙扶著,老師,我送您回家,好多年沒見到您了,我送您,我送您。說著,就把父親往駕駛室牽去。父親說,不不,我在散步,幾步就回去了,你不送。哦,不,老師,我一定要送。父親回過頭看看我,我用眼睛告訴父親,就讓學生送您吧,路雖然短,可情意深長呀。父親被他的學生送走了,獨自留下我一個人在馬路上閑走,我忽然羨慕我的父親,他一次不經意的相遇,卻讓他享受了一份美好與崇高,一次被頂敬的褒獎。不久,我從縣城調到了另一座城市,陪父親的時間更加的少了,直到他猝然離世。父親藏在豬圈梁上的那些書,也被蟲蛀得破爛不堪,并隨著歲月的更替,蕩然無存。父親未能實現的夙愿:做一名醫術高超的中醫,醫治人間疾病,沒有在我們這一代人里實現。相反,我也做了一名教師,選調成了一名機關工作人員。回望這風風雨雨的如歌歲月,父親沒留下點點財富,沒留下良田莊房,也沒留下錦緞綾羅。只為我留下了一種勤勉的生活態度,一種曠達的人生哲學,一種相伴一世的嚴謹作風和一種寧靜悠遠的簡單命題。這些財富,讓我精神強大,內心飽滿。
愿父親靈魂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