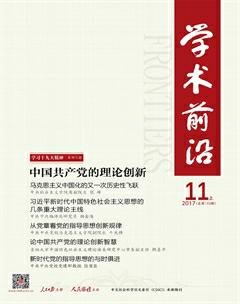列奧波爾德對《論猶太人問題》的解讀
李真
【摘要】牛津大學教授大衛·列奧波爾德所著的《青年馬克思》一書是近年來西方馬克思學界的一部力作。《青年馬克思》指出,《論猶太人問題》作為馬克思與鮑威爾思想的第一次公開交鋒,是馬克思爭議最多的文本之一。列奧波爾德認為,之所以造成如此歧義化的解讀,主要在于我們對于鮑威爾的思想既不熟悉也不理解,簡單地將鮑威爾作為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一個重要“他者”。因此,只有深入了解鮑威爾與馬克思的思想對話,把握政治解放和人類解放的統一,才能觸及“當代的普遍問題”,實現個體自由。
【關鍵詞】猶太人問題 政治解放 市民社會 自由
【中圖分類號】 A1 【文獻標識碼】A
【DOI】 10.16619/j.cnki.rmltxsqy.2017.21.028
根據列奧波爾德的描述,1781年約瑟夫二世簽署了《寬容法令》,開啟了歐洲猶太人解放的法律進程。數十年過去,對猶太人多樣化的限制和歧視政策并沒有消失。1841年冬《內閣敕令》草案一經頒布,便成為猶太人的眾矢之的。在一片口誅筆伐的聲討中,該法案最終沒有得以實施,卻引起了社會上對“猶太人問題”的重新探討。在經過啟蒙運動的德國,“猶太人問題”對猶太人而言實際是一個政治問題,即接受還是拒絕猶太人獲得與基督徒平等的權利。鮑威爾和馬克思就猶太人問題的辯論就是這次論戰的一部分。列奧波爾德提出,鮑威爾和他同時代的幾個人經歷了一場相同的命運,即被現代讀者稱為是青年馬克思的論戰目標之一,從而遮蔽了他們思想本身對馬克思的輻射力量。因此,只有溯本清源,在文本的語境中廓清鮑威爾的思想,才能使馬克思的思想得以更加明晰的彰顯。
鮑威爾與猶太人問題
列奧波爾德認為,在《猶太人問題》一書中,鮑威爾的文筆洗練、大膽、透徹,作品中包含著對猶太人和猶太教深深的敵意。鮑威爾為了論證“猶太人解放”提法的矛盾性,概括了猶太教的特征:排他性、肯定性和虛偽性。首先,鮑氏認為《舊約》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圣經中的猶太教并沒有教授“人類同胞的普遍愛”。排他性是一切宗教的共同屬性,這種屬性在猶太教身上表現的更為明顯。其次,猶太教是肯定性的宗教。在《猶太人問題》中,鮑威爾這樣描述“肯定性”:猶太教認為自己的教義是就像“上帝”的意志一樣,是一種無法解釋的東西,一種與所給予的環境無關的秩序,信徒所需要的是一種對“無法理解和武斷的命令”的不加思考的服從。第三,猶太教具有“虛偽”和“空想”的特性。鮑威爾據此得出結論,認為只要依然堅持猶太教信仰,猶太人獲得政治解放從而獲得平等的政治權利是不可能的。列奧波爾德指出,這不僅顯示出鮑威爾缺乏必要的同情心,而且缺乏知識。雖然鮑威爾的圣經研究成就是相當可觀的,但他對后圣經時代的研究是有缺陷的。①列奧波爾德進一步指出,鮑威爾對猶太教歷史角色的理解,同時也體現在他對猶太教和基督教關系的敘述中。②鮑威爾把猶太教和基督教關系定義為“果實”和“花朵”、“母親”和“女兒”的關系。列氏認為,鮑威爾對猶太教必然消亡的解釋基于這樣一個歷史性的敘事邏輯:他將歷史的發展與“普遍性”的逐步實現聯系起來,認為猶太教到基督教的發展歷程是普遍規定性從部分到整體的實現之路。假設一個實體存在(猶太教)的基本原理,即它是否具有為歷史進步作出貢獻的獨立價值。那么,一旦更完美的實體(基督教)出現在歷史舞臺上,不那么完美的實體將失去繼續存在的理由。基督教也因其“更完善性”擁有更高的權利。鮑威爾進一步指出,基督教作為完善化的猶太教,在發展猶太教普遍性的同時,也將猶太教的排他性推向極致。因此,在鮑威爾的描述中,雖然猶太教僅僅體現了特殊的利益,基督教則體現了普遍的關懷,但二者都受到宗教本質和核心精髓的約束。
列氏認為,經過對“猶太人問題”的重新認識,鮑威爾把猶太教問題定義為宗教問題,他又逐一批判了當下存在的解決問題的方案,并從中揭示出消滅宗教是解決猶太人問題的唯一出路。鮑威爾指出猶太人通過皈依基督教不可能獲取真正的自由,任何宗教信徒都是仆人和奴隸,猶太教徒也不例外,他們皈依教基督教只不過放棄了一個具有更多苦難的群體和那些看起來更加有利可圖的群體聯盟。德國歷史已經證明,一旦基督教國家強大起來,它就會收回這種特權。鮑威爾指出,任何想通過這種方式來解放德國猶太人的做法,無異于想要洗白污濁的荒原。在列氏的描述中,鮑威爾對猶太人以及猶太教都有一種貶損的觀點,但他認為這并不構成消滅宗教,亦或是拒絕猶太人與基督徒享受相同的公民和政治權利的充足理由。因此鮑威爾進一步論證,認為猶太人不可能擁有真正的自由。列氏指出,在鮑威爾自我意識哲學中,所謂“真正的自由”不僅僅是指自我意識沖破宗教的枷鎖,它更是人類歷史的推動力和目標。對鮑威爾來說,要實現真正的自由,必須有兩個要素:(1)消極的要求是個人放棄他們的宗教信仰;(2)積極的要求是人類用自我認同取代那些被拋棄的宗教信仰。同時,鮑威爾認為鑒于自由是人類普遍性的實現,基督教的“人的普遍性”較之于猶太教所承認“民族普遍性”更接近于真正的自由。因此,在離真正的自由更近的地方,“基督教遠高于猶太教,基督徒遠高于猶太人”。基于基督教與真正的自由之間的概念聯系,鮑威爾認為,相對于基督徒而言,猶太教徒的自由實現之路似乎更為坎坷。為了實現自由,“基督徒只有一個階段,即通過放棄基督教而放棄宗教信仰”,而“如果猶太人想要實現自由,則會更加困難”。③
列氏指出,通過以上論證,可以看出雖然鮑威爾認為基督徒比猶太人更接近自由,然而獲得真正的自由之路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坦途。但是,鮑威爾提出,人類現在處在一個即將治愈人類“所有疾病”的“全面革命”(批判的哲學革命)的時刻,猶太人的世俗力量(金錢)也會征服一切狹隘的偏見。此外,由于人類的天性在真正自由的環境中才會得到真實和充分的展現,因此,歷史同樣可以被視為人類自我實現的過程。真正的自由是普遍性的實現,要求個人在認知上理解并實際承認人類的共同性。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不僅在認知上認同人類本性的“普遍性”,而且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保障人類本性“普遍性”的實現。endprint
馬克思對鮑威爾觀點的重建
列氏認為,盡管《論猶太人問題》表面上與宗教有關,但很明顯,青年馬克思的真正興趣在于通過重構鮑威爾的政治解放概念,將注意力從鮑威爾所關注的問題(猶太人和猶太教的歷史角色)轉移到他自己感興趣的問題上(政治解放的成就和局限性),從而將宗教的問題還原為世俗社會與世俗政治問題,實現了從政治解放到人類解放的超越。列氏指出,根據馬克思的闡述,在完成政治解放的現代國家,宗教的政治廢除并不意味著徹底廢除宗教信仰。毋庸置疑,馬克思的這一論斷直指鮑威爾“基督教國家”的錯誤概念。鮑威爾把落后的(尚未實現宗教和政治的分離的)普魯士國家界定為“基督教國家”,它的本質特征是宗教特權的國家,它的政治綱領是基督教圣經,它的核心是排斥其他宗教。列氏緊扣文本繼續分析,馬克思認為政治解放是現代國家的一個標志性特征,它一定是“完善的基督教國家”,是“無神論國家,民主制國家,即把宗教降級為市民社會其他要素等級的國家”。④也就是說,真正的國家可以撇開宗教,因為它已經用世俗方式實現了宗教的人的基礎。⑤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通過分析北美許多州的經驗指出,在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國家,并沒有發生宗教的消除,宗教被降級為市民社會的領域,并依然以星火燎原之勢存在著。
列氏指出,在馬克思早期的作品中,市民社會在國家的首要地位以多種方式表現出來。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認為政治國家的更大的權力來源于市民社會的“支持”,而不是國家本身。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認為,行使最高權力的是市民社會,并將國家的主權稱為“虛構的”。列氏認為馬克思采取歷史敘事的方式證明政治國家是市民社會和政治生活分離的結果:封建社會把一個統一的市民社會和政治生活結合在一起,沒有一個屬于所有公民的政治團體,反之,現代社會的特征是政治領域的發展并成為整個政治社會的“普遍事務”,但卻與市民社會的日常生活分離開來。列氏認為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青年馬克思不僅強調市民社會和政治生活分離的事實,還強調了分離對其各組成部分的性質的影響。現代的人民和政治生活之間的鴻溝并不是兩種原本獨立的自然力量的分離,而是“從政治上解放市民社會”,這使市民社會的成員從對共同利益的關注中解放出來,馬克思將市民社會描述為“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利己主義的領域”。列氏認為,這是一種與霍布斯的觀點(關于自然狀態的描述)相呼應的描述,表明這種強化的利己主義影響個人動機和社會關系,就這些狹隘自私的個人之間的關系而言,馬克思并沒有說現代個體是完全沒有聯系的,而是認為他們之間的社會聯系是一種競爭和敵對的關系。列氏繼續談到,在對托克維爾思想的幾次回應中,馬克思把市民社會的成員描繪成一個單子式個人,作為一個“孤立的自我封閉的”個體,越來越“內向他自己,他的私人利益和他的私人愿望”。馬克思認為,市民社會用“自私自利和實際需要”來代替共同體的契約,產生了一個狹隘的、利己主義的個人在敵意中互相對抗的世界。
列氏認為,年輕的馬克思對共同體的理解并不精確,這并不影響共同體的概念在馬克思早期作品中的重要地位。馬克思“擁有一個富饒而不是一個整潔的頭腦,如果它變得更加整潔,它可能會變得不那么肥沃”。⑥也正是馬克思思想解讀的歧義性,造就了馬克思思想旺盛的生命力。在馬克思的哲學訴求中,“共同體”往往與“人的全面發展”的終極致思之路連接在一起。馬克思認為政治生活是一個共同的領域,其中的成員更多地表現為共同體的存在而不是追逐私人利益的孤立個體。列氏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即盡管馬克思很少直接討論共同體的性質,但他關于“共同體”的表述是與“社會協作”相關聯的。馬克思始終關注人的自由發展和潛能實現,在他看來,對于個人來說,作為共同體的人,不僅意味著他們意識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會力量”⑦,從而與他人“協作”,并結成一定的個人關系。也正是在與他人的“協作”中,人擺脫了原始的自然狀態,超越了把他人看作工具和手段的單子式存在,達致“本來意義上的人,真正的人”,從而實現人的自由。因此,個體的潛能只有在一個理性自由的共同體中才有充分實現的可能,只有自由理性的共同體生活才能孕育自由發展的個體。
結論
在著作的結尾,作者再次重申開篇提到的觀點,即打破對馬克思的碎片化解讀,從整體上解讀馬克思在當代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啟示。此觀點源于一種不可撼動的理論信仰:青年馬克思的豐富思想來自于對當時市民社會中個體命運的關注,針對現代政治生活的得與失,洞察和闡釋人類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尚未意識到)。在某種意義上,傳統馬克思主義宣稱在《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完成了由主觀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雙重轉變的斷言雖然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一致認同,但至今仍缺乏有力的論證和研究。馬克思認為,鮑威爾站在激進民主主義的立場,主張通過宗教批判解決“人的問題”,其實質還是把政治批判還原為宗教批判。在馬克思看來,宗教批判只是政治批判的起點,也正是政治批判這一立場使馬克思從自由主義分裂出來,走向不同于鮑威爾的共產主義批判之路。
毋庸置疑,作者具有扎實的理論功底和寬廣的學術視野,將大眾熟稔的話題賦予新的考察視角。可以看出,思想史的視野是本書的一大特色,該書史論合一,實現了規范性理論與學術創新的結合。然而,作者卻更多地拘泥于局部的思想史和時代背景去把握青年馬克思的思想,不能為從宏觀上解讀馬克思思想提供一個更有張力的實踐空間。再者,作者更多局限于“馬克思學”的框架進行文本解讀和人物分析,從而忽視了馬克思的思想發展史,更忽略了馬克思思想在西方世界乃至全球的發展歷程。然而,這對于從整體上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致思之路和價值訴求,結合實踐需要,從而更好地發掘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踐導向,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注釋
David Leopold, The Young Karl Marx,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12, p.113, p.133.endprint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4、46頁。
John Plamenatz, Karl Marx's Philosophy of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03.
責 編∕樊保玲
Abstract: The Young Karl Marx by David Leopold of Oxford University is a great work of the Western Marxism academia in recent years. According to the book, On the Jewish Question represents the first public argument between Marx and Bauer and was also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texts of Marx. Leopold believes that such mistaken interpretation is mainly because we are not familiar with nor understand Bauer's thought and simply treat him as an important "the other" in the study of Marxs thought. Therefore, only by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ideological dialogue between Bauer and Marx and grasping the unity of political liberation and human liberation, can we reach out to the "common problems of the present-day era" and realize individual freedom.
Keywords: Jewish question, political liberation, civil society, freedom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