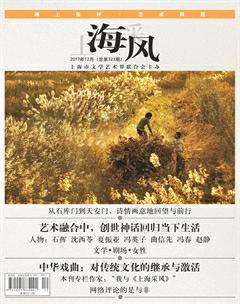從《相愛相親》說到“電影也是人學”
光明網刊文說,前不久離世的著名文藝理論家錢谷融先生早年曾寫過名篇《論“文學是人學”》,后來被廣為引用,以此說明文學的特質。其實,何止文學,戲劇和電影亦如是。一部好的電影,假如未能塑造出一個成功的人物形象,人物未能走進人們的心靈,很難說是一部成功之作。由張艾嘉執導的電影《相愛相親》,充分展示了“人學”的特質。在這部電影里,沒有事先設定的各種“正確”,一切都跟隨著人性的脈絡發展。比如,那位女強人母親(張艾嘉飾),為了達成讓親生父母死后同穴的目的,真是風風火火不顧一切,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可是在“獨戰”過程中,作為女人,她也免不了有點“小心思”,甚至有點“小曖昧”,雖然只是稍縱即逝,但編導用貌似不經意的幾筆,勾勒出了人性的豐富。還有她的丈夫(田壯壯飾)縱然對妻子百般呵護,但當面對嗲妹妹型的女鄰居(劉若英飾)時,也不由得心有旁騖,神馳魂飛,恨不得天天可以手把手教她開車……然而,編導并沒有在這些“無傷大雅的細節”上用力過度,只是用若有若無的線條勾勒幾筆,人物的立體感頓時顯現。
最精彩的莫過于姥姥(吳彥姝飾)一角的設置。半個多世紀前的一紙婚約,讓姥姥等了一輩子,她把牌坊立在了心里,用一生堅守刻下“曾氏”二字。在她的觀念里,她是丈夫的原配,這是“有書為證”的——族譜里記載的就是她這個正牌妻子,何況丈夫很長時間一直都在寄錢養家。哪怕她明知他已有了新家、有了后代,但只要守著丈夫的墳墓,心里自有一份安寧。孰料,丈夫“法律上的妻子”逝世了,其女強人般的女兒死活要把父親的墳墓遷走,讓親生父母天上相會。這就引發了“法律婚配”與“民俗婚配”的沖突。這一人設非常獨到而精彩,可供挖掘的內涵非常豐富。其中沒有是非對錯,只有人性的張揚和暗示,每個人的行為邏輯都非常在理,但又水火不容。如何解開這團亂麻?通常我們容易循入“秋菊打官司”或“我不是潘金蓮”的窠臼,但張艾嘉還是從人性入手,讓姥姥在各種盡情表現后,用“我不要你了”的“人性豁達”,親手解套;與此同時,經過心靈掙扎的女強人,也終于了悟“相愛相親”的真諦,企圖給出姥姥滿意的答案……劇情在此戛然而止,結局令人欣慰。
劇中演員的表演都拿捏得十分精準,尤其是吳彥姝飾演的姥姥,將一位堅守傳統而又通情達理的魅力老人演繹得頗具立體感,可謂精彩。這個老人既要矜持傳統、堅毅隱忍,又要豁得出去、不惜一戰。豁出去時,還不能是潑婦式的,必須保持一份尊嚴和美感,所以說這個老人并不好演。
《相愛相親》是一部難得的好電影,它告訴我們什么是“真正的電影”,也為我們呈現出電影“真正的樣子”——沒有“正確第一”的主題先行,沒有主題單一的宗旨設定,沒有好壞分明的人物形象,沒有“砍掉枝枝叉叉”的過于干凈……因為,電影也是“人學”,在“人學”的世界中,人性之蘊藉、情感之豐富,是不能被條條框框所限制的,而是應立足于藝術本體。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