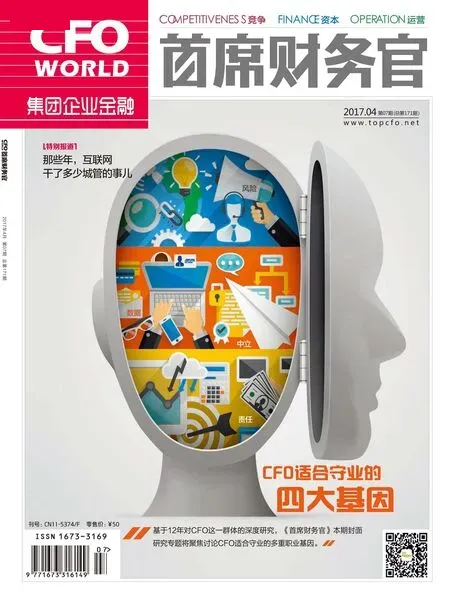特朗普時代的赴美投資風險
文/本刊記者 馮珊珊
文/本刊記者 馮珊珊
中國赴美投資開始逐步進入一個新的周期——特朗普時代。與之相伴而來的,是復雜的市場情緒。
2001年,國家將“走出去”戰略正式寫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到2016年,中國大陸企業的海外并購投資交易總金額達到7700億美元;交易總數量達到11409宗。
其中,投資額在1億美元以上的項目,美國第一、澳大利亞第二、加拿大第三。美國也是除了避稅港地區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最多的國家。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在美的投資與并購之路一直布滿荊棘。除了整合失敗外,美國政府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干涉投資行為,同時對中國企業的調查也呈愈演愈烈之勢。
“唐吉坷德”當了總統
“此次美國大選,基本上成了一個‘沒有最差,只有更差’的‘比丑運動’,美國社會的很多精英如布隆伯格等選擇退出。”中投公司副總經理祁斌在財新-云鋒海外投資論壇上發表《國際金融形勢與海外投資戰略》演講主題時的感悟。
2016年11月9日,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J.Trump)贏得美國大選,2017年1月20日,正式入主白宮。
特朗普的當選被認為是2016年最大的“黑天鵝”事件之一。在就職后的首次國會演講上,特朗普意氣風發,“The stock market has gained almost three trillion dollars in value since the election on November 8th,a record.”(自11月8日美國大選以來,美股市值漲了近3萬億美元。)
在美國主流社會精英階層眼中,特朗普就是一位唐吉坷德式的總統,挺一桿長矛就準備大戰風車,這種不確定性似乎沒人可以琢磨。
正如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戰略研究部一位專家所指出的,未來中美關系能否繼續健康發展下去,還是回到“修昔底德陷阱”的老路上,這是當前亟待做出的一個大判斷。如果特朗普瞄準中國“開火”,未來他可能聚焦在哪些領域、采取哪些手段,也需要提前研判并提出應對之策。
特朗普的政治理念,無論是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民粹主義,還是通過逆全球化的方式,重振美國經濟,都是對美國傳統主流政治模式的一次顛覆。
在一些專家看來,特朗普政策的內在邏輯只有一個,就是增加就業。在國內政策上一切圍繞就業,在對外政策上也是如此,一切有利于美國就業的事情他就會努力做,一切對就業影響不大的問題他就會選擇性忽視,一切導致就業流失的政策他就會堅決反對,正如他堅決反對TPP、要求重談北美自貿協定、在美國和墨西哥間修建隔離墻、抨擊中國是匯率操縱國、威脅對中國開展貿易戰等等。
所以,悲觀的看法是,未來一個時期,中美在經貿領域的競爭與沖突將更加激烈,特朗普將踐行競選時的承諾,出臺針對中國的保護主義貿易政策。如果縮小貿易逆差,那么大量就業被留在美國國內,這正是特朗普希望看到的并通過多方努力想要實現的結果。
但也有不少樂觀者認為,特朗普是一個生意人,一切都可以談判,中美貿易與投資關系甚至會上升到一個新臺階。
“特朗普并不是像大家想像的那么沒有機會。”在祁斌看來,特朗普上臺是一個反思的機會,或許沒有那么糟糕。“很多人認為特朗普當選意味著反全球化,或是全球化的挫敗。事實上,這更多地應該理解為對全球化的一種反思——“你可以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全球化是個好東西,也不可阻擋,但在推進的時候,你可能需要更多的實事求是的推進。”
祁斌認為,理解中美關系,用一句話概括,就是競爭與合作。在與美國前財長薩默斯的對話中,薩默斯提到很多美國人擔心中國的威脅和挑戰,祁斌的回應是:“中國的勞動生產率還只是美國的百分之七,所以中美之間合作的空間遠遠大于其他,我們應該加強合作和雙邊投資,這樣既有利于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也有利于美國經濟復蘇和繁榮。”
風險一:國家安全審查升級
普華永道中國國際稅務部合伙人王鵬認為,“特朗普就任后對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的態度會直接體現在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批的尺度上,民企投資會相對容易些,但即便如此,一旦涉及到敏感領域或者說行業,即使獲得批準,批準也是有條件的,比如有些知識產權必須是在美國境內完成研發而不能拿到境外。”
其實,發達國家對中國企業尤其是國有背景企業的投資一直以來都懷有警惕,認為這會威脅國內的經濟安全。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可能會讓海外標的公司受到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更為嚴格的審查。
據了解,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簡稱CFIUS),它由9個部委的主要負責人組成,他們來自財政部、司法部、國土安全部、商業部、國防部、國務院(其實就是外交部)、能源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科技政策辦公室,由財政部長擔任主席。
CFIUS負責審理外國在美投資項目,如果發現項目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利益”,可以要求投資人對投資項目進行適當調整,或者建議總統暫停或禁止該交易。
CFIUS的審查程序,例常審查期限為30天。包括一個7至14天的在材料提交前受審對象與CFIUS的討論過程。如果在例常審查中發現,交易屬于受轄交易范疇,須進入為期45天的調查期。最后,總統裁決,須在15天內作出最終決定。
美國成美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柳治平認為,“以往中國企業赴美投資,和CFIUS打交道比較多的可能就是在能源、電子通信和材料領域。直到2013年雙匯集團收購全球規模最大的生豬生產商及豬肉供應商史密斯菲爾德(Smithfield)時,很多人才意識到,CFIUS的觸角并不只是拘泥于其通常的審查對象——制造業、金融和信息服務業、礦業,以及建筑和運輸業,而是可能涉及包括食品生產業、農業等在內的行業。簡單來講,無論軍事、科技、民用生活還是農業、能源、交通運輸,各個領域能產生的影響都可能被視作是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
“這并非沒有道理,畢竟現代科技和生活方式把國家安全從軍事領域擴展到其他領域。現代通訊和交通手段,以及城市生活,使得外國公司更容易通過實際操作與控制的任何位于美國境內的資產通過蝴蝶效應,危害到美國的食品與水,網絡,基礎設施,甚至政治過程比如選舉。”
“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現在他們對于來自中國的跨境并購交易是比較關注的。我們現在執行的幾個案子都在CFIUS過會審查過程當中,但總體來講,CFIUS過會審查不批準的比例非常非常低。我們也看過統計數字,大概不到1%的比例。”投中資本董事總經理楊斌表示。
風險二:減稅羅生門
特朗普主張啟動自上世紀80年代里根執政以來最大規模的減稅方案。個人所得稅方面,將聯邦個人所得稅由目前七檔簡化為12%、25%和33%三檔,最高檔將由目前的39.6%降至33%。企業所得稅方面,主張將最高聯邦企業所得稅率由目前的35%降至15%,對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的私人股權融資提供82%的稅收減免。海外投資稅方面,將跨國公司海外收入稅率降為8.75%,對把工廠搬到他國、雇傭他國員工卻想把產品售回美國的企業,征收高達35%的產品關稅。
一種觀點認為,大幅減稅以及對于美國受控外國企業可能會加強征管,意在希望美國境外企業利潤回歸本土。
“意味著對外國投資者的投資回報會提高,無疑也會刺激中企赴美投資。”普華永道王鵬就表示,特朗普提出的一些經濟政策主張,如解除對能源行業的限制,重點關注天然氣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放松對金融機構的監管等,可能吸引有關行業的中企赴美并購,分得市場的一杯羹。
據了解,美國擁有世界上最為繁瑣的稅收法律體系。不同州有不同的稅收規定,同時受美國三級政府的分權型稅制的約束。只要不違背憲法規定,州和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州和地方的稅法并自主調整稅種和稅率。
中國企業會根據自身戰略在不同州進行投資:部分企業跟隨主要合作伙伴選擇投資地點,而部分企業從優化供應價值鏈角度考慮選擇投資地點。此外,中國企業通常會通過海外中間控股公司收購目標公司,以減少或消除對股息和對處置股份取得的資本利得征收的預提所得稅,從而獲得較優化的稅負結果。
正如一些研究文章中所指出的:隨著中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投資主體和投資方式日益多元化。從稅收角度看,中國企業、VC、PE等投資主體將面臨美國的雙重征稅,而資本弱化是降低股東層面稅負的常用方式,隨著美國對股東的反避稅力度加大,中國投資企業面臨著更大的稅務風險。
運動認識能力,就是學生對體育健身知識、運動技能和相關健康知識的獲得、轉化和評價的能力,伴隨著思維、理解和感悟等活動,是自主健身的先決條件。
世界各國的公司所得稅率逐步降低,美國同時面臨成為世界上所得稅稅率最高的國家的壓力。跨國公司有持續通過資本弱化實現利潤轉移的趨勢,同時政府財政赤字壓力增大,這迫使美國對資本弱化規則的管制日趨嚴厲。因此,中國企業在美國投資的過程中應謹慎采用資本弱化避稅。
風險三:跨文化深層思考
巴菲特說,如果一個商人不知道自己該不該去并購,哪個公司與他的公司有協同效應,哪個公司是好下游(客戶),好上游(供應商),哪個公司是有實力的競爭對手,那他就不該做這個生意,因為他不懂自己的行業。延伸下去,如果你做一個收購或者投資,都不知道這個標的對你的價值,那你其實也不應該做這個投資或者并購。
柳治平認為,投資美國公司時候,中國投資方經常會犯一些錯誤,體現在中國思維和慣例:比如,中國投資方往往聲稱自己需要“控股”。在美國,一個投資人不需要擁有51%的股份,也可以有效地控制標的公司的大政方向。相反,即使中國投資人擁有51%甚至更多股份,也不一定能夠有效把控公司,甚至在公司里基本沒有治理權利。
原因是,美國的公司法在“實質法”上比較“無為而治”:它假定公司各個股東之間會按照自己的情況和需求,討價還價,各取所需,量體裁衣設計自己的治理框架。也就是說,這很大程度上是個靈活的私人契約,而不是政府代替市場或者私人企業指定的條款或者說條框。
再比如,在美國,對沖基金或者其他私募基金采用的是有限合伙(limited partnership)組織方式,其經理(就是GP)可能在基金中股份微薄(當然他們收取基金利潤一般20%的權利(carry)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股權),但是他們操控基金的投資決定。如果中國公司投資一個其他實業,即使被告知獲得90%股份,如果是有限合伙的一個普通合伙人,那也是基本沒有任何決策權,甚至知情權也很少。
一般而言,美國這邊少用對賭條款,公司創始人也不會個人為股權投資人的投資提供擔保。
柳治平表示,中美兩國在商業慣例上的區別還體現在中介機構的選擇上:一是在美國尋求并購或者投資標的時,中國公司一般只愿意支付第三方中介(比如投資銀行)成功費,而不愿支付其合理開銷。二是在美國尋求并購或者投資標的時,中國公司很多試圖利用多家中介機構尋找標的來提高命中率,但是美國的中介機構一般希望獲得獨家授權。三是中國公司很多缺乏評判遴選中介機構的耐心。他們在評判中介機構時,往往在找過于簡單化的“排名”,或者以比較收費額度為主。
由于以上觀念上的差別,中國公司遍地撒網尋找“項目”,經常出現以下局面:有能力尋找合適的標的的中介不愿接受中國公司的聘用,而愿意接受中國公司無開銷補償加無獨家授權的聘用的機構或個人,經常沒有能力或者專注程度尋找到合適標的。
此外,很多中國企業對對合同的重要性沒有充分的重視。“就拿美國人和中國人的對待并購的方式相比:美國人投資首先要求由自已的律師起草合同,因為自已聘請的律師起草的合同能夠把對他有利的條款和保護都寫在里面,對自已最為有利。中國人講求君子風度,比較謙讓,不愿意為誰起草合同產生爭議,甚至有的認為讓對方起草合同比較省事,而且能節省律師費。”
其實,在跨境并購交易中,合同不僅僅是個形式或者技術性的文件,它直接決定風險在雙方之間如何劃分,是企業把管理和把握風險的最重要工具。比如“分手費”,在談判中,雙方都希望降低由于對方原因帶來的交易不確定性,為了增加交易確定性和保障,雙方會達成“分手費”的約定,即如果由于一方的原因致使交割條件不能滿足,應當支付給對方分手費用。
近期媒體爆出,萬達集團與DCP(Dick Clark Productions是一家為好萊塢制作頒獎典禮的電視制作公司,1957年創立,擁有20多項著名IP。)一筆高達10億美元的交易已經確認終止。萬達為此或許將支付高達5000萬美元的“分手費”。
柳治平認為,“中國隊”也在進步。“我一般建議他們循序漸進,對于來美國并購條件不成熟的團隊,可以考慮先以消極投資人身份投資美國目標公司或者其同行業公司,以觀察員或者董事會成員身份進入公司董事會,實質性地參與公司運作2-3年左右,有一個學習了解以及信心共建的過程,再審慎地謀劃海外并購。”
“另外,很多中國公司來美國尋求好的資產,把它們拿回中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這個模式避開了美國這個不熟悉的商業和法律環境,回到買家熟悉的中國,實現并購交易的潛在商業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