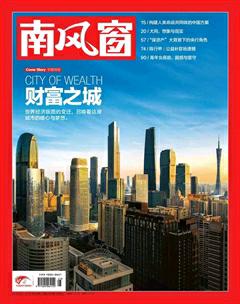一所“暴力學校”的存在與消失
向治霖
一所專收有網癮、厭學、叛逆等類型學生的民辦學校,用了有800年歷史的豫章書院的名號。“用國學中的精華部分啟發年輕學生”,創建人如此說。
書院內,名目混雜:既設《論語》、“六藝”等儒學經典課程,也有以古代監察為名的“告密”、“連坐”制度;學生間設“議員”“學長”;日常生活又在教官監控下實行軍事化管理;高強度體訓外,懲戒有戒尺戒鞭,還有舶自日本、打上“森田療法”標簽的煩悶室……
身著古裝,書院學生仿佛回到另一個時空的“古代”,在這種怪異感中學著競爭、生存。當然,他們本不必回到這里。
“危機孩子”
兒子黃遠思的心里話,黃輝不是聽到的,是看到的。
2010年9月14日在煩悶室,黃遠思先睡了3天,醒來的晚上漸漸感到難受了,他開始寫日記:“錯的,對的,過去的事一下子涌進了腦海里……”
四下無聲,煩悶室內約10平米,只有高處的排氣孔和兩重加鎖的門的縫隙與外相通。當時24歲的黃遠思不怪父母騙他到這里,他覺得父母用心良苦,不富裕的家湊出3萬元治療他的網癮。
他形容網癮是一種感冒,只要碰到電腦“感冒”立馬痊愈,身體充滿精神,幾天的時間便眨眼而過。因為網癮,黃遠思2006年讀高二時被勸退,休整一年轉學到有親戚照應的高中。再次輟學,他開始打工,在江西學汽修,到東莞工廠做普工,到廣州當保安,每領到第一筆錢,黃遠思就要去網吧“放松一下”,直到花光所有的錢。黃的老板常常到附近的網吧找人,有一次找到他,“頭杵在鍵盤下睡覺,死了一樣”。他被開除,換下一份工作也是這樣。
兒子在青春期受太多苦,一直讓黃輝內疚。2003年,黃輝與黃遠思生母離異,凈身出戶,帶走黃遠思,先后寄養在隔壁縣的妹妹家和哥哥家。黃遠思在成長過程中不少遭到白眼。

黃遠思上了高中,黃輝也回到江西,接兒子回了他的“新家”。黃輝的現任妻子卻希望他能少管這個兒子,最好不管,兩人為此吵了不少架。黃輝又將黃遠思寄養到了姐姐家。但此時,兒子開始待在網吧睡在網吧,不回任何一個“家”了。“現實太壓抑,在(網游)里面可以呼風喚雨”。
同在江西,24歲的楊光寅也記恨父母,他幼時記憶中父母經常吵架。3歲時,楊光寅蹲廁要扶著眼前的水管,楊發看不慣,拿一把剪刀磨他的門牙,這是他所記得的父親第一次施暴。
到高中, 楊光寅發覺自己“長大”了。父親有一次揮來皮帶頭,他迎手抓住了,搶了過來,父親改用衣架,掄掃帚,還是占不到優勢。楊光寅不再忌憚父親了,他開始還手。
2012年高考后,楊光寅沒考上理想的大學,也不愿去父母聯系安排的本地大專。楊光寅鎖自己在房間看小說,偶爾上網,父母每早晚都催他去大專報到,他不在意,但感到厭煩,時間一久就開始吵架,但父親的暴力對他早就沒了效力。沖突最激烈的一次,楊光寅砸爛了家里的門、沙發等家具,木質的防盜門從正中間裂開成錐形的碗口大的洞,遍地狼藉。
打砸事件發生在2013年9月1日,楊光寅自閉在家已過了一年。兩天后,他被強迫去了豫章書院。
戒尺、龍鞭、煩悶室
在南昌市青山湖區羅家鎮儒溪吳村的民宅間,略顯突兀的徽式建筑便是豫章書院,仿古樓牌后是一個大院,院中空地擺一尊孔子像。每天早上五點半,約百名書院學生起床拜像,他們中的大多數要么如楊光寅那樣被強制押送過來,要么被父母欺騙而來,在豫章書院的定義中,他們都是“危機孩子”。
這個定義在家長看來是成立的:浙江女孩黃玲讀初一時被高年級學生敲詐“生活費”,整整一學期沒錢吃午飯,到了初一下學期,她抗拒去學校;山東男孩周義在一場大病后成績下滑,一年后確診抑郁癥,“愛上網,不愛和人打交道”;江西上饒男孩肖瀟,厭學,寧可讀體校或外出工作;同在上饒的劉歸,他的父親鐘情傳統國學,而他與父親關系不好,表現叛逆……家長們把“危機孩子”送到這里,支付一學期(半年)31250元的費用,期待孩子改正、改善。
煩悶室是學生進書院后的第一站,大部分人是被教官強制拉進去的。書院教官多服過兵役,他們會先對學生搜身,拿走包括有鞋帶的鞋,帶金屬絲的女生內衣等所有“可能用來自殺的東西”,再把學生押進煩悶室,關門上鎖。周義進煩悶室之前反抗激烈,打了教官,他被按倒在地,過程中失禁了,教官脫了他的衣服,他赤裸著被關進煩悶室,里面昏暗潮濕,鋪著大理石磚,只有一床軍用棉被和枕頭,一個排泄用的中號塑料盆和一臺壞了的空調機。周義哭著睡去,醒來發現這不是夢,又哭了。
睡覺、排泄和吃飯都在煩悶室內,最少要關夠7天。豫章書院校長任偉強也確認了這一做法,他接受央視采訪時解釋,剛來的孩子會有一些對抗性,有的甚至會攻擊老師,單純的語言溝通沒有效果,“我們就通過一個相對比較緩和一點的方法,讓他先把這個情緒疏導開來”。他介紹,這是一種名叫“森田療法”的心理治療方式。
浙江女孩黃玲是和父母一起參觀書院時自愿留下的,因此沒進煩悶室,進校后她發現,參觀時吸引她的古箏、書法課很少有,更多的是上書院自制的“修身科”、體訓和“考德”。“考德”課在晚上,全部學生集合到大教室“勝友堂”站著,吳軍豹等書院高層和老師在臺上,清算每個學生在當天犯的錯誤,被點名的學生上前領受教官的戒尺。黃玲印象中,戒尺最少3尺起,每天不挨戒尺的學生不超過10個,戒尺直抽手心,越躲打得越狠。
校長任偉強接受采訪時則表示,書院體罰學生有審批程序和要求,不會隨便一件小事就進行體罰,為了控制力度,“有時會先打自己幾下”。在書院當過教官的周文亮曾親手打過學生,他介紹,打戒尺是很平常的,第一下就會起個紅印子,后邊再打就會紅腫,“我個人覺得肯定是做得很過的”。
關于戒鞭(又稱“龍鞭”)的材質,也存在兩種說法。任偉強稱,龍鞭是“約81厘米的一個竹炭纖維(棍)”,而在受訪學生口中,龍鞭是材質為鋼筋或玻璃鋼的一根金屬質地的棍棒,約中指粗,是他們最恐懼的懲戒工具。
14歲的肖瀟曾挨過兩次龍鞭。2016年5月,肖瀟所在宿舍出現偷竊事件,他作為寢室長被罰龍鞭1鞭,“只一下,屁股火辣辣地疼,手能摸出來有一道痕”。當年8月,肖瀟“二進宮”面臨10下龍鞭,他感受到其中有本質區別,龍鞭打得很快,一鞭一鞭之間只隔著三五秒時間,“雖然手腳被人壓著,但我感覺自己整個人痛到跳起來了”。
“小王國”
鞭尺之下,書院學生看上去克服了他們原有的“危機”。
書院生活重復而單調:每天從5:30起床開始,10分鐘全員集合到空地,作禮孔子像,接著吳軍豹在前臺講話30到60分鐘,晨儀過后洗漱、吃早飯,飯前也要集合,按隊列依次進食堂,三餐都是這樣,
一般上午學習吳軍豹自制的《修身科》和三節文化課,下午很少有老師來,學生就上自習或體訓,晚飯后集合看《新聞聯播》,接著上晚自習,到晚上9點“考德”,結束后回宿舍休息,10點熄燈。
學生在“考德”所挨的戒尺數由當天表現決定,全天候的監管從起床開始,從疊被到內務衛生,上課是否有動作、有無交頭接耳,是否20分鐘內吃完飯……書院從老師、教官到食堂工人都有權反映、記下犯錯的學生,留到“考德”懲戒。書院有初一、初二、初三和大專四個班,每個班一兩名“學長”和三四名“議員”負責記錄,同時也負責監察,戒尺數視錯誤的嚴重程度來定。
學生間的互相舉報也是重要的監察一環。每到課下,有學生會偷偷溜到老師處打小報告。對告密者,同學彼此心照不宣,這一行為受到書院制度的“鼓勵”:成功的告密者,可在當天減少自己的戒尺數,還能獲得一些糖果和額外的加餐,更重要的是在老師前爭表現,有利于得到學生中的“三階官職”—寢室長和班長是最低階,往上是“議員”,“學長”最高,后兩者幾乎不會受到懲戒。
“三階官職”的爭奪自然演化為小團體的“窩里斗”,這在男生之間尤甚。部分受訪學生介紹,住在一間宿舍下的同班級男生自然選邊,形成小團體,團體間互相檢舉錯誤,頻繁給對方設置陷阱,比如挑釁打架,對方一旦動手就中了套,被抓現行。在豫章書院,“打架”和“談戀愛”、“頂撞師長”被稱為三大紅線,是屬于“龍鞭”的嚴懲項目。
和人打交道是劉歸所擅長的,捱過第一個月,他感到日子一點點舒服起來,“只要和議員學長搞好關系,他們就不記你的名字了”,他告訴記者,在里面一直受欺負的,要么脾氣太沖,要么就是人太笨了。其實搞好關系在哪兒都一樣,因此,“議員”“學長”身邊從不缺人追捧,有人的父母來看望,帶來的零食一定分給他們,平日的洗衣服、衛生等活都有學生幫著干。
女生方面,黃玲對“內斗”也有同樣感受。某一天在宿舍熄燈前,黃玲看到隔壁床女生捂著頭,看上去很焦慮,女生主動搭話:“告訴你一個秘密哦,我今天傳了紙條(給男生),不知道有沒有人看見了,有就完了”,她越說越不安,就快哭了,黃玲就安慰她:“沒什么,我也傳了,要挨打我們一起挨”。隔天,僅黃玲一人因“傳了紙條”被打戒尺,第三天的晨儀上,她被吳軍豹點名批評,說她“和男同學搞來搞去,把學校當公園,把教室當賓館”。此后,黃玲在宿舍只聊學到了什么又領悟了什么。
不會打架、不會甜言蜜語的楊光寅一直沒能適應,“不知道為什么,每個人都可以欺負我,活得很窩囊”,楊光寅說,那里就像是一個小王國,他是其中最低端最下賤的……年底,楊光寅的外婆來探望他,看到暴瘦的孫兒邊哭邊叫,你怎么這么苦,外婆回去不久,楊的父母被迫前來接他回家,楊光寅回憶出門那刻,他很想打父母,但忍住了。
三人相見無言,一路上了車,楊光寅咬牙說出第一句話:“世上竟然有這樣的地方。”坐在前排的母親沒有回頭,回答他:“世界上這樣的地方多的是。”
尾聲
在豫章書院體罰學生的事件曝光前,大多數離校學生將這段經歷埋藏,從不與人說起。黃玲在2015年畢業后,回到浙江讀了衛校,現在是實習護士;由于厭學被兩次送到書院的肖瀟,出來后回學校待了一周,再次輟學,開始外出打工;劉歸直接沒回去學校,他玩了一年多“玩膩了”,今年轉學為藝術生,開始準備高考……剛出書院時,他們都試圖告訴父母里面的真實生活,父母們聽后表情都很平淡,都沒說什么,久而久之,他們也不再對父母說什么。
周義在2016年9月回到山東家里,他覺得自己整個人在呆滯狀態,又怕被送回書院,父母說什么就做什么,“處于極度恐懼的狀態”。周義同時在網上曝光,但收獲甚微。
2017年10月18日,周義在某問答社區發現了博主“溫柔”關于河南某校老師沒收學生手機的話題。“溫柔”的帖子引起大量關注和討論,周義想著試一試,便向他爆料了豫章書院的經歷。10月25日,“溫柔”發帖《中國還有多少個楊永信?》,這一擊掀起了一場輿論風暴。
10月30日,南昌市青山湖區多部門聯合調查后回應,網帖反映的問題部分存在,書院確實有罰站、打戒尺、打龍鞭等行為和相關制度。對此,已責成區教科體局對該校教育機構進行處罰,對相關責任人進行追責。
11月2日,豫章書院回應爭議:已主動申請停辦,待政府部門批準后,由家校溝通對在校生逐步分流。
11月3日,當地民政局同意豫章書院申請注銷,此后數天之內,百余名學生分流被家長帶走。
事件始末,吳軍豹一直沒有現身回應。記者通過微信留言等多渠道聯系,均未取得回復。
七年過去了,30歲的黃遠思已經成家立業,有了一個3歲的女兒。他顫抖著手,把新聞發給父親看,說:“吳軍豹這次栽了”。
他決定起訴吳軍豹,同時要起訴的還有11名學生。11月初,河南刑辯律師付建以公益形式接下委托,免費代理了此案件。
楊光寅也是起訴人之一,2014年初回家后,他在當年10月確診重度抑郁。
關于豫章書院體罰學生的新聞不斷刷新,學生或多或少轉給了父母。但他們多數被平淡回應,都過去了,現在都出來了別管那些。
劉歸的父親一度認為是兒子撒謊,新聞報道后,他向兒子鄭重地道了歉。劉歸有時會“指桑罵槐”,看到電視里有父母教訓小孩的畫面,劉歸就說:“這是誰家的父母啊”,他聲音很大,轉下一句:“畜生不如,把孩子送到這種地方”。
他余光瞟了一眼父親,在電視機前明暗的光線里,劉父不動聲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