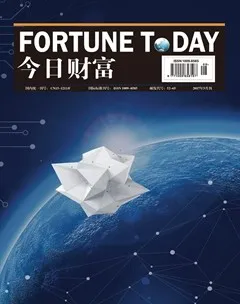媒介人類學視域下的新疆少數民族文化旅游
一、媒介人類學
媒介人類學是討論媒介在現實世界中位置相關問題的人類學的一個分支,隨著傳播媒介技術對社會生活的影響逐漸變大,人類學家開始將眼光轉向過去不愿意涉足的媒介領域,在以英美人類學為代表的西方學界關于媒體人類學的研究實踐,始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但是對于“媒介人類學”這個概念的研究,已經到了20世紀末21世紀初。目前西方學界對于“媒介人類學”的概念仍沒有達成統一的共識。美國傳播學研究者瑞克·羅森布勒曾給人類學做過這樣一種寬泛的界定,他認為媒介人類學應該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媒體研究中使用人類學的概念和方法,一類是人類學對媒體的研究。阿筠-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在一篇副標題為“對跨國人類學的看法和質疑”(1991)的文章中創造了“媒介景觀”(mediascapes)這個概念,該文回顧了早期人類學科的自我界定,并指出了大眾傳媒在20世紀后期人們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以及人類學對其分析和實用性意義探究的迫切要求。英國文化研究探討大眾傳媒在當代文化霸權研究項目中的中心位置,聚焦媒介消費,在消費過程中,媒介被復制、改變或抗拒。原住民傳媒采用的獨特文化運動同樣吸引了國外學者的眼光,這種運動是對大眾傳媒進入初先民族生活的一種回應。大眾傳媒主要通過衛星和商業電視強行進入的,埃里克-邁克爾斯(Eric Michaels)的研究主要表現了原住民在面對大眾媒介強行進入時采取的回應都努力將情況朝對自己有力的一面轉變。安德森在討論小說和報紙及廣播電視時,認為媒介在民族的制造和想象的塑造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目前國外的媒介人類學研究出現兩個明顯變化:一是傳統上位于鏡頭前的人們逐漸有能力接近和使用媒體,二是出現了一種知識上的轉移。這種變化擴大了對人類學影視工作者如何再現他者的質疑。
國內媒介人類學的研究開始于本世紀初,主要由從事人類學研究及新聞傳播的一些學者來完成的,這些相關研究并未明確地歸于媒介人類學范疇,在此之外中國大陸第一套“媒體人類學”譯叢也出版面世:周永明的《中國網絡政治的歷史考察》、布萊恩-拉金的《信號與噪音》(Signal and Noise Media,Infrastructure,and Urban Culture in Nigeria,2008)、金斯伯格等人主編的《媒體世界》(Media World:Anthropology on New Terrain,2002),普尼爾瑪-曼克卡的《觀文化,看政治》以及阿布-盧赫德的《國家戲劇》。這一譯叢的出版,讓大陸的學者對媒體人類學有更為具體的認識和理解。 國內對少數民族文化產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傳承及經濟發展領域,媒介產業本身就是文化產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媒介是文化產業的重要載體,因此從媒介人類學角度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產業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
二、媒介變遷對新疆少數民族文化旅游的影響
(一)大眾傳播對新疆少數民族文化旅游的影響
在全球化過程中,由于新疆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不僅受到了來自漢族文化的影響,同時深受中亞國家的影響,受西方國家的影響。以美國主導的大眾傳播對文化產品的分配,是世界文化同質化的主要原因。二戰后,歐洲被削弱,美國力量上升,接受了歐洲過去的殖民地,新的帝國主義格局形成,美國對以電子為基礎交流體系進行通斷,這種壟斷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的廣播體系,這是一種完全建立在廣告財政之上的商業體系,已經成為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廣播系統的原型。這種強勢的大眾傳播體系對地方傳統文化的保護造成了威脅。邊緣文化逐漸吸收越來越多的中心傳過來的模式與意義,逐漸變得與中心模糊不清,雷同,文化的差異性被逐漸消除。
權力是傳播學領域最經常提及的一個概念,在傳播學的批判視角中,龐大的權力機器生產出代表統治階級意愿的意識形態,大眾媒介正是意識形態符號化的絕佳場所,知識是一種權力的工具。大眾傳播媒介以愈來愈強勢的姿態參與到少數民族的生活中,并以愈來愈明朗的方式對其行為產生影響。我們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對新疆的少數民族文化進行宣傳,而宣傳是一種具有明確目的及指向性的大眾傳播活動。大眾媒介機構包括電視臺、廣播臺、出版社等運作組織,這種大型組織實體和機構,在參與“制造”與“規范”整個社會不斷流動著的“文化價值”。大眾傳播媒介對社會具有很強的整合效果這是毋庸置疑的。
大眾傳播分為對內傳播及對外傳播,如果說經濟驅動是新疆的少數民族文化旅游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同質化傾向的原因,那么大眾傳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南疆以農業為主的文化與北疆以伊犁地區的高山畜牧業為主的文化出現趨同。新疆多民族聚居的多樣文化逐漸趨向于西北文化。以伊犁地區為例,哈薩克族的艾肯彈唱旅游節、察布查爾縣錫伯族旅游文化節、昭蘇天馬節等文化旅游在內容與形式上,所體現出的文化核心元素趨于一致,對外宣傳的內容也雷同。因此新疆少數民族一些極具本民族特色的文化面臨著傳承危機。
大眾傳播媒介的話語霸權還體現為對特殊群體的“妖魔化”及對弱勢群體的“邊緣化”。在大眾傳播過程中,少數民族的聲音很少能夠得到全面的呈現,在我國社會轉型期階段,產生了許多新的社會階層,社會分化現象日益嚴重。由于信息分配的不均衡、物質基礎的差異及選擇性接觸,大眾傳播的受眾也開始出現新的變化,強權受眾階層由于其物質及文化優勢,直接或間接地控制著媒介的信息傳播,從而導致信息傳播活動中占絕對優勢的媒介話語霸權出現。這種話語霸權直接的后果就是導致大眾傳播媒介對弱勢群體的傳播權、知情權和媒介接近權等一系列權力的公開侵害與剝奪,使弱勢群體日益處于社會的邊緣,失去了與主流話語權對話和發生的機會。
(二)自媒體對新疆少數民族文化傳播的影響
“自媒體”是搭載第四代及第五代傳播媒介技術,以普通大眾為信息發布者,通過媒介互聯技術向他人發布信息及新聞的傳播方式。新疆的少數民族文化旅游在發展過程中,一個挑戰就是如何將新疆的少數民族文化傳播出去,以文化傳播帶動文化旅游。民族文化傳播,究其本質就是要解決在永遠變動著的世界里如何堅定地保持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問題。少數民族的文化傳播最重要的是在傳播過程中保持文化的原生態,規避同質化,能夠提煉出民族文化的精髓進行傳播。自媒體對新疆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播過程中,關鍵點大部分集中于美食、服飾、特色音樂舞蹈等方面,娛樂性較強,主要集中于大眾消費的熱門領域,對少數民族宗教信仰、語言文字、文化內涵,社會生活規范等民族文化的核心探討較少。傳播的內容太過迎合和圍繞時下熱門的少數民族文化消費,敷于表面,聚焦于少數民族文化的淺層,對少數民族文化的精神內涵挖掘不夠,因此造成體驗者感覺看完阿勒泰就等于看到了整個新疆。
同時,隨著手機媒介的興起,海量的信息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傳播,著名的傳播學家蒂奇諾討論大眾傳播造成社會分化時提出了一種假說,在現代信息社會里,隨著信息傳播的增量,由于社會經濟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會經濟低者更快更有效地獲得和利用信息,因而,大眾傳播媒介傳送的信息越多,這兩者之間的信息格差和知識格差也就越有擴大的趨勢。也就是說,在信息接收過程中,必然存在兩種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貧窮者,隨著信息傳播的增量,這兩者之間的差距也將會越來越大,而在現代化過程中,信息同樣意味著經濟價值,因此極易造成國家、地區、人與人之間的“馬太效應”,富者越來越富,而窮者越來越窮。新疆地處偏遠,地區發展長期落后于東部地區,地區信息建設的成本過高,因此在新疆仍然存在著眾多的信息貧困者。同時,由于受教育水平較低,新疆的中老年群體對手機及互聯網的使用嚴重落后,對自媒體的利用遠遠不足,因此利用自媒體推動少數民族文化傳播后來居上,實現信息傳播的跨越式發展對于新疆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三、新疆主流媒體對疆內民族文化旅游宣傳存在的問題
盡管新媒體在當前的發展成井噴之勢,在新疆不乏有很多運作良好的新媒體平臺,但是大眾傳播依然是推動文化發展最強勢的力量。
(一)報道內容單一
報道內容單一主要表現在新疆對外新聞宣傳上,新疆主流媒體的對外宣傳主要體現新疆經濟發展的速度及內部各民族的和諧關系,表現為穩定、團結等。主要重視策略性的宣傳,缺乏文化類的宣傳。對各民族的文化宣傳呈現碎片化、片面化,長期使受眾對新疆的少數民族文化形成刻板印象及固化認識。太過于注重挖掘少數民族的“特色”而忽視了少數民族文化的變遷。
(二)議程設置明顯
在對新疆的主流媒體在對外宣傳上,對外宣傳方針與云南貴州等地存在明顯區別,相對于其他省份在宣傳旅游時倚重自然風光,新疆更加注重刻畫民族團結及社會穩定和諧,因此在做媒體報道策劃時,民族團結是宣傳少數民族文化旅游最先要考慮的因素和議題。
(三)信息連接度差
一方面新疆主流媒體在宣傳新疆的少數民族文化旅游時主動性較差,直接導致了新疆少數民族旅游的知名度不高,對信息有明顯的挑揀痕跡,對新疆各少數民族的形象描述有失偏頗。另一方面,新疆主流媒體對外宣傳報道嚴重滯后,不僅體現在時間上也體現在制作質量上,缺少精品,炒冷飯現象嚴重,對一個議題重復報道,缺少新意。
四、整合與互動——媒介人類學視域下新疆少數民族文化旅游的發展路徑
民族傳統文化是少數民族地區具有歷史傳承性的文化體系,是少數民族地區大力發展文化旅游業的基礎,新疆的少數民族文化旅游業發展要取得實效,就必須提高媒介使用的效果,利用文化事業體系提高文化產業的發展,實現良好的互動。
(一)增強傳播學與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互動與整合
大眾傳播媒介的技術弊端恰好可以由新媒體來補充,尤其對于新疆來說,文化旅游還沒有形成一定的模式,文化消費生產還處于初步發展階段,面對激烈的競爭,就不得不考慮如何使用好大眾傳播媒介的宣傳功能及新媒體的交互功能。大眾傳播媒介傳播的信息量是一定的,受播出時間及渠道的影響較大,但是其傳播的內容導向性明確,有內在邏輯,但由于客觀條件所限內容不夠豐富,新媒體恰恰補充了這一缺點,新媒體傳播的內容是海量的,且接收更加方便。因此新疆的少數民族文化旅游業如果想取得階段性的突破,那么政府與企業的互動整合、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互動與整合尤為重要。政府在確立了傳播導向性的同時,還應該采取措施提高少數民族文化旅游參與者的積極性,將他們的聲音發出來。從旅游者的角度看,旅游是一種文化消費,文化元素使旅游產品增值,因此政府各部門對文化旅游高度重視。大眾傳播媒介的工作者在采寫新聞時,除了自己的見聞一般還會從政府、專家、企業等權威部門獲得信息,從當地少數民族那里獲得的信息比例非常小,忽視了主體行為,而人類學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與之恰好相反,因此少數民族自己的聲音要發出來,在旅游實踐中,少數民族及少數民族的文化一同構成了旅游資源的全景。
(二)避免媒體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差異化建構
旅游開發背景下,媒介的少數民族文化建構被置于商業化背景中,“差異”使少數民族產生一種異域情調的美,刺激了外界的好奇心和窺探欲。差異主要通過服飾、語言、風俗等體現出來,大眾媒介往往已經成為差異制造的共謀者,積極的參與了少數民族差異化符號的挖掘、包裝與傳播實踐中。同時,大眾傳播媒介又是差異的傳播者,在旅游與文化產業發展的背景下將差異廣泛傳播,吸引圍觀。當然避免媒介對少數民族的差異化建構并非要求媒介失真地刻意地表現少數民族的現代性,在新疆舉辦的旅游節上,節目錄制時通常會要求臺下的觀眾穿上傳統服裝,即使這種服飾在日常生活中已經被大眾服飾所取代。
(三)保護少數民族文化傳統與文化產業化的互動與整合
在市場化的驅動下,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成了旅游的消費符號,少數民族自愿將本民族的文化包裝成一種可以消費的文化,旅游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了當地居民的生活,但是旅游經濟的發展對民族文化的傳承也造成一定影響,甚至會引導少數民族的文化向世俗化商業化發展。民族文化是少數民族文化旅游的核心,因此在發展少數民族旅游中如何保護傳統文化成了一個難題。保護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并不意味著不產業化發展,而是在產業化的過程中應該有意識地保護本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避免在市場化的過程中走向庸俗化和同質化。
五、結語
隨著全球化的加快,媒介對于人的影響研究不再是傳播學界的專利,人類學研究毋庸置疑已經找不到過去那種與外界阻隔的原住民居住地,媒介已經成為文化研究必然要考慮的因素,新疆的少數民族文化旅游有其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的意義,媒介人類學在中國的研究還并不成熟,本文受薩義德對媒介的中東報道的影響,結合新疆少數民族文化旅游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以期為少數民族文化旅游研究提供一種不同的視角。(作者單位為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民族學15級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