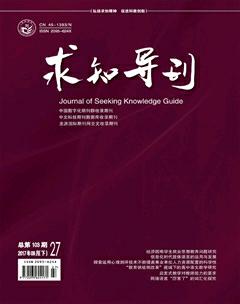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理論對我國文化建設的啟示
彭堅 韓雪晴
摘 要:法蘭克福學派獨創性地提出了“文化工業”這一理論,并從這一概念出發,揭示出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中“文化工業”的商品化、技術化和標準化的特性,他們批判了“文化工業”在資本主義社會大生產下喪失了文化的真正本質,文化成為欺騙人、統治人的異化的文化力量,文化的異化也把人推向單調平庸。基于此,我國的文化建設要在吸收“文化工業”批判理論的基礎上,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用先進文化引領文化建設的方向,注重文化創新,文章就此展開論述。
關鍵詞: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理論;文化建設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一、“文化工業”理論的主要內容
“文化工業”理論是法蘭克福學派在批判“大眾文化”的過程中提出來的。1944年,霍克海默在《藝術與大眾文化》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文化工業”的概念;1947年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出版的《啟蒙辯證法 》一書中,全面探討了“文化工業”。在這之前,他們使用的是“大眾文化”,在這之后,他們則用“文化工業”取代“大眾文化”。通過“工業文化”理論的提出,法蘭克福學派對科技革命影響下的“文化工業”化傾向提出了批判。
1.“文化工業”的商品化及帶來的“商品拜物教”導致文化和人的雙重平庸
法蘭克福學派之所以用“文化工業”取代“大眾文化”,是由于“文化工業”映現了““文化工業”資本”。資本的本性即是追逐利潤的最大化,資本侵入文化領域必然使之發生變質,文化產品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創造性的價值藝術品,而是工業機械生產出的批量商品,商品化成為“文化工業”的最顯著特征。
阿多諾堅決認為,“文化工業”的產品完全由藝術品變為商品,由市場的需求決定,目標也是在市場上銷售。文化與資本合作,使得文化淪為了資本擴張的工具,“文化工業”的生產、銷售都被納入“文化工業資本”運作范疇,完全由市場的經濟規律所支配。文化商品化后,對文化作品的創作者來說,上座率高、經濟效益好就會成為他們的至上追求,而直接忽視文化作品本身的審美價值;對消費者來說,本來消費的是“文化工業”產品的使用價值,在市場導向原則下,使用價值往往被商業性的交換價值所掩蓋甚至完全喪失,這樣人們看重的只是文化產品的市場價格,而不是其文化內涵本身,這就形成了文化領域中的“商品拜物教”。“文化工業”的完全商品化,所帶來的后果不只是人們對物欲的強烈追求,更主要的是,正如法蘭克福學派進一步所分析的那樣,人們對市場價格高、廣告宣傳的這類文化產品的盲目崇拜把自身也推向單調平庸的一面。
2.文化生產的過于技術化導致文化墮落為統治者維護秩序的工具
法蘭克福學派強調,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給文化的傳播提供了現代化的載體,由此才產生“文化工業”和實現文化的產業化,否則不可能產生相應結果 。法蘭克福學派稱之為“文化工業”的技術化,也是“文化工業”的第二個特征。
除本杰明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推動了文化藝術的進步,其他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對“文化工業”的技術化都持否定的態度。阿多諾就認為,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最終會導致“文化操縱”,即文化及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被技術的工具理性所支配,人的理性已是純工具化的思維。馬爾庫塞認為,文化傳播的過程本身就是文化操縱的過程。通過傳播媒介的技術過濾,“大眾傳播媒介的專家們傳播著必要的價值標準。他們提供了效率、意志、人格、愿望和冒險方面的完整訓練”[1],傳播進來的價值觀念等意識形態的東西,“事實上,它們被用作社會凝聚的工具”[2]。實際上,這些大眾傳播媒介充當的是政府“代言人”的角色,統治者利用文化與技術的同謀,使其為統治者服務,導致文化墮落為統治者維護秩序的工具。正如法蘭克福學派史專家馬丁·杰伊一針見血的評價:“技術在美國廣泛服務于“文化工業”,恰像它在歐洲幫助權威政府的控制。”[3]
3.文化產品的標準化導致自身成為異化的文化力量
法蘭克福學派把文化生產和文化產品的齊一化、標準化歸納為“文化工業”的第三個特征。法蘭克福學派認為,文化和藝術真正的本質在于創造性,這種創造性表現為自由和超越性:人可以自由地在作品中實現自己,藝術是對現存制度的否定和批判。馬爾庫塞也揭露了藝術自由和超越性的本質,將藝術看作是構造現實的一種力量。但是,“在壟斷下,所有的大眾文化都是一致的,它通過人為大方式生產出來的框架結構也開始明顯地表現出來”,文化作品像流水線上的工業生產品,千篇一律、毫無個性,這就是“文化工業”的標準化。標準化的文化產品借助現代科技手段批量地生產、復制出來,文化自身所具有的本真性被不斷消融,慢慢失去自身的創造性。文化本來是人創造的,但是,標準化的文化產品讓文化成了一種娛樂消費品,人沉浸于其中,思想逐漸被欺騙和麻痹,文化反過來就成為欺騙人、統治人的異化的文化力量。
二、“文化工業”理論對我國文化建設的啟示
法蘭克福“文化工業”理論對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全面的反思,進一步拓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視野,對我國文化建設有重要啟示。
1.文化建設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堅持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
法蘭克福學派抨擊最甚的是“文化工業”的商品化,認為商品化最終會導致“文化工業”完全淪為利益需要的商品,把經濟利益置于首位,全然不顧文化的價值及社會效益。文化產品具有商品屬性,文化資源受到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從而促進了文化產業的形成和發展。在我國,文化已成為一種產業并且是我國國民經濟中的支柱產業,文化產業能夠帶來經濟效益的同時,也促進了文化的繁榮和發展。但是,我國的文化建設不能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迷失方向,文化不能完全被資本所控制只顧經濟效益而不顧社會效益。相反,我國的文化建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導向,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這是因為,一方面,從文化的本質上看,文化的價值在于感化、教化大眾,文化作為一種精神力量,在社會發展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對社會發展具有深刻的影響。另一方面,文化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決定我國的文化的根本屬性是為人民利益服務的,因此,在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必須始終體現公益性原則,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的根本原則。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糧,讓人民享有健康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文化作品應是人民的精神食糧,而不是“快餐文化”,優秀的文化作品既能夠喚醒人、鼓舞人和激勵人,又在市場上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也就是說,文化建設要堅持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央視新推出的《中國詩詞大會》和《朗讀者》,不僅取得了收視率高的經濟效益,更為重要的是該類欄目以實現文化自身的價值為旨歸,喚起了人們對古詩詞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世界優秀文學的熱愛,掀起了全民朗讀的熱潮,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這類電視欄目就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統一的文化作品,應大力推崇。endprint
2.文化建設要加強先進文化建設,用先進文化引領文化的方向
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科學技術和“文化工業”的意識形態功能,認為“文化工業”的技術化導致文化墮落為統治者維護統治秩序的工具,但是,法蘭克福學派“拒絕把文化現象還原為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反映”。從政治角度上看,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有利于維護政治統治,關鍵是文化的性質和方向問題。我國文化建設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道路,決定了我國文化建設的性質和方向始終是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要加強先進文化建設,其一,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武裝全黨和全國人民,從根本上保證文化的前進方向;其二,緊緊圍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凝結著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髓,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的價值表達,堅守我們的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用先進文化引領文化的方向,堅定人們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
3.文化建設要加強文化創新,注重文化的獨創性
法蘭克福學派指出文化產品的標準化扼殺了文化的個性和創造性,導致文化異化為統治人的力量。基于此,在我國的文化建設過程中,要加強文化創新,不斷提高文化自身的內在價值和藝術品位。創新是一個社會進步的不竭動力,文化創新是民族繁榮進步和國家興旺發達的根本要求,“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關鍵是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要實現文化創新,根本途徑是立足于社會實踐。文化作品既來源于現實生活,又高于現實生活,這就需要創造者立足于現存的生活和制度,以現實為素材進行文化創作;文化創新要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創新。”中國傳統文化是我們的“根”和“魂”,是我們的精神命脈,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采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推陳出新,按照時代的新發展要求,補充、拓展、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文化創新要走出去,面向世界,世界文明是多樣的,中華民族特色也是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學習其他民族的先進文化而逐漸形成的,中華文化也要在汲取世界文明的養分中不斷地豐富和發展。
總之,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盡管其中存在諸多不足,如當年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理論對文化發展現狀揭露出來的許多問題至今也仍未得到有效解決,但是“文化工業”現象在后來的許多國家中卻是普遍存在的。當前中國在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過程中,也出現了類似于當年法蘭克福學派面臨的諸多問題,因此,在當前高舉文化自信的大旗,建設先進文化的時期,重新探討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對如何更好地進行文化建設有著較大的啟示意義。
參考文獻:
[1](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M].劉 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2](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審美之維[M].李小兵,譯.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3](美)馬丁·杰伊.法蘭克福學派史[M].單士聯,譯.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