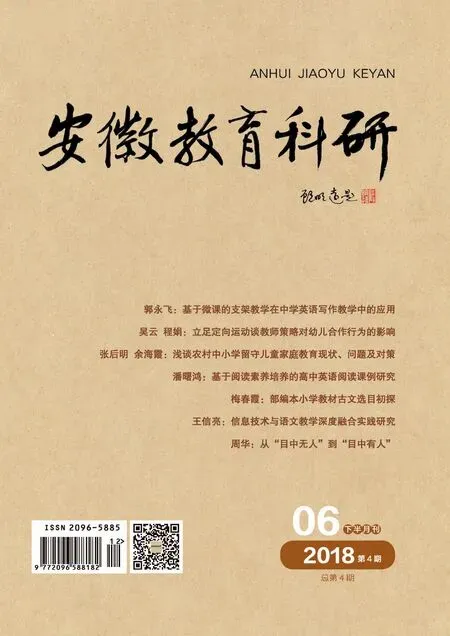不妨允許“亂”讀書
——教師閱讀工程建設之我見
胡萍萍
(合肥市芙蓉小學 安徽合肥 230001)
2018年9月,筆者所在學校新一期“讀書沙龍”新書發放活動中,《將小家變大》《五歲熊孩子教我的事》《乖!摸摸頭》等十余本書遭到教師“瘋搶”,不少教師新書到手即刻津津有味地捧讀起來。這種“洛陽紙貴”的盛況讓校長彭正欣喜不已,忍不住感嘆道:“真沒想到,還會有這樣一天!”
時鐘撥回兩年前,學校剛剛推行“教師閱讀工程”,欣欣然采購了一批教育類書籍,計劃采用“讀書漂流”的方式推進教師閱讀。
當時,學校每個月定期在教師的案頭擺上書籍,殷殷期盼教師能認真閱讀。學校要求教師“每月一交流,每學期一篇讀書筆記”。在監督機制的推動下,這項工程看似紅紅火火地開展下去了,然而在期末回收盤點時,教務部門驚訝地發現,這些教育類書籍大多數沒有被翻閱的痕跡,有的甚至連封皮都沒有去除。
原來,這“繁花似錦”的一切不過是場“海市蜃樓”。
究其原因,教師給出的理由多為“沒有時間”。的確,在我校,主課教師任班主任,副課教師兼任學科以外崗位的現象普遍存在,教師總體課業任務繁重,缺乏空閑時間,難以進行閱讀。
那么,在大背景難以改變的情況下,如何引導教師重拾書本?筆者認為首先應該允許教師“亂”讀書。
在上述案例中我們不難發現,雖然影響教師讀書的首要因素是時間,但是學校以教育類書籍倡導閱讀,其實并不明智。學校將教育類書籍推薦給教師的目的是什么?表面上是為助力教師的專業成長,實則還是為提升辦學效果、辦學成績。這樣的目的就難免蒙上“功利”色彩。
在我校針對教師閱讀興趣的一項調查中,數據顯示愛讀文學書籍的教師有12人,占總人數的21%;愛好推理書籍的教師有10人,占總人數的18%。此外,受教師喜愛的書目還有歷史類、育兒、心理類等,共計12種。而教育教學類讀物僅6人喜愛。
對不少教師而言,教育類書籍只是專業“工具書”,在空閑時間將“工具書”視若珍寶,恐怕常人難以做到。特別教師在高強度工作下,更希望將讀書作為娛樂放松的方式。如果我們能轉變思路,去除讀書工程急功近利的煙火氣,按教師的“口味”做出第一道菜,也許能邁出令人欣喜的第一步。
當然,筆者提倡的“亂”讀書絕不是胡亂讀書。這種“亂”強調的是由心而發,而不是“胡吃海塞”,任性而為。也就是說,這種選擇的“自由”是建立在選擇后的“自在”里,是在良性土壤上生長的奇珍異果。
如何構建教師讀書的“良性土壤”?除了從根源阻截“低級趣味”讀物,構建種類豐富的優質讀物儲備庫,更要樹立榜樣的力量,喚起教師閱讀優秀讀物的興趣。
作為一名一線教師,筆者常常看見小學生對漫畫手不釋卷,卻將經典少兒讀物束之高閣,究其原因是經典少兒讀物對其吸引力不夠,沒能蓋過“輕松好讀”的漫畫。筆者針對這一現象,舉行了多場讀書會,用舞臺劇、經典講讀的方式“誘導”學生們開啟經典。筆者記得一個愛好漫畫的孩子在周記中寫道:“老師講得繪聲繪色,我們聽著聽著,仿佛進入了故事,隨著小羅曼一起憂傷,我好想趕快看到這本書啊!”
閱讀本性為樂,歸根結底要靠內驅力,尹建莉在《好媽媽勝過好老師》一書中談到,對成人來說,持久的閱讀興趣是來源于書籍的“有趣”而不是“有用”。
令人欣喜的是,筆者所在的學校在挫敗后即刻收起“功利”的心態,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遴選出涵蓋各個類別的優秀書目供老師們“投票”選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些書籍居然成了老師們心頭的“白月光”,老師們將其擺放于案頭,一有空就拿來翻閱,還在同事間交流心得體會,一本看完就急切地“呼朋喚友”要求交換。
據語文教研組長宋老師分析,發生此次轉變的原因主要是“放松”,“老師們覺得看現在的書是一種放松,一種休閑,所以都愿意去閱讀。”
為了增強這種“放松感”,也為了擴大這種良好勢態,學校修葺了圖書室,專供師生自由閱讀。經過調研,學校還將每周五晚定為“讀書沙龍”時間,一方面教師一周的忙碌工作暫告一段落,心情上比較放松,另一方面周五晚便于準備免費晚餐,解決部分家遠教師的吃飯問題。目前,“讀書沙龍”活動開展已達六周,每周都有二十幾名教師參與,自發性呈升溫狀態。
人作為群居性動物,“從眾性”特點顯著。在每周的“讀書沙龍”報名中,筆者發現,教師報名往往成“組團”樣態。尤其是同一辦公室的教師,常常一個帶動一個,一個號召一群,在這樣的態勢下,個別“懶得讀書”的教師也會“盛情難卻”去看上兩眼。
現在,筆者所在學校的老師們都在這種“亂”讀書的氛圍里愉悅閱讀,真心希望這種“亂”能成“亂花漸欲迷人眼”,讓教育工作者隊伍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美好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