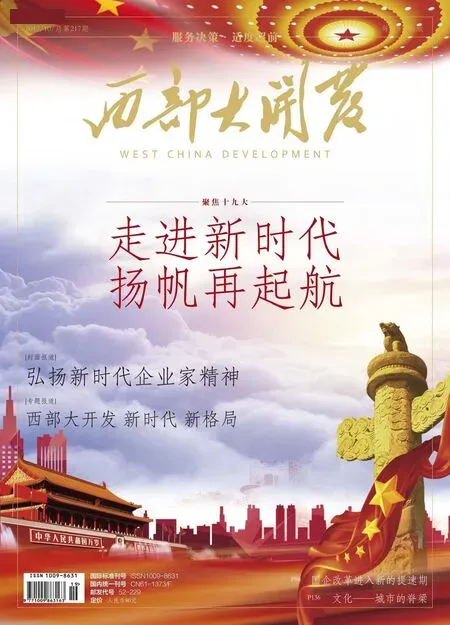吃的藝術(shù)
吃的藝術(shù)
人類熱衷于吃,與填飽肚子的本能不同,現(xiàn)代人的“吃”已經(jīng)從“要能吃”進化到“要好吃”的類型,這是千百年來,人類進化出的特有技能。但地球幅員遼闊,僅中國這一個地方就有無限多種的食材的隨機搭配。隨著《舌尖上的中國》這一電視紀(jì)錄片的熱播,我們才了解了,即便是擺在山溝溝某一小家庭餐桌上的日常小菜,都浸滿了祖先的智慧,講究的習(xí)俗,虔誠的宗教習(xí)慣,以及祖祖輩輩辛勤勞動的汗水。
電影《飲食男女》中,男主角老朱憑借自己臺北名廚的手藝小心翼翼地維持著本就顫顫巍巍的家庭關(guān)系,每日晚餐豐盛如饕餮盛宴,但兒女們迥異的性格和價值觀,依然讓本該其樂融融的餐桌一次次上演分裂和告別的舞臺劇。但這并不妨礙失去妻子的丈夫期待用自己擅長的“做好吃的”的技能來彌補生活帶來的空缺和遺憾,雖然結(jié)果并不盡如人意,但我們難以否認(rèn)的是,吃,在中國,人們早已賦予了其比“吃”多得多的功能與意義。
“吃”,究其本質(zhì)是動物本能,是指用手或工具(筷子,叉子,勺子等)把食物送進口腔,經(jīng)過牙齒咀嚼后下咽經(jīng)食道管進入胃里,再由消化系統(tǒng)完成整個消化過程。“吃”常和“喝拉撒”一起構(gòu)成人類難以抗拒的本能組合,但當(dāng)人類社會隨著工具的進化不斷向前發(fā)展時,“吃什么、怎么吃”這一話題逐漸被抬到桌面上來,尤其在物質(zhì)極大豐富的工業(yè)社會,交通運輸工具速度的飛速提升將各個地區(qū)的生產(chǎn)要素積聚,于是,食材的重新搭配,以及外來吃食的補給,都成為打破傳統(tǒng)吃法,是“吃”進入到更高境界的主要推手。

吃的新玩法層出不窮,正當(dāng)消費者被新花樣搞得眼花繚亂之時,一股復(fù)古潮流又氣勢洶洶席卷而來。追求傳統(tǒng)吃食,在趨近“天下大同”的今天,難免有些苛責(zé)。交通運輸工具速度成幾何倍增之后,不僅打破了地域局限對食材的保護性,同時為了擠占更大的市場以換取更多的利潤,生產(chǎn)和進化出迎合當(dāng)?shù)乜谖短厣摹巴獾夭恕保@不倫不類的“外地菜”仿佛一時間成了本地的新傳統(tǒng)。另一方面,人類分工的細(xì)化,讓原本復(fù)雜的吃飯工序充分簡化,現(xiàn)代人從超市、菜場買到半成品,只需數(shù)十分鐘,就能烹制出一桌飯食。

汪曾祺談吃
如果說人在烹制飯食上時間的縮短,體現(xiàn)了人類對“懶”的極致追求,那么在這個飛速運轉(zhuǎn)的時代,能為了招呼人完成從采買到烹煮這一在過去看來稀松平常的完整工序,本身就該是情感的凝結(jié)與社會關(guān)系的升華體現(xiàn)。因此,相比于下館子解決臺面上的問題,可能請人回家吃飯更能顯示其人情味吧。汪曾祺在談到吃時曾說道,“到了一個新地方,有人愛逛百貨公司,有人愛逛書店,我寧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雞活鴨、新鮮水靈的瓜菜、彤紅的辣椒,熱熱鬧鬧,挨挨擠擠,讓人感到一種生之樂趣。”

社會人口流動頻繁也常常引發(fā)“吃”上的激烈爭吵,有“甜咸之爭”,也有“酸辣之辯”,拋開爭吵不說,人總能從爭論中發(fā)覺這世上存著一些與自己全然不同,但又息息相關(guān)的人們,也許我們有朝一日也不會接納他們“吃”的方式,但至少當(dāng)下,我們正在了解他人的生存文化,開始了解了,路就不遠(yuǎn)了。正如汪曾祺所說,“有些東西,本來不吃,吃吃也就習(xí)慣了。也就是口味這個東西是沒有定性的。有些東西,自己盡可不吃,但不要反對旁人吃。不要以為自己不吃的東西,誰吃,就是豈有此理。一個人口味最好雜一點,南甜北咸東辣西酸,都去嘗嘗,耳音要好一些,能多聽懂幾種方言。口味單調(diào)一點,耳音差一點,也不要緊,最要緊的是對生活的興趣要廣一點。對食物如此,對文化或者其他的東西也是一樣。”
在“吃”被賦予了很多超出“填飽肚子”的意義以后,“吃”不但成為了文化的傳承介質(zhì),更在不斷創(chuàng)造出新的文化。“吃”在很多情況下就只是吃本身而已,但在更多情況下,其意義不僅僅是“吃”,不論是情感紐帶,還是文化傳承,不可否認(rèn)的是,“吃”都亙古不變的占據(jù)著我們?nèi)祟惿鐣l(fā)展的重要位置,也是人類進步的動力之一。“吃”讓人類感知到生之樂趣,活之盡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