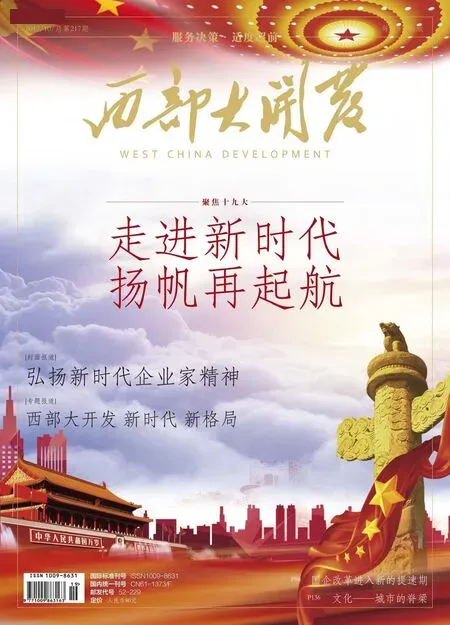燕伋:為后人豎起尊師的最高標桿
文 / 李慧奇
燕伋:為后人豎起尊師的最高標桿
文 / 李慧奇

一
一座兩千五百多年前黃土地上人壘的土筑臺,沒有成為千年風雨侵蝕下的廢墟,沒有成為西風古道邊荒草萋萋的黃土丘,而是直到今天,來自四面八方的慕名者仍虔誠的圍臺仰望,細步丈量,輕步觸感,聲聲驚嘆,這樣神奇的土筑臺你相信存在嗎?
你當然不會相信,認為這是一個古老的傳說。
一座底徑三十多米、高約十余米的土筑臺,這么龐大的土方量,兩千五百多年前竟然是一個人為了思念恩師,以一己之力,用衣襟兜土的方式,歷經十余年而筑成,只為墊足登高眺望遠在千里之外的魯國老師,這樣的奇事你能相信人間發生過嗎?

望魯臺燕伋祠
你還是不會相信,認為這是一個天方夜譚的故事。
但它就真實的矗立在今天陜西寶雞市千陽縣城以西的裴家臺塬上。
這座黃土筑臺,史叫燕伋望魯臺,被后人稱之為中華尊師第一臺。
以這樣龐大的實物形式表達尊師的望魯臺,比煌煌史書中記載的耳熟能詳的《程門立雪》的尊師典故,整整提前了一千五百多年。
這座筑臺人,就是距今2500多年前春秋戰國時期秦地千陽燕家山(今陜西千陽水溝鎮水溝村)人——燕伋。
二
史料記載:召公奭(shi)封燕,五世別為公族,燕伋,其后裔也,生于公元前541年。
五世公族的身份使燕伋的祖父輩們識文斷字。相傳從燕伋幼年開始,他見多識廣的祖父就成為他的啟蒙老師。燕伋4歲時,卓有遠見的祖父臨終時對他父親交代:要用心撫養這個聰慧過人的兒子,若有哪個諸侯國里有學問大、學問深的高人,就一定要送去拜師學藝,教子明大理、識大義,成大器。當年燕伋的祖父不會想到,他期望的這個孫子,日后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他的期望值。
稍大一些的燕伋就開始白天和同村的孩子上山放牧,參加勞動,夜晚跟著父親學文識字。學習中燕伋養成了勤奮、好學、善思的好習慣。正是這種從小就開始堅持不斷的學習和積累,為他日后赴魯求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燕伋18歲時迎娶壤駟氏。據說一次岳父來信告訴他,魯國曲阜有個名叫孔子的人,學問高深,設壇授徒。從此,魯國、孔子就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
三
遵父輩的遺命,燕伋22歲那年初春,義無反顧的踏上了赴魯求學的征程。
走的那天,在妻兒和同族人的目送下,燕伋背起妻子準備妥當的衣服、鞋子和口糧的包裹,踏出了家門。
在村口,妻子望著丈夫孤獨的腳步、孤單的背影越走越遠,風刮起黃塵來,不一會,什么也看不見了。妻子摟緊了懷中的孩子,眼淚無聲地流了下來。我一直在想,這淚水為后來燕伋設壇授教這顆“種子”的發芽,澆下了第一滴水。
走在西風中的燕伋,緊了緊青袍,狠狠心沒有回頭,擔心一回頭,妻子的淚水會濕綻開他繃緊前行的心。
古道上,青衫飄飄,千里奔赴,只為一個道聽途說從未謀面的人。
一路向東,經雍城(鳳翔)、西岐(岐山)、鎬京(咸陽)、下邽(渭南)、潼關、函谷關(靈寶)、洛邑(洛陽)、蘭封(蘭考)、陶邑(定陶),最后到達曲阜杏壇。近四千里的長路,燕伋步行了快兩個月。
從陜西千陽到山東曲阜,在今天的交通條件下,直線距離也很遙遠,而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時期,沒有向導、沒有路標、沒有地圖,要東渡黃河,還可能面臨風雨、討食、走錯路等等想象不到的苦難,這實在是一條漫漫的坎坷路途。
燕伋到達魯國,師從孔子5年后返回家鄉。長途跋涉去一次就夠讓人震撼了,讓人震驚不已的是在他35歲時二次赴魯,更不可思議的是58歲時已步入老年的他第三次又赴魯了。
究竟是什么神奇的力量給了他這么大的勇氣和決心?
探究其原因,第一次赴魯是他從小就胸懷大志,意志堅定,為了追求知識再苦再難也在所不辭,還有一點應是兌現父輩的遺命;二次赴魯是他在秦國報國無門,郁悶至極,急需有人解惑,卻找不到一位能像孔子一樣隨口說出的話,撿拾起來都是金玉良言的老師來;三次赴魯是他聽到孔子的兒子孔鯉去世的噩耗后,想到老師白發人送黑發人,接連沒了師母和兒子的老師一定很悲苦,作為學生一定要去陪伴孤單的恩師。

燕伋文化景區


漁陽塾壇(上圖)與中華尊師第一臺(下圖)
四
據傳說,燕伋第一次從魯國歸來,在岳父的舉薦下,秦哀公敕封他一個相當于現在公安專管戶籍的職位,但在這個位上他只做了幾年就辭職了。
燕伋辭官的原因是看不慣官場的行徑。從小就學文識字的燕伋,特別是師從孔子5年的學習,從政時往往容易表現出理想化、情感化的傾向,缺少周旋能力,難于適應官場環境,這應該是他辭官后一生不再涉入仕途的真正原因。
燕伋第二次從魯國歸來后,計劃在家鄉燕家山創辦塾壇,族人認為他兩次赴魯師從孔子10年,精通六藝、學富五車了,該入仕,不該授徒。在一致反對聲中,一心想讓更多的人讀書、識字、睜眼、明理的燕伋,最終把塾壇選在了漁陽塬邊,舉家遷此。
經過多日的籌備,由一個老師、三口窯洞、五張蘆席、十五個學生組成了最簡陋的塾壇。
燕伋選擇第一次赴魯拜師這一天作為開學日,在學生和村民的注目下,懸掛起了他書寫的“漁陽塾壇”木匾。這一掛,居然牢牢的掛進了歷史中,使后世的人掂出了這四字的千斤重量。
燕伋授徒不只繼承了孔子的教育方法和教學內容,并根據實際進行了創新和增補,除教“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外,把“農藝”等也納入了教學內容。他還更加注重學辯結合、動靜結合、講練結合的方法,使得教學效果十分良好。
讀書聲越傳越遠,影響越來越廣,學生越來越多,后遍及今陜、甘、川、寧等地,為這些地方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官場生涯,沒有成就燕伋“學而優則仕”的初衷,漁陽設教18年,成就了他“學而優則師”影響千古的一生。
從這幾口不太顯眼的窯洞處,西秦大地平民文化教育由此開始邁步上路,燕伋開創了先河。
五
相傳,漁陽塾壇授徒幾年后的一個仲秋,一批學生就要出師,在告別老師的聚會中,聽到一學生彈奏演唱的《別漁陽》,讓燕伋思緒萬千,勾起了他對老師孔子的深深思念。
人常說,情到至極處,便是有法時。燕伋腦光一閃,何不筑一土臺,登高望魯,寄托相思?
送走了出師的學生,燕伋上到窯洞崖背上,這兒是一塊臺塬,眼界開闊,他覺得這兒就是理想的筑臺地址。
第二天早上,燕伋用千河岸邊撿拾來的小石頭勾劃出了筑臺的范圍,用衣襟兜黃土從崖下運之塬上,他東望魯國,行叩拜大禮后,倒下了第一襟心土。
燕伋運黃土上塬筑臺,不用籮筐等工具,更拒絕了家人和學生相助的請求,堅持衣襟兜土,堅持一人筑臺,每天早晚各一次,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土臺越筑越高,年歲越來越大,步履越蹬越慢,喘氣越走越粗。
以這種特殊的方式筑臺,燕伋持續了整整十多年,足可見其心之誠,其志之堅。
據說筑臺高度原計劃三丈六尺五,代表一年365天,天天對恩師的思念。高度就差一點了,燕伋因急著三赴魯國,筑臺從此中斷,但豐碑就此矗立。
從有筑臺望魯的想法起,燕伋當然清楚,即便晴空萬里,放眼遠眺,也不過十多里遠。但在他心中,筑臺只是表象,深意是要將信仰轉化為有形的行動,即慰己心,又示后人,讓弟子們明白,尊師重道乃治學的基石,處世的前提。
兩千五百年前一個人舉行的尊師奠基式,一個人壘起的尊師高臺,沒有任何想要成為標桿的企圖,卻為后人豎起了尊師的最高標桿。
六
燕伋第三次去魯國服侍孔子4年,孔子去世后又為其守孝3年,西歸時已65歲。
太陽總要西下,漸漸地,燕伋那跋涉千里的步履已顯蹣跚,高大的軀體一天比一天疲憊,疾病也接踵而來。
燕伋背著“尊師重教”這四字走的太久了,走累了,終于走不動了。歸來后第二年初春的一個黃昏,他倒下了,但就在這一刻,卻為后世高高的托舉起了一座千年的土筑臺,一塊千年的木匾。
鑒于燕伋一生在傳承儒家學說、弘揚民族文化等方面作出的豐功偉績,辭世后,歷代朝廷對其大加封贈:唐玄宗封漁陽伯;宋真宗加封千源侯;明追稱先賢燕子。
今天去看望魯臺,不是為了看兩千五百年多前的黃土臺,而是為了觸摸跳動了兩千五百多年尊師重教的脈搏。
一撥又一撥祭拜過望魯臺的人,我相信,會不約而同的拾起擱在此處“尊師重教”的四字精神糧袋,扛到自己背上,向遠方的路走去……
千陽縣農業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