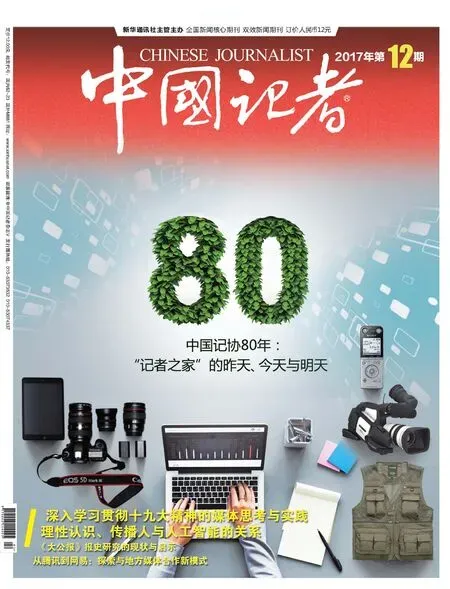“一帶一路”全球傳播構建新話語體系探析
□ 文/文智賢 毛 偉
一、全球話語體系與文明等級的思辨
近年來,“話語”已經成為一個跨學科的學術概念,話語體系則可被視為思想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的外在表現形式,承載著話語所蘊含的文化傳統、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等。話語體系的研究已經超越了學術范疇,成為國家戰略層面的重要考量,它代表著一種文明的延續、文化的傳承,在當今社會被視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掌握全球話語權的基礎。全球“話語體系”競爭主要表現在話語體系所構建的學術話語、新聞話語、藝術話語、民間話語等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方面。影響力越大、感召力越強則意味著擁有更強的國際話語權,也意味著在全球發展格局中的優勢地位。[1]
在全球話語體系中,西方長期占據絕對優勢,這賦予了西方主流媒體強大的全球新聞話語權,通過精心設置議程議題,甚至不惜用“假新聞”的手段,在國際輿論場臆造了“伊斯蘭恐怖論”“中國威脅論”等議題。西方媒體報道的偏見往往歸結于多種因素,如意識形態差異、政治正確導向、國家利益驅動等。但如果放在一個更長遠的歷史環境中去考察,沿著西方文明等級論傳播和全球話語實踐的發展沿革,可能會發現一些更深層次的原因,來解釋國外社會精英和普通民眾對中國的認知和態度變化、解釋中國人對于自己的認知變化,也為“一帶一路”全球傳播提供新的學術視角考量。
長期以來,西方話語體系中形成了一個看不見、摸不著卻又無所不在的思想理念——文明等級論[2]。“文明”一詞是從英文“civilization”翻譯過來的,而“civilization”這個單詞是18世紀中期才提出的,特指西方國家的自我意識,試圖用“文明”來代表西方社會的發展成就。“文明”不是作為一個孤立的詞匯存在的,在其背后隱含的是對“非西方”和“野蠻”的認定,[3]以后更形成一套含有由低到高的排列標準的話語體系,經典的西方文明等級論將世界各地人群分別歸為“野蠻的(savage)”“蒙昧/不開化的(barbarian)”“半開化的(halfcivilized)”“文明/服化的(civilized)”及“明達的(enlightened)”五個等級,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變化,這個文明的等級劃分趨向穩定,19世紀初,已經成為國際法、國際條約簽訂乃至成為西方認識世界的基礎。
西方文明等級論在全球的“隱形”建立是一個過程,18世紀以前,歐洲人能將中國文明與歐洲文明等量齊觀,中國人被認為是“白人”[4],但歷史的進程推動了西方人認知中文明等級的落差,到18世紀后,西方種族主義對中國人的偏見在話語實踐中不斷強化,中國被視為“半開化”國家,中國人的皮膚由“白”變成了黃[5],如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來中國,就將所謂“支那人”(英文Chinese本義)稱為“barbarians”。在西方人的思想意識中,中國、日本、奧斯曼帝國等亞洲國家被視為“半開化”國家,漢語、阿拉伯語等都被視為一種“半文明”語言[6]。“西學東漸”使得中國維新人士逐步接受了西方的“文明等級論”,將自己視為“半開化”或“半文明”,并將這種意識貫徹于各個領域的話語實踐,將加入“文明”行列作為自己國家的發展目標。文明等級論成為一種政治無意識,不僅早已被西方人所內化,而且已經滲透進他國家的話語實踐中,中國的文化不自信、道路不自信乃至對“一帶一路”話語實踐不自信都能找到“文明等級論”思維的影子。
中華民族早已有一套傳統的話語體系,但近現代被外部壓力和自身動力的作用下被政治無意識的文明等級論所解構,形成了向西方話語及話語體系學習、轉變的趨勢。這也解釋了為什么西方能一家獨大控制著全球輿論場的話語權,在西方構建的世界話語體系中,其他國家文化傳統形成的話語體系都“半開化”“半文明”,在向西方話語體系模仿學習的過程中,又被西方文化霸權主義不斷打壓或者被西方實際控制,進入了模仿和被打壓的發展死循環。
二、“一帶一路”全球傳播的話語困境
“一帶一路”倡議是全球戰略思維,將會深刻改變現有的一些不合理、不適應時代發展潮流的舊秩序,改變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將構建更加多元包容的新的世界秩序。“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近四年來,國際輿論場一直存在不同的聲音而我國又長期處于話語劣勢,如果輿論場中的擔憂和質疑得不到積極回應,則會成為傳播盲點,盲點愈積愈多則會形成傳播屏障,誤導受眾。必須厘清當前“一帶一路”這一話語的傳播輿論困境,才有可能優化改良,抑或開拓新的話語空間和新的傳播路徑。筆者對全球主流媒體及社交媒體的“一帶一路”報道進行調研發現,在“一帶一路”全球熱議的表象下,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話語困境:
一是海外主流媒體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存在局限性。這種局限性集中體現為對“一帶一路”報道主題的單一上。海外關注點普遍集中于“一帶一路”所帶來的短期經濟和政治影響,較少從長遠角度闡述對人類發展、文化交流、文明融合所帶來的機遇和對世界格局的影響,“一帶一路”倡導的“五通三同”內涵幾乎沒有出現在海外媒體報道中,即使是持積極態度的伊斯蘭主流媒體也更多將“一帶一路”簡化描述成一個中國主導的投資計劃或者本國與中國雙邊合作的計劃,一些強勢西方媒體則是從自身的話語體系出發對“一帶一路”進行模糊化、污名化的報道解讀。
二是國內外“一帶一路”報道態度復雜化。從表面上看,國內主流媒體的“一帶一路”報道不僅數量龐大,而且全部都在進行正面解讀,但報道形式單一,很多報道內容浮于表面,官話套話等程式化報道居多,完成政治任務的正面宣傳意味濃厚。伊斯蘭主流媒體的“一帶一路”報道大多都屬于正面解讀,但在一些具體項目實施等微觀層面的報道中表現出消極和擔憂態度;這也凸顯出由經濟利益驅動形成的正面解讀更多是一種暫時性的、協議式的認識。西方主流媒體的“一帶一路”報道有自己的議程和話語體系,態度既有相對中立的解讀,也有對未來國際秩序變革的徘徊觀望和消極隱憂。
三是國內外“一帶一路”輿論場與現實脫節。這種脫節表現在新聞輿論與民間認知的脫節和新聞輿論與學術研究脫節兩方面。筆者在實地調研采訪時發現,各國民眾對于“一帶一路”的認知其實極為有限,尤其西方國家民眾對于“the Belt and Road”“One Be One Road”等概念較為陌生;一些伊斯蘭國家民眾不熟悉“One Belt On Road”的表達方式,但卻知道美國媒體創造的具有二元對立內涵的概念“China’s Silk Road”;新聞輿論與學術研究的脫節集中體現為國內外媒體在“一帶一路”報道時選擇學者信源時的隨機性、以及普遍忽視“一帶一路”的研究動態等。
四是對伊斯蘭報道受到西方認知框架誤導。薩義德用“Covering Islam”的語義雙關“報道”與“遮蔽”之義暗諷西方主流媒體對于伊斯蘭報道的偏見,而長期以來,國內輿論深受西方影響,缺少自己的議程議題,時常陷入“恐怖主義”話題陷阱,由于缺乏真正權威的解讀,公眾對于伊斯蘭形象的認知也趨于極端化。“一帶一路”戰略涉及眾多伊斯蘭國家和國內外穆斯林人民群眾,而國內的穆斯林同胞大多居住生活在通向絲綢之路的重要邊疆地區,伊斯蘭報道關涉的不僅是“一帶一路”,更影響著民族安定團結,但對于伊斯蘭認識的輿論爭議有擴大化的趨勢。
三、“一帶一路”話語體系與文明融合
參照國學大師季羨林“文化體系”的概念[7],世界文化共有四個文化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波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歐洲文化體系,其中有三個都屬于東方,這四個文化體系對應形成了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中帶有強烈文明等級色彩地將伊斯蘭文明視為威脅,甚至擔心伊斯蘭文明與中國的儒家文明(中華文明)聯合抗衡西方文明。實際上,在西方文明還未出現以前,三個東方文明直接已經由絲綢之路進行了廣泛的交往活動,并形成了一些共同之處,到了近代,歐洲崛起,西方文明給世界帶來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而東方的三大文明都處于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在西方文明等級意識中逐漸被歸為“半開化”或者“半文明”,在這種客觀歷史外部環境下,東方三大文明造就的共同之處就更加突出和強烈了。
從文化地理學角度看,“一帶一路”連接歐亞大陸,“中華文明”一路向西連接“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與“歐洲文明”。從當前現實層面看,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中,伊斯蘭國家占比最高。而中國和伊斯蘭國家的形象長期遭受掌握全球話語權的西方政府、媒體、智庫的妖魔化、污名化解讀。在西方新聞話語實踐中,伊斯蘭和中國都被視為西方(“文明”)的對立面,“他們-我們”的話語建構實際上也代表著“他們”是“半文明”,“他們”是“不正確”的隱藏邏輯。中國和伊斯蘭的話語體系遭受美國主導的西方話語體系的排斥和邊緣化,西方的話語主導了近代世界對于中國、對于伊斯蘭的認識。不僅在新聞話語層面,在世界秩序的構建和維護上,依然由西方主導。但“一帶一路”倡議與西方主導的國際合作模式完全不同,以開放包容共享的原則推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共同進步。“一帶一路”倡議本身即蘊涵了一種全新的話語體系,這個話語體系提供了一個蘊含中華文明包容精神的創新全球治理、重塑世界秩序的新模式和新思路,將成為人類發展史上的一項重大理論和實踐突破[8]。
當前全球的話語體系與話語權幾乎被美國一家所掌控,但客觀看,美國全球話語霸權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是經過數次戰爭重塑世界格局及近200年的戰略調整才得以建立的。這種帶有侵略性和文化霸權主義色彩的話語體系已經逐漸凸顯出與未來全球經濟社會發展格局不相適應的征兆。“一帶一路”全球傳播需要構建一個人類文明融合的話語體系。從社會發展格局、話語體系現狀以及文明交往歷史看,“一帶一路”所構建的新的話語體系應當以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融合為切入點,在未來,還應該融合印度文明,抓住“一帶一路”戰略機遇期,形成“中華-伊斯蘭-印度”三大東方文明融合的全球新的話語體系,也將為歐洲發展帶來機遇。但從現實層面考量,美國主導的話語體系及西方長期以來的文明等級論的政治無意識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全球傳播屏障,從政治經濟領域到文化教育領域,從宏觀布局到微觀突發事件,無不具備一套完整的話語霸權;此外,西方使用的英語也潛移默化地構建了一個交流屏障。
“一帶一路”的傳播與建設需要一個新的全球話語體系和世界秩序,也只有一個融合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以及印度文明的話語體系才能真正推動“一帶一路”的全球傳播,重塑世界秩序。中國文化的核心是和諧包容,中正平和,不走極端,不搞民族斗爭和宗教戰爭,是能夠團結“一帶一路”沿線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文化[9],這也是東方三大古老文明對話與融合的基礎。“一帶一路”全球傳播所構建的新的話語體系將形成一個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識形態支撐,即政治和文化上的多極化,尊重歷史和傳統,形成一個文化共同體和文明共同體。(作者文智賢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毛偉是新華社新聞研究所編輯)
【注釋】
[1] 楊鮮蘭. 構建當代中國話語體系的難點與對策[J]. 馬克思主義研究. 2015(2):59-65.
[2] 劉禾.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 劉禾.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1-14.
[3] 郭雙林. 從近代編譯看西學東漸——一項以地理教科書為中心的考察. // 劉禾.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235-290.
[4] 梁展. 2016. 文明、理性與種族改良:一個大同世界的構想.// 劉禾. 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101-162.
[5] Walter Deme. Wie die Chinesen gelb wurden: Ein Beitrag zur Frühgeschichte der Rassentheorien[J].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992, 255(3):625-666.
[6] 程巍. 2016. 語言等級與清末民初的“漢字革命”.//劉禾. 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M].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101-162.
[7] 季羨林. 論東方文學——《簡明東方文學史》緒論[J]. 國外文學. 1986(4):6-27.
[8] 劉再起, 王曼莉. “一帶一路”戰略與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研究——以話語權和話語體系為視角[J]. 學習與實踐.2016(4):68-74.
[9] 李希光.建設“一帶一路”文明圈(下)[J]. 經濟導刊.2016(2):8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