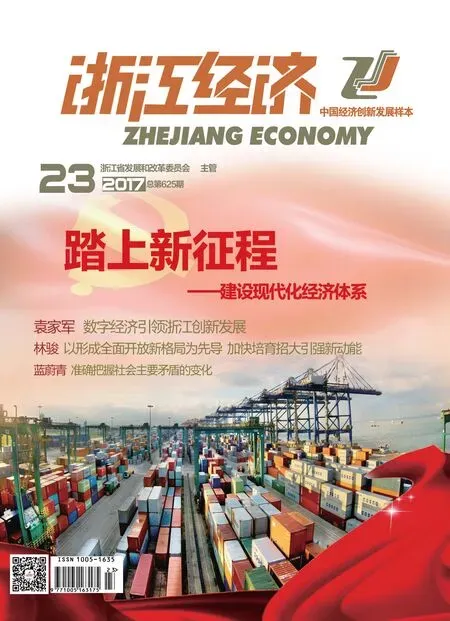中國經濟為什么不會硬著陸
卓勇良
中國經濟為什么不會硬著陸
卓勇良
只要草根經濟活力尚未充分發揮,只要這種活力與約束尚未均衡,只要一如既往地踐行“放”的價值取向,中國經濟仍將有較大空間
中國改革開放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被一些學者說得云里霧里,令人不得要領。以筆者看來,“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就一個“放”字。“放”字的字面意義是去掉加之于人民群眾身上的束縛。市場化雖是“放”的一個結果,但并不能完全涵蓋這個“放”字。這里透著一絲無奈,一種回歸;意味著計劃經濟的終結,更意味著對一個大寫的“人”的應有尊重的開端,顯示著這個古老國家長期被桎梏的人文精神的復興。這個“放”字的思辨依據也很簡單。因為我們任何人的任何行為都應該有思辨依據,“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這個“放”字的思辨依據就是若干不言自明的社會倫理。
根據讀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心得體會,人類社會的知識根據其與經驗的關系,大致可分為三種:一種是源于經驗,需要將綜合分析上升為理論的知識,諸如社會科學知識等;另一種是不一定源于經驗,但需要大量分析推論的知識,且能夠被實踐所證明,如愛因斯坦相對論等;再一種是不需經驗、不言自明、不需實踐證明的知識,如兩點形成一條直線,1+1=2等。康德認為,勾股定理無法以實踐證明,因為不可能窮盡所有的直角三角形。
至于一些最基本的社會倫理習俗,大概也可以歸并為這類不言自明的知識。譬如不能隨意侵犯別人的身體和財產等。所以,每當聽到腐敗官員說自己不懂法、缺少學習時,就覺得特別可笑。
改革開放初期,浙江農村的一些干部群眾就是根據不言自明的社會倫理,即人民的政府必須能讓人民吃上飯、吃好飯等,放手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并由此引發了經濟基礎的根本性變革。
此時也出現了兩種不同倫理規范的碰撞。按一般要求,黨政官員必須在黨和政府確定的政策路線框架內思考問題,規范行動;必須嚴格遵守執行黨和政府的各項政策。這是作為黨和政府任命的官員,必須遵守的政治紀律和政治倫理。按當時的認識和政策,不允許個體經商開作坊,雇工8人以上即為剝削等。
然而,滿足人民群眾基本生存訴求的社會倫理,促使一大批干部只能站在人民群眾一邊。黨和政府的領導干部執行大政方針,雖然“上”必須對黨中央和任命機關負責,然而“下”也必須對生你養你、天天直接面對的人民群眾負責,這顯然也是一個不言自明的社會倫理。
“如無必要,勿增實體”的奧卡姆剃刀,在這里又一次產生了作用。個別的、分散的、缺少有意識合作的社會個體,當他們僅僅是實施一種以自我維生為目標的經濟行為時,自然而然、順理成章地采取直接占有生產資料、自主生產經營的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這也是民間不言自明的一種行為準則,農民根本不需要以經院式的學術研究來確定生產關系。
自然而然是民間經濟近40年來發展的最大特點。因為至少就浙江言,民間經濟發展壯大是人民群眾求生圖變、創業創新的“自然過程”;浙江的制度變遷,是生產力與市場化相融相適,不斷提升的“自然進程”;浙江的市場化主要并非行政推動,是隨著創業進程而推進的“自然演進”。
希望在民間,希望在千千萬萬民間企業家當中。上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政府依靠民間、企業家,形成了快速的工業化、市場化和城市化,如今也必須緊緊依靠他們。或許到了某一天,中國經濟真的將有大問題,但至少現在不會。
本輪經濟回落之所以正在逐漸成為過去式,還因為存在著一個勞動相對價格變化的奧秘。勞動價格下降及其上升,均有利于經濟增長。前者奧秘在于降低成本和強化積累,后者奧秘在于加大內部約束同時也增強外部激勵。
于是,盡管中國經濟硬著陸說法甚囂塵上,中國經濟卻巍然挺立,且在2017年出現了居民收入和企業利潤雙雙回升的較好景象。這也正是《中國經濟為什么不會硬著陸》①《中國經濟為什么不會硬著陸》卓勇良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的一個主要分析視角。
只要草根經濟活力尚未充分發揮,只要這種活力與約束尚未均衡,只要一如既往地踐行“放”的價值取向,中國經濟仍將有較大空間。當下關鍵是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增強民間信心,增強對于若干最基本的不言自明社會倫理的敬畏。積極促進經濟保持平穩健康增長,迎來持續的消費景氣,創造中國人民更大的福祉。

浙江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浙江省信息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首席專家、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