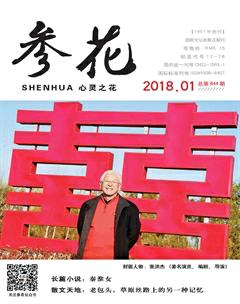老包頭,草原絲路上的另一種記憶
孫桂芳
1
幾次去內蒙,都沒有去包頭。提起包頭,不由自主就想到了鋼花,想到了烏云一般滾滾的濃煙,也就沒有了前往的興致。包頭的朋友說:“來包頭吧!北魏六鎮之首的懷朔鎮故城,希拉穆仁圐圙古城,麻池古城,都在我們包頭。據說,最近有考古發現,六鎮之一的武川鎮,也在包頭。”
草原古絲綢之路重鎮武川,正是我此行的目標。我所了解的武川,位于內蒙古自治區中部,陰山北麓,呼和浩特市北。新的發現,不管是否經過考證,都引起了我前往一探究竟的興致。我放棄了呼和浩特市北的武川,踏上包頭之路,尋找武川。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包頭,這座塞外鋼城,那么干凈。街道寬敞,沒有擁堵。不堵車的城市已成為稀罕之物,城中草原,城中湖泊,茂密的林木,更是把包頭與其他的城市區別開來,給我帶來了一種全新的體驗。
我喜歡這樣充滿勃勃的自然生機,它讓城市變得更加闊大,人文與自然的交融,給視覺上帶來一種無限延伸的可能。
“從晉陜冀走西口的,目標就是素有水旱碼頭之稱的包頭,也就是從這里進入包頭的。”
陪我同行的包頭朋友,指著眼前浩闊的水面說。此時,我們已穿過城中草原,穿過城中大片的樹林,來到了南海子濕地。
我有片刻的微怔,沒料到我正漫步而行的這個城市,正是當年走西口人進入口外之地。而我眼前這片浩闊的海子,正是當年走西口進入包頭的水碼頭。
南海子(蒙古族認為所有的湖泊都是海的兒子,均將湖泊稱為海子)位于內蒙古包頭東河區,南以黃河北岸為界,與鄂爾多斯隔河相望。昔日,南海子曾是九曲黃河的一段故道,河水改道南移后形成了我眼前的水面和灘頭草地。
南海子很大,環水而行,需費多半天的功夫。環水而行時,我心里忽然有一些感動,我知道自己正踏著中華文明的起源——黃河的浪濤而行。而黃河流經之地,不僅有許多蘊藏著文明的古跡可尋,同樣也有著民族交融的文化可循。
眺望著煙波浩渺的水面,遙想當年,那些挑擔謀生的,船筏裝卸的,做皮毛生意的,千里迢迢聚集到這里,有的就近駐扎下來,也就是現今兒的包頭東河區;有的再從這里向歸綏、喀爾喀、庫倫、多倫、烏里雅蘇臺和科布多,以及蒙古恰克圖、俄羅斯等地繼續前行。
“商胡販客,日款塞下”“驅牛馬萬余頭,來與漢賈客交易”。短短幾十個字,不僅盡述了昔日包頭的繁榮,更讓我從中領略了走西口,通過人類的遷徙,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交匯融合。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實難留,手拉著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門口……”
一曲走西口,唱出了當年走西口人多少的蒼涼、多少的辛酸、多少的無奈……
2
“山西走西口的,當年大都住在這東河區。東河區,也就是老人們常提起的老包頭。”包頭的朋友帶著我,從東河區的大街再穿過小巷,尋找當年走西口的痕跡。
包頭,蒙古語包克圖,意思是有鹿的地方。因此,包頭也被稱作“草原鹿城”。也有傳說,包頭是因一條河而得名,這條河叫“博托河”,意為包頭。博托河與黃河的交界就在南海子。
南臨黃河,素有“水旱碼頭”“塞外通衙”之稱的包頭,位于內蒙古高原的南端,陰山橫貫城市中部,形成了北部高原、中部山地、南部平原三個地形區域。
或者,正是這獨特的地理位置,才有了當年人類的大遷徙。人類的遷徙,打通了中原腹地與蒙古草原的通道,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如水乳得以交融,使得包頭這座塞外老城充滿了活力。
如果說新鮮的元素能夠打破固有的格局,那我又何必非要追尋走西口人的腳步呢?!
一定要追溯歷史,其實,從秦漢到清末,橫跨包頭的陰山古道,早已歷經了兩千多年的風雨浸淫。
陰山綿亙千里,秦直道、陽道(北魏稱中道)、白道、居延道(參天可汗道)、豐州道、駝道,幾條古道縱橫交錯。
為了北拒匈奴,秦始皇令蒙恬率大軍屯于河南地(今伊克昭盟),在陰山修筑長城,將秦、越、燕長城連成一體。同時修筑秦直道——南起陜西淳化,北至包頭麻池。有民謠這樣唱道:“條條道路通直道,郡郡縣縣送糧草。”
據史料記載,秦始皇第五次出巡死于沙丘(今河北邢臺),丞相李斯和中書令趙高,將秦始皇尸體從秦直道運回咸陽。
秦直道上也曾留下司馬遷的足跡:“吾適北邊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筑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史記·蒙恬列傳》卷88)。
3
我沒有走秦直道尋古。我沒有走并入草原絲綢之路的駝道,尋找遺落在駝道旁草叢里的聲聲駝鈴。我沒有走曾經走過的白道、居延道、豐州道。我只想去達茂旗希拉穆仁圐圙古城,考古新發現,那里有可能是古武川鎮的鎮址所在。
我從昆都侖河山口進入陰山,去往固陽。這條道稱為陽道,即中道。臨時改去固陽,是因被告知達茂旗希拉穆仁圐圙古城正在修復。陪我同行的包頭朋友說,那就去固陽吧!北魏六鎮之首的懷朔鎮故城遺址就在固陽。固陽的朋友對懷朔鎮的歷史可謂了解得很詳盡。
車沿著蜿蜒的陰山山脈,向大山縱深處行駛時,我想起了唐楊凌的《明妃曲》:“漢國明妃去不還,馬馱弦管向陰山。匣中縱有菱花鏡,羞向單于照舊顏。”
想起這首《明妃曲》,望著窗外一閃而過的層巒疊嶂,我不禁有些傷感:為了那馬馱弦管,為了那一去不還,為了那羞于拿出的菱花鏡,為了那深宮中的柔弱女子,竟能擔肩國家大義,遠嫁他鄉……
4
誰說女子不如男?
行走于漫漫陽道的不僅僅明妃一人,替父從軍的花木蘭,正是在這陽道上打馬飛馳。
“旦辭黃河邊,暮至黑山頭”,站在懷朔鎮故城遺址(黑山頭)重讀少年時讀過的《木蘭辭》,心中涌起一股打馬放歌的豪邁之情。
懷朔鎮故城遺址位于一望無際的大漠之上。放眼望去,既沒有我所渴望看到的遍野的牛羊,更不再是花木蘭從軍時“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的烽火場。蕎麥、攸麥、小麥,鋪展在遼闊的大漠之上,幾種麥子花兒如錦緞一般,交相輝映。而在五彩的麥田中,一條藍色的河流蜿蜒而過。
這條藍色的河流叫五金河,依傍懷朔鎮故城北西墻,由北向南流淌而過。五金河的兩條支流,又分別穿越故城的北墻與東墻入城,于城址西區偏南位置匯合后,流出城外,注入五金河。
擇水草而居——眺望著遠去的河流,我恍惚看到了人類一代一代,沿著河流從古走到今天的旅痕。
越水而過,懷朔鎮故城遺址被一條河道分為東西兩個區。在東區和南門外,伴我們一行的固陽朋友講述了此地考古的發現,有陶器、鐵劍、銅佛像等。沿著東區和南門,我們來到地勢較高的西區。雖然已過千年,但草叢之中,仍可看到殘留的瓦礫和建筑物基址。而在西區靠南的一處建筑廢墟,固陽的朋友說,就是在這里,考古發現了一座佛教殿堂遺址,出土了一批與佛教有關的小型泥塑像。
懷朔鎮是迄今發現的北魏古城遺址中規模較大的。據專家考證,懷朔鎮始建于北魏始光年間,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歷史。公元四世紀末,拓跋鮮卑族建立北魏政權。與此同時,一個強大的部落汗國——柔然,在蒙古高原崛起。為了防備來自北方草原上的柔然南下,北魏大規模修筑長城,又在長城一線,沿陰山以北設置邊防六鎮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作為長城防線的支撐點和戰略依托,形成了一條點面結合的堅固防線。六鎮之中,懷朔鎮是河套及陰山一帶的政治中心和軍事要塞。
從建立到廢棄,懷朔鎮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風雨,見證了北魏王朝的興衰。而與故城見證北魏興衰的,還有北齊神武帝高歡與北齊文宣帝高洋父子。
北齊神武帝高歡,其祖高謐曾為北魏侍御史,后因犯法舉家徙于懷朔,此后三代遂世居于此。天寶元年,高歡之子高洋逼東魏孝靜帝讓位,建立北齊王朝,高歡被謚為神武皇帝,廟號高祖。
5
將要離開懷朔鎮故城時,正是晌午時分。夏日的陽光一覽無遺地灑在頹壁殘垣間,大朵大朵的白云如羊群,在碧藍如洗的天空上慢慢地蠕動著。空曠的原野,讓我有一種躍馬奔馳的沖動。
然而,當風從原野上吹過時,我卻似恍惚地聽到了一支悲咽的琴曲:云山萬重兮歸路遐,疾風千里兮揚塵沙。雁飛高兮邈難尋,空斷腸兮思愔愔。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是……
我仰頭望望天,再望望遼闊的原野,《胡笳十八拍》這聽了無數次的千古悲音,在作曲人蔡文姬被匈奴擄去走過的陽道上,我終于覓到了曲中的真音。那真音并非只有對個人際遇所感到的悲愴,更是對民族、對歷史、對歲月的一種深情的傾訴。
“雁南征兮欲寄邊心,雁北歸兮為得漢音。雁飛高兮邈難尋,空斷腸兮思愔愔。”
伴著傾灑而下的大雨,伴著一縷千古琴音,我離開了包頭。我知道自己此行包頭只是一個開端,我還會再來,來尋找鐫刻在草原絲路上的另一種記憶!
(責任編輯 象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