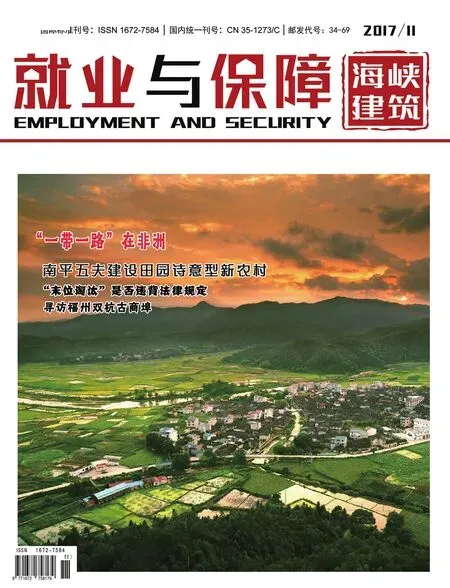蘇州博物館的“硬氣”
辰夜集
蘇州博物館的“硬氣”
辰夜集
國人在貝聿銘先生設(shè)計的蘇州博物館上投入很多博物館之外的情感,包括我自己。某種意義上,它最接近貝聿銘的建筑理想。這是一個正確的建筑。木心去世之前,貝聿銘的學生去到烏鎮(zhèn),商議如何設(shè)計他的美術(shù)館。木心笑談:“貝先生一生的各個階段,都是對的;我一生的各個階段,全是錯的。”有時候,正確并不比錯誤更可愛。
擅長設(shè)計公共建筑的貝聿銘,尤其偏愛博物館與美術(shù)館的項目。他曾說:“博物館一直都是我的主題,不停地提醒著我:藝術(shù)、歷史和建筑確實是合為一體、密不可分的。”回顧他過往知名的博物館設(shè)計作品,我們或許能夠體會到貝聿銘建筑設(shè)計中的強大生命力。
貝聿銘長達六十載的職業(yè)生涯與20世紀中到晚期建筑史的多個關(guān)鍵時期緊密相連。這位世人所稱的“現(xiàn)代主義最后的大師”,以幾何為紙,以光影為筆,游走于東西之間,與社會、文化、地緣等互為關(guān)系。如今,他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從法國到卡塔爾,從中國到美國,散落亞歐。而蘇州博物館是他最后一部作品。
1998年,來自蘇州的一個消息震驚了建筑界:古城蘇州要在三個古典園林——拙政園、獅子林和忠王府旁邊,修建一座現(xiàn)代化的博物館。經(jīng)過長達三年的選擇與論證,來自美國的著名建筑師貝聿銘最終成為這座博物館的設(shè)計者。新館的選址曾引發(fā)過巨大的爭議。那是當年事,多提無益,還是看看現(xiàn)在。
“蘇州博物館,我認為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這個項目,是我一生中值得紀念的一筆。我對中國的記憶少之甚少。你們知道,我很小的時候便離開了中國,所以我對中國一直抱有懷念之情。設(shè)計這座博物館,給了我一個機會,讓我能夠?qū)⑽覍χ袊挠洃洠脤嶓w表達出來。”

光影
在蘇州的各種宣傳資料中,蘇州博物館無疑處于耀眼的位置,不容置疑。蘇州博物館宣傳頁上“中而新,蘇而新”的設(shè)計理念被反復(fù)提及。這個“新”字,在這種語境下顯得跳脫,承載了太多的鄉(xiāng)愁國夢。貝聿銘先生并不是中國建筑師,蘇州博物館也不是現(xiàn)代化的中式園林,這是一個典型的、成熟的、“正確”的作品,并不“新”。
“我努力將這些記憶融入這座建筑之中。所以,我希望我所設(shè)計的建筑,充滿著蘇州特色。設(shè)計蘇州博物館,對我來說是一次令人激動的旅程。雖然困難重重,但我仍有強烈的興趣,來面對這些挑戰(zhàn)。回想起來,這座建筑可以算作我對家鄉(xiāng)的饋贈。”貝先生用政治正確與學術(shù)正確完成了任務(wù)。
記憶是片段的、個人的、有選擇的。允許新建筑中容納傳統(tǒng)并不是傳承,而是滿足民眾感性的需要,繼續(xù)增強記憶的價值。貝先生自認他在建筑上的成就基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素養(yǎng)之上,但他承認自己是西方建筑師。
每次參觀完蘇州博物館,都會轉(zhuǎn)身進忠王府。當年李鴻章攻進忠王府所見之“玉宇瓊樓”早已不復(fù)存在。李秀成半身塑像,“太平天國”四個大字,分立影壁前后,猶如斷簡殘篇。只嘆蘇州立都太早,曾經(jīng)的吳國宮殿自是留不下,唯一的王府,雖是農(nóng)民起義,也仍然全貌難存。至于拆舊而新建的蘇州博物館,是不是有如宣傳的那樣,完美契合了吳地原有城市肌理,也契合了緊鄰的拙政園和忠王府,還是值得商榷、見仁見智的一件事。
貝先生確實厲害,敢作敢當,在這種選址位置也“硬上”現(xiàn)代主義,螺螄殼里做道場,基本上是香山飯店的發(fā)展,走得現(xiàn)代建筑本地化的路子,明確而堅定,堪稱教科書式的構(gòu)思思路。他的很多建筑都有中國元素,但一定要把蘇州博物館和蘇州建筑綁定就牽強了。蘇州博物館的形式符號都是貝先生多年玩剩下的,并沒有太多創(chuàng)新,只不過中國風在中國會顯得和環(huán)境心理協(xié)調(diào)一些。
一座建筑,要想動筆,就要先找到它的語言、它的腔調(diào),一種控制其內(nèi)部所有事物的氛圍。蘇州博物館幾何造型,片狀山石,鋼結(jié)構(gòu),都不是傳統(tǒng)語匯,它依然保留了江南園林的符號,深灰色的花崗巖作為屋面和墻體的邊飾,與白墻相映,雅潔清新,錯落有致。然而從建筑工藝上,這些石板看起來像是傳統(tǒng)建筑上的灰瓦,但是是以干掛石材的方式安裝,沒有任何類似屋面瓦的防水效果。真正起到屋面效果的,是下面的金屬屋面板。此舉被很多人批評有形式主義之嫌,有違現(xiàn)代主義的一貫立場。
貝聿銘非常善于純粹幾何造型的運用,尤其在20世紀后20年里的幾次以金字塔型為原型的設(shè)計作品最為成功,比如巴黎盧浮宮擴建、克利夫蘭搖滾音樂名人堂,以及香港中國銀行大廈等。在晚年,也可以說進入21世紀之后,他的作品風格越發(fā)突出、造型趨向復(fù)雜,比較偏愛用正方形的平面扭轉(zhuǎn)加八邊形相疊的組合。

幾何構(gòu)造
如果說密斯、柯布西耶在提煉幾何性上做出了成績的話,那么貝聿銘則在繼承現(xiàn)代主義建筑師的基礎(chǔ)上豐富了幾何構(gòu)成,從而為流于僵化的現(xiàn)代主義建筑開拓了新的道路。貝聿銘以他豐富多彩的建筑作品,向人們表明:現(xiàn)代主義仍是有活力的,它決不是一種機械主義,而是同樣可以呈現(xiàn)多姿多彩的藝術(shù)形象。由于這個原型形象鮮明而典型,并曾被貝聿銘多次使用,好像轉(zhuǎn)動一個三乘三的魔方,蘇州博物館也似這個魔方轉(zhuǎn)出來,然后又折疊,由于過硬的線條,與陳從周所說蘇式園林的“糯”相去甚遠。
進門即是前庭,滿目還是一個“簡”,粉墻圍合出來的一個敞庭,中軸通道鋪的是青石板,不走人的地方鋪的就是碎石,一棵樹、一根草也沒有。前庭除了拍照之外,游客顯然是無需停留的。不過我喜歡這樣。
留連在蘇州博物館里,感受到極簡主義在這里得到了的貫徹,比如院墻、建筑外墻、內(nèi)墻一統(tǒng)都是粉白、青石勒腳,所有門套一律青石,人行通道還是青石,內(nèi)外一體,拒絕一切多余的表現(xiàn)。這種“極簡”的設(shè)計處理,使所有的構(gòu)造形式都在視覺中后退,退縮到它們純粹的結(jié)構(gòu)使命中。于是,建筑空間仿佛在退隱,主體建筑內(nèi)沒有一件多余的細節(jié),也沒有任何隱喻“文化”或“歷史”的痕跡,干脆。

片山
即使沒來過蘇州博物館的人,也大都知道新館里有一幅“以壁為紙,以石為繪”、具有米芾山水意境的片石假山。這組假山確實精彩,創(chuàng)意高明而又推敲得當,有其則全園景色皆活。用的是并非傳統(tǒng)而是現(xiàn)代派雕塑的手法——在現(xiàn)今假山疊石大師確實難覓的情況下,若是硬要按“疊、豎、墊、拼、挑、壓、鉤、掛、撐”的傳統(tǒng)手法來做假山,終究不免畫虎類犬。石頭選得也好,是貝聿銘親自從數(shù)以千計的照片中挑選的。拍照片時,還按照貝老的要求,必須在石旁站一人以作比例參照。假山以新館的后圍墻為背景。正如陳從周所言:“江南園林疊山,每以粉墻襯托,宜覺山石緊湊崢嶸,此粉墻畫本也。”“山”水之間,竟無土、無草、無樹、無花,而是以潔白的碎石一鋪了事。
面對像拙政園、獅子林這樣的蘇州園林經(jīng)典,不僅在建筑上超越是一種挑戰(zhàn),而園藝上更是無法超越。貝聿銘認為,傳統(tǒng)園林的假山已經(jīng)做到了極致,后人是無法超越的,為此,他則選擇了另辟蹊徑。以和拙政園相鄰的一面白墻為背景,在前面以石片作為假山,將其喜愛的米芾山水畫加以立體呈現(xiàn),遠遠望去就像連綿不絕的山巒將新館與拙政園相連。

冰裂紋窗
貝先生是個理智的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邊界就是這堵白墻,他超越不了。
有時候,當藝術(shù)家太過于追求一種純粹的形式,可能會“矯枉過正”,導致大家去看他們的作品可能就會覺得平淡。這個時候如果有興趣,不妨看看同時代的其他作品,看看建筑師的理論思想,也許可以讓你轉(zhuǎn)變一些些看法。貝聿銘的設(shè)計理念是時間的建筑。可以說,蘇州博物館是設(shè)計給外國人看的,是設(shè)計給下一代人看的,唯獨不是設(shè)計給當代中國人和蘇州人民看的。
世紀之交,中國成為所謂后現(xiàn)代建筑的試驗場,帝都的大劇院蛋蛋與電視臺大褲衩或是什么其他不可名狀之物,提醒世人這片土地安放了眾多所謂世界著名建筑設(shè)計師心中無處安放的魔鬼。蘇州博物館是正確的作品。
在北京,喜歡去香山飯店;在蘇州,喜歡去蘇州博物館。我個人而言,更喜歡香山飯店的借景,與其內(nèi)部裝飾的趙無極抽象畫。曾經(jīng),貝聿銘作為設(shè)計者對選址有重要影響。對于貝聿銘本人來說,無意創(chuàng)立一種屬于中國本土的建筑風格,香山飯店是一個開端,蘇州博物館則是一個的結(jié)局。他用自己的努力,實現(xiàn)著一個特殊的記憶,為中國留下了一種建筑語言,雖然不新,但是正確。
貝先生終未能在蘇州博物館開館后到里面一個人轉(zhuǎn)轉(zhuǎn),看看自己設(shè)計的光影與空間,坐下喝杯咖啡,端詳熙熙攘攘的人流。而我,一定還會去,去坐下喝杯咖啡,在光影之下,看看博物館中熙熙攘攘的你來我往。
又出蘇州,再別蘇博;十載之間,幾度漫游;若有所思,情隨事遷;碧窗展紙,一抒己見;管窺之論,存商求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