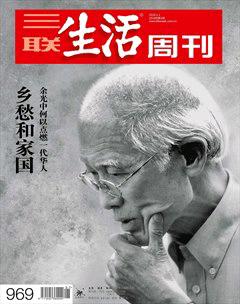我的畫像一張網(wǎng)
“你這是什么,是花布嗎?”
三聯(lián)生活周刊:我還是比較好奇,就是你當初從對郁特里羅那種很具象的臨摹,如何轉(zhuǎn)換到了抽象?你最早看到的抽象作品是什么,給你什么感受?
丁乙:早年國內(nèi)抽象作品有兩個嘗試方向。一是趙無極的路子,水性的流動的狀態(tài)。1983年我專門去杭州看他的個展,他的東西其實比較好懂,和山水、意境都有聯(lián)系。但是對美國抽象繪畫的線條,那時候還是有障礙的。我受到的另一影響是結(jié)構(gòu)性的,是和城市風景有關(guān)的畫面構(gòu)成。這也跟我學過設(shè)計有關(guān)系,設(shè)計的第一課就是平面構(gòu)成。
三聯(lián)生活周刊:但你開始畫抽象后,第一幅《紅黃藍三原色》幾乎就是趙無極的反向,他有中國意境的混沌感性,而你卻徹底理性。
丁乙:1988年那件作品其實有很多思考,不是無緣無故的。我那時候在國畫系讀到了第三年,已經(jīng)感覺到了國畫的局限。而我對西方現(xiàn)代主義也很了解。所謂的現(xiàn)代主義從塞尚開始,到畢加索和馬蒂斯,把塞尚的色彩和結(jié)構(gòu)理論更概括化了。我就想把曾經(jīng)影響我的塞尚理論和學校教的中國傳統(tǒng)都扔掉。當時有一批老藝術(shù)家已經(jīng)在探討抽象,吳冠中發(fā)表了關(guān)于形式美的文章,劉迅也畫有點趙無極路子的潑彩抽象,但他們的畫里還是有意象在。我就想全部去掉,只留下結(jié)構(gòu),像一張網(wǎng)一樣。我當時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三聯(lián)生活周刊:會不會還有一種顧忌,就是你從工藝美校出來的,現(xiàn)在又用平面設(shè)計的方法去繪畫,會不會被人認為,你作為藝術(shù)家卻擺脫不了工藝的語言?
丁乙:對的。但那個時候看到我畫的人也不太多。我每次畫出一批畫,都會拿到工作室樓下有陽光的地方去拍照,鄰居就經(jīng)常會問我:這是什么,是花布嗎?完全把我當成花布設(shè)計師。偶爾有同學老師來看畫,也覺得你是不是走錯路了。那時候繪畫很講究繪畫性。我實際上是很懂技巧的,但正因為如此,我要把它們丟掉。
色彩方面,我也有想法,要讓色彩像本來世界一樣無序,隨手拿到什么顏料就用什么顏料,讓色彩有一種隨機性。基本我很多畫的顏色都是直接打開瓶蓋用,不調(diào)的。我這里一直沒有調(diào)色板。
三聯(lián)生活周刊:西方現(xiàn)當代藝術(shù)有不少專注畫格子的人,對你有多大程度影響?
丁乙:早期對我影響最重要的兩個抽象藝術(shù)家,一個是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現(xiàn)代幾何抽象繪畫的先驅(qū)),就是結(jié)構(gòu);另一個是弗蘭克·斯特拉(Frank Stella,美國戰(zhàn)后極簡抽象代表),尤其是他六七十年代的作品我覺得很感人,這么簡單又這么明確的繪畫語言。但我自己的繪畫還是不一樣。從開始到現(xiàn)在,我所有的方法,最大特點全部是線,用線來組織,這在西方幾乎沒有。西方人還是偏愛體積的塑造。
三聯(lián)生活周刊:“抽象”這個詞最早是怎么譯過來的?和你交談中,突然覺得這個中文翻譯特別準確,大象無形的概括。
丁乙:我沒有深究過這個詞的來歷。和“抽象”相似的詞,我們還用過非具象、構(gòu)成繪畫等等。說到構(gòu)成,學中國畫給我最大的體會,就是讓我看到中國繪畫里面始終意象的思維,從來沒有過純粹抽象和理性抽象。我們當時在國畫系的學習和傳統(tǒng)師徒相授的方式還是比較像,這和西方的條目設(shè)置完全不同。我們的老師今天教你畫石頭,明天教你畫松樹,畫山總結(jié)幾種皴法,畫竹子就是風竹雨竹,這些東西到腦子里再組合。國畫很難突破就在這個地方,它教會你所有的零件,等畫一幅畫時,這些零件再被取出來拼在一起。
“我好像沒有什么困惑”
三聯(lián)生活周刊:你9月份有個展覽是在抽象主義大師肖恩·斯庫利位于紐約切爾西的畫室里,你有四幅作品和他的作品一起展示。你們也有過對談。有沒有感覺到彼此之間看待抽象繪畫的差異?
丁乙:我們的對談從蒙德里安開始,但并沒有真正談論抽象藝術(shù)本身,好像是關(guān)于更大的題目。實際上我覺得我和肖恩·斯庫利之間的連接更多是從作品來感受,一個西方的抽象藝術(shù)家他在想什么,用什么方式作為他創(chuàng)作的基本靈感來源。我感受最深的是,他在談論繪畫的時候,更多時候談論的是情感。但我們起步其實很相似,基本形態(tài)都從方格開始。我的方法可能更嚴謹一點,我用鴨嘴筆,他用美工紙貼上膠帶刷完之后撕掉。
抽象藝術(shù)基本有兩類途徑,理性的必然從構(gòu)成起步,感性的必然從無意識的表現(xiàn)性起步,蒙德里安和康定斯基在他們的時代都用自己的實踐把這兩條途徑指明了。我現(xiàn)在仍然想要堅持住理性部分,但也覺得,自己感性的東西越來越多。這可能是年齡原因。在二十幾歲的時候沒有經(jīng)歷,我的情感是“假”的,有的是宣言和決心,也可以很徹底地用理性來實踐這種決心。但現(xiàn)在,這么多年積累的情感的豐富性是年輕時候達不到的,肖恩是這樣,我也是這樣。你無法抑制它在畫布上出現(xiàn)。
三聯(lián)生活周刊:你的畫看似嚴謹規(guī)整,但實則每一個單元的色彩和筆觸都有很多細微變化的隨機性。這恐怕是助手無法完成的。但現(xiàn)在很多藝術(shù)家都用助手來做作品。
丁乙:我見到過兩次基弗(Anselm Kiefer,德國新表現(xiàn)主義代表畫家之一),兩次他都跟我說,這個世界上就是我跟你兩個人不用助手創(chuàng)作了。他其實是想強調(diào),他是自己創(chuàng)作。但去過他的工作室后,我不敢肯定。他的工作室原先是一個百貨公司的倉庫,巨大,人在里面移動可能需要騎自行車。他差不多是一個區(qū)域一個主題幾十張畫,那么大的體量,一個人有點不可能。我覺得流水作業(yè)是肯定的,他經(jīng)常一個主題20張畫,同時開工。
三聯(lián)生活周刊:你覺得為什么中國藝術(shù)家如此推崇基弗?
丁乙:我覺得他的人文精神和中國需要的人文精神很像。他所有創(chuàng)作的主題都是反思,反思納粹,我們這一代人受他的影響是反思“文革”。燒焦的土地,荒涼,蒼茫,這些情緒我覺得有共通的東西。但年輕一代不一定有這種感覺了。
三聯(lián)生活周刊:你個人對他有強烈的共鳴嗎?
丁乙:我對他是對半切吧。我這個人很喜歡去藝術(shù)家工作室,通過工作室可以了解藝術(shù)家他是怎么想問題的。在基弗工作室參觀的最后,他跟我說,我?guī)闳タ匆幌挛易鼋o那些畫廊看的一個畫廊。我們走出工作室,進了另外一個大房子,私人飛機都可以開進去的那么一個高大空間。我一看就明白了,他其實是做給想要收藏他作品的機構(gòu)看的,大畫、飛機、雕塑……你要買就全部買去,一個非常完整的基弗收藏館。
三聯(lián)生活周刊:看過那么多大藝術(shù)家的工作室之后,還有誰留給你的感受比較深?
丁乙:去年我去了埃利亞松(Olafur Elias-son,丹麥著名當代藝術(shù)家)的工作室,我為他捏一把汗,因為鋪張得這么厲害,幾乎是一棟大樓,像學校一樣,每一層不同功能,這邊做光學研究,那邊做模型,頂樓還有大廚房,廚師在研究食譜什么的。我一直觀察這樣的明星藝術(shù)家,以多媒體方式創(chuàng)作,但技術(shù)革命太快,很容易今天有,明天沒有。藝術(shù)一經(jīng)商業(yè)的擴散,到處都有作品變異后的影子,藝術(shù)中令人崇敬的東西就全部沒了。
三聯(lián)生活周刊:那么在你看來,什么是“藝術(shù)中令人崇敬的東西”?
丁乙:正,即藝術(shù)家對藝術(shù)熱愛極其嚴肅嚴謹?shù)膽B(tài)度,還有對作品品質(zhì)的極致追求。沒有投機、沒有取巧、沒有歪門斜道,只想著做出最好的作品。
三聯(lián)生活周刊:藝術(shù)家尤其成名藝術(shù)家會有類似的困惑,就是走到一定的程度走不動了。你有過這種感受嗎?
丁乙:我好像沒有什么困惑,都在工作中化解了。中國當代藝術(shù)30年起起落落,我們經(jīng)歷很多。我覺得中國的藝術(shù)家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再需要像從前那樣看外面。我們可以在創(chuàng)作中把自己看世界的角度和力量充分表現(xiàn)出來,一頭扎進去,而不是像以前浮在表面,做一個(西方藝術(shù))謙虛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