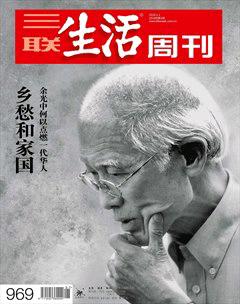安仁,從當代藝術中“觀看”歷史
薛芃
從成都到安仁古鎮很近,車程半小時,但目前的公共交通并不方便。如果不是自駕或包車,只能坐長途大巴前往,大概要開一小時。大巴啟動的那一刻,車上彌漫的四川各地方言和招手就停的習慣,很快就會把乘客帶離城市的氛圍,送進鄉鎮上嘈雜、熱鬧的“熟人社會”中去。那么,一個被定義為國際性大展的雙年展為什么會選在安仁小鎮舉辦?安仁又是哪里?
為什么是安仁?

首屆“安仁國際雙年展”的主展場離安仁古鎮很近。像許多在廢舊工廠基礎上改造的藝術區一樣,這里原是寧良機械工廠的生產車間。在雙年展的方案落地之后,建筑師劉家琨用48天完成了老廠房的改建工作,使之成為雙年展的永久場館,也完成了現代工業記憶與當代藝術之間的嫁接。
安仁鎮隸屬成都市大邑縣,其歷史雖可追溯至唐,但真正被人們記載是近百年的事。清代以來,安仁的社會結構以宗族為主導,目前仍存留27座公館,都是民國時期達官顯貴的私邸,這個數字甚至超過南京現存的26座公館。據史料,歷史上最多有56座公館同時在這個小鎮上,見證著安仁最鼎盛時期的榮光。這些達官顯貴并非來自五湖四海,而是大多出自清初從安徽徽州移民入川的劉氏家族。清末民國,劉氏在戰亂中迅速崛起,出了一批軍事、政治、經濟領域的重要人物,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這個家族掌握著四川和西康兩省的軍政兩界,實力雄厚。“大地主”劉文彩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他的故事也被渲染得最有傳奇色彩,此外還有國民革命軍第21軍軍長劉湘、24軍軍長劉文輝等人。
近幾十年來,安仁鎮早已褪去當年的輝煌,但特殊的歷史地位讓這里的底色依舊厚重。2005年,“建川博物館聚落”在安仁建成開放:棄官從商的樊建川先以抗戰、紅色年代為主題建了24座民間博物館,聚合在一起,與安仁的歷史相互呼應,形成一個“主題公園式”的博物館群落。后來,汶川地震博物館的加入,又給這個群落的“疼痛感”增加了一個新的維度,也與當代歷史產生關聯。
在安仁辦雙年展,一方面因為其歷史性,另一方面也因為安仁與中國現當代藝術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現在的劉文彩莊園里,仍然陳列著由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創作于1965年的群像雕塑作品《收租院》,114個人物,以劉氏莊園的故事為原型,用寫實和敘事的手法講述地主收租的全過程,是當時階級斗爭下的藝術產物。劉文彩故事的真實性在改革開放以后已經受到很多質疑,這是另一個話題。而它之所以成為中國現當代藝術的一個符號,不僅因為一度引起全國轟動,更重要的是作品完成后很快就進入了國際視野。上世紀60年代,德國左派對《收租院》很感興趣,也提升了這件作品在西方世界的知名度。1972年,第5屆卡塞爾文獻展邀請《收租院》參展,但由于正值“文革”未果。在種種歷史際遇下,《收租院》用本土化的藝術語言引發了超越國界的關注。又因為有《收租院》的存在,安仁國際雙年展在藝術層面也被認為有了文脈的依托。
最近的傳統
在安仁雙年展的展場,觀眾進入的第一板塊就是“譜系修辭”。策展人杜曦云和藍慶偉的意圖龐大:以安仁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遭遇為背景,嘗試梳理晚清以來中國社會的發展軌跡。雙年展總策展人呂澎則在展覽前言中寫道,這個板塊的意義在于“探討當下問題的歷史成因,和最近的傳統,以及對未來的期待和推測”。
呂澎將展覽主題定為“今日之往昔”,出自王羲之語“后之視今,亦如今之視昔”。“歷史”是呂澎一直強調的,“如果不對歷史問題很好地理解、思考和清理,怎么能走向未來?”他希望借由對安仁的觀察,激發出藝術家和參觀者對歷史的審慎思考。
從展覽的結構來看,一共分為四個主要板塊——“譜系修辭”“十字街頭”“回不去的未來”和“四川故事”。倘若稍微改變一下觀看順序,以“譜系修辭”“四川故事”“十字街頭”“回不去的未來”這個順序去參觀展覽,又是一個從地域性逐漸轉向國際性的思考過程,即安仁、四川、全球、未來。“譜系修辭”基于安仁歷史;“四川故事”以幾件四川題材的傳統作品為支撐,探討戲劇和歷史的關系;“十字街頭”這個板塊,可以用幾個關鍵詞來概括——權力、戰爭、選擇、變革,呈現出迷茫又掙扎的社會現狀;“回不去的未來”里展出了更多年輕藝術家的作品,試圖描繪未來,卻發現怎么也逃不出歷史。所以,“歷史”“往昔”是所有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影射的概念。
第一單元“譜系修辭”不能免俗地匯集了諸多中國當代一線藝術家的作品以吸引觀眾的目光,陳丹青、方力鈞、何多苓、隋建國、王廣義、徐冰、岳敏君、張曉剛、周春芽……這些藝術家的作品被擺放在醒目的位置。據呂澎介紹,在這個單元里,大約70%的作品都是這些大牌藝術家為此次展覽最新創作的。這些作品都帶有強烈的藝術家個人風格烙印,但仍有新鮮的可看性,一是他們自身與四川或四川美術學院淵源頗深,二是他們幾乎是同代人,有共同的時代痕跡,因此作品之間也可以形成某種對話。
張曉剛的《舞臺》尺幅巨大,以他一貫冷靜克制的風格來描繪一個魔幻的歷史場景,藝術家這樣描述這件作品:“在一個虛擬的空間中,我植入了三個不同時代、身份的床、雕塑、浴缸、浴桶等物件,鏡子中映射出一個扛著槍的少年。這些物件分別由來自安仁的素材,也有個人和國家的記憶——他們分別來自不同的時間并共處一室。空間的兩側設置了兩塊幕簾,烘托出某種魔幻舞臺劇的場景。”或許可以說,《舞臺》是“譜系修辭”板塊的一個縮影,象征時代趨勢和個體軌跡交織成的復雜譜系。
這個板塊中的不少作品,都有集體記憶的元素。比如徐冰的《蜻蜓之眼》,一個全部以網上公開發布的監控視頻鏡頭來完成的影像作品;姜杰作品《向前進向前進》中,象征紅色芭蕾舞的舞鞋;陳曦的《中國記憶系列》用不同時代的電視畫面來講述時代記憶,藝術教育小組(張濱、葉洪圖)用圓珠筆在畫布上復制雪花屏幕影像。它們都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產物,成為一代人的記憶,不同經驗的觀眾對這些歷史記憶都會產生不同的反應。
“四川故事”的策展人是意大利獨立策展人馬可·斯科蒂尼(Marco Scotini)。這個板塊有意思之處在于碰撞——西方視角與四川往事的碰撞,戲劇與歷史的碰撞。馬可長期活躍在歐洲當代藝術領域,在他近幾年策劃的大型展覽中,2015年的“太早太晚——中東藝術及其現代性大展”、2016年的“在圍墻的那一邊——東歐生態藝術展”、2017年的“白種獵人——當代非洲檔案與影像”,都是聚焦于地區性社會生態的展覽。
這個板塊對歷史的探討以幾部戲劇為依托,探討“臉譜化的戲劇表達”。1940年德國劇作家貝爾托·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劇本《四川好人》是這個板塊的一條線索,串聯出魏明倫根據此劇新編的《好女人,壞女人》,以及與布萊希特有交集的梅蘭芳在上世紀50年代出訪蘇聯時的一系列史料梳理。在這條主線之下,策展人也嘗試搭建一個“形而上”的劇場,當觀眾進入劇院后臺式的展廳后,木偶、玩具、面具、戲服,這些道具進一步增強了展覽的代入感,“讓觀眾轉變成單個或群體故事的敘述者”。馬可更像是一場戲劇的幕后導演,他希望呈現的是一出結構完整、內容統一的戲,而不單單是一個拼盤式的展覽。
從馬可的這出大戲中走出,一進入“十字街頭”展廳,會立刻被展廳內嘈雜、躁動的氣氛包圍,不自覺地感到焦慮和不安。這種感覺不是來自于直接的視覺沖擊,而是首先來自聽覺。“十字街頭”這個題目取自1931年12月11日魯迅與馮雪峰創辦的雜志《十字街頭》,策展人劉鼎、盧迎華希望借由這本雜志的現實性和戰斗性來警示當下。大量影像作品,如香港藝術家陳佩之重新編排創作的《等待戈多》,意在提醒觀眾哪些東西是更值得被更新和重建的;斯坦亞·卡恩(Stanya Kahn)的《切莫回歸沉睡》拍攝于密蘇里州堪薩斯城因經濟危機遺留的爛尾樓里,是一部讓人產生不安感的實驗性電影,隱喻國家暴力導致的國民創傷;《一個接一個的戰爭》講述一個有多重國家背景身份的逃兵流亡的故事,影射愛國主義與現實政治生活之間究竟應該有怎樣的關系……在這些影像里,槍炮聲、吶喊聲此起彼伏,雖然每一個作品都有獨立播放的小空間,但集合在同一個展廳中,觀眾可以感受到世界上各個角落的不安與疼痛感。
如果我們站在未來的視角,這種疼痛感是會增強,還是減輕?這是“回不到的未來”這個板塊引發的思考。在這里,策展人劉杰和呂婧虛擬了一個自未來回望當下的場景,也恰好呼應了“后之視今,亦如今之視昔”的命題。
小鎮與大展
在小鎮舉辦國際性的大型藝術展,安仁并不是國內第一個。除了上海雙年展、廣州三年展等有影響力的展覽之外,也有一些攝影雙年展、建筑雙年展選在不為人熟知、規模不大的小城鎮舉辦。2016年3月,烏鎮舉辦“烏托邦·異托邦——烏鎮國際當代藝術邀請展”,引起廣泛關注。但這個展覽最終沒有固定成“雙年展”或“三年展”,主辦方還在試探藝術展這種模式是否對小鎮整體發展起到持續的良性作用。
雙年展這種形式本身也經歷過一個從邊緣走向主流的過程。1895年,第一屆威尼斯雙年展雖由威尼斯市長牽頭籌辦,但從評委到參展藝術家和作品,都是脫離學院派傳統的,他們主張更前衛的“現代精神”,為那些進不去美術館辦展的邊緣藝術家打造一個獨立的展覽空間。而百年后的今天,威尼斯雙年展已是國際藝術界的主流標桿。威尼斯雙年展不僅是一個展示藝術作品的盛會,更重要的是帶動了全球藝術產業鏈的轉動。在第一屆威尼斯雙年展中,參展的500多件作品售出了186件,總售價超過36萬里拉(以當時貨幣計)。當這個為期半年的雙年展閉幕時,參觀人數總計22萬余人。
在談到安仁雙年展如何保持旺盛的狀態時,呂澎認為:“人文生態的搭建需要時間,要靠堅持和不斷的投入來強化一個展覽或某個地域在文化上的持續貢獻。”安仁雙年展主辦方的負責人為我們描繪了一個更清晰的愿景,雙年展是對安仁古鎮規劃改造的一個起點,進而開展藝術品拍賣、藝術品衍生品開發、藝術市集、藝術節等一系列產業鏈條。當雙年展作為產業鏈中的一環存在時,該如何保持其藝術水準和學術水準,又如何兼顧在地性與全球性?這是拋給未來策展人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