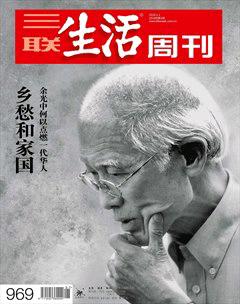減稅的潛力在哪里?
邢海洋
4月到2017年底,特朗普的減稅計劃終于落地,美國的企業所得稅從35%降到了21%,個人所得稅率也有所下降。中國的企業所得稅是25%,除此之外,企業承擔的社保繳費也遠高于國際水平。全球降稅的聲浪中,我們是否會跟進呢?
其實早在美國之前,中國政府就致力于為企業減負了。“五險一金”中有一種99%的人從未有幸領取過的失業保險金,繳費比例一度高達工資的3%。因為領取率低,該保險金曾年年巨額結余,在2015年開始的企業減負中首當其沖,至今已經降至1%。至于不斷發出“入不敷出”警報的養老社保,對尚有余力的如養老金累計結余可支付的月數高于9個月的省份,單位繳費比例已經由20%降至19%。多次調整后,我國企業繳存的“五險一金”費率中位數從44%降至40%以下,約降低了4.5個百分點。相對于約70%的企業綜合稅率,相當于降低了6.4%。當然,這和美國大刀闊斧一下子將企業所得稅免去了一小半比,顯得微不足道。并且,中國的減稅,最容易的部分降下去以后,又到了一個瓶頸期。
美國減稅之所以“四兩撥千斤”對周邊國家形成了虹吸效應,在于美國的稅負體系中企業所得稅只占很少的部分,這就給予它較為靈活的操控能力。雖然美國有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大公司,但是公司所得稅只占聯邦政府稅收收入的10%左右,而個人所得稅占比達到48%。以直接稅為主導的西方國家,個人所得稅、資本利得稅、遺產稅等林林總總的圍繞納稅人收入的稅種“層層包圍,處處設卡”,將個人的各種收入都納入到稅收體系。而相對于個人,企業作為創造價值、追逐利益的現代經濟的直接參與者,對稅收體系最為敏感,卻不是納稅的主體,而是價值傳導的“二傳手”。當今的全球經濟體系,商品流動的自由度遠勝于企業遷移的自由度,企業的自由度又遠勝于個人在國家間的遷徙能力,在收入流向的終端,也就是個人處征稅,也就有了最穩定的稅基。又因為征稅于終端,掙得多的多繳,掙得少的少繳,除了“養活”公務人員、為公共服務付費,稅收對收入二次調節的“副作用”也發揮了出來。
我們以間接稅為主導的稅收體系,一大半的稅收“隱藏”在商品之中,最后由消費者買單。而富人消費少,窮人購物卻是剛需,直接稅為主體稅種的稅收體系無疑是向窮人征集了重稅。扭轉這一稅負失衡,建立現代稅收制度就成為經濟結構調整的必由之路。這條改革路徑,在個人所得稅的調整中已見端倪。在2006年至2011年的5年間,國家曾連續3次上調了個稅起征點,從800到1600到2500再到3500元。可最近的6年時間,曾經緊鑼密鼓的個稅調整徹底啞火,于是乎個稅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2016年突破萬億大關,增速竟達到17.1%。我國的個稅稅率分為七檔,剛過3500元起征點還只有3%的稅率,可很快稅率階梯就“陡峭”起來,一旦應納稅部分超過4500元就是20%的稅率,超過9000元就是下一個25%的階梯,對于城市中勉強生存的所謂“中產”,幾乎無一例外都會觸碰到四分之一收入來納稅的高收入。也就是說,生活在一、二線城市的國人,已有相當比例與西方國家居民的稅負看齊了。
減稅的另一個重頭戲流轉稅也在下降,2016年啟動的營改增一年共減稅7000億元。但最高檔增值稅率仍為17%,遠高于海外消費稅的稅率。當然流轉稅最終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并非企業的真實稅負。
最終,企業的真實稅負還是高在了“五險一金”等人工費率上,即使下降了,我國企業繳費養老金比例為19%,是美國的3倍,也高于福利國家瑞典的11.9%、老齡化國家日本的7.7%,而企業減負的潛力也正在此。一些省份養老金虧空,是1992年退休金由企業向社會轉制的結果,巨量國企收益理應用于彌補這個虧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