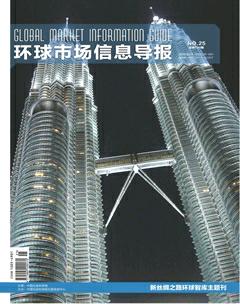“一帶一路”金融合作的意義與挑戰
袁燕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及其重大意義
2013年9月,習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首提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2013年10月,習主席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講時提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合稱“一帶一路”倡議。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順應了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以及社會信息化發展的大潮流,對中國而言,“一帶一路”建設有利于形成陸海統籌、東西互濟的全面對外開放新格局,是我國積極應對全球經濟政治形勢深刻變化、適應國內改革開放發展的新需要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重要的頂層設計。“一帶一路”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時代背景。
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動力
當前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一是新興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復蘇發展的引擎。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產業結構進入深度調整期,世界經濟復蘇緩慢。發達經濟體由于高額政府債務、歐債危機沖擊和高失業率等因素的影響,增長乏力,難以帶領世界經濟的發展。據IMF統計,發達經濟體GDP增長平均值從2001-2007年的2.25%下降至2008-2014年的1.3%。世界經濟中心發生轉移,新興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二是新興經濟體增長漸趨放緩。盡管金融危機之后,新興經濟體成為引領經濟發展的引擎,但是因為內部一系列結構性問題以及主要新興經濟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新興經濟體增長放緩。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結束了近10年的快速增長,全球經濟增速也隨之放緩。三是世界投資、貿易格局調整。世界資本流動速度減慢,發達經濟體對外投資減弱,全球資本跨境流動下挫,新興經濟體資本市場持續動蕩;疲弱的經濟增長也導致世界貿易低迷,諸多國家出口形勢惡化,世界貿易也經歷著深度調整。
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
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二戰之后圍繞著美元霸權而建立起來的,其兩大支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布雷頓森林體系為國際融資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有助于金融業和國際金融市場發展,IMF和世界銀行也對戰后世界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隨著世界經濟格局的發展變化,原有國際經濟治理機制及規則已經不能滿足所有國家的發展需要。近十年來,新興市場對世界GDP增長貢獻率超過50%,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貢獻率超過70%,整體影響力不斷上升。據IMF統計,新興經濟體所占世界經濟比重由2000年的23.6%上升到2012年的41%,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來計算,新興經濟體占世界經濟比重則由40.7%上升到53.7%;從國際貿易的層面來看,25年來,新興經濟體占比從之前的15%上升到40%;從全球FDI流入來看,25年來,新興經濟體占比從15%上升到2012年的58%。與此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新興經濟體的經濟體量和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卻嚴重不匹配。在IMF和世界銀行中,份額和投票權未能及時調整,主導權仍掌握在西方國家手中,而且美國對該組織具有否決權,兩個機構都存在較為嚴重的代表性問題,既無法有效捍衛發展中國家利益,也無法使其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此外美國主導的TPP與TTIP談判正竭力重塑全球新的貿易體系和規則,企圖繼續占領全球治理高地。
滿足國際國內經濟發展新需要
契合世界經濟復蘇發展的需要。“一帶一路”貫通了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東連亞太經濟圈,西接歐洲經濟圈,覆蓋約44億人口,經濟總量約21億美元,分別占全球的63%和29%,“一帶一路”是世界上最長的經濟帶,也是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合作帶。同時,“一帶一路”有利于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基礎設施的提級換擋,打破增長瓶頸,同時也可在全球范圍內促進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增加發達經濟體的出口需求,進而促其進行結構性改革,對于新興經濟體來說,可以通過“一帶一路”深入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全球經濟治理,逐漸增強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而公共品能力建設正是全球經濟治理體制的核心內容。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可以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逐漸增強自身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滿足區域發展的需要。亞太地區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發展區域,也是世界經濟的主要引擎。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院發布的《亞太地區發展報告(2014)》藍皮書預計,亞洲地區名義GDP約為41.1萬億美元,亞洲占全球GDP比重為31.8%。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一項題為《2014亞太大都市觀察:全球增長引擎》的研究報告顯示,2014年100個亞太地區大都市經濟體GDP約占全球20%,對全球GDP增長的貢獻率高達29%,其人均GDP增長2.6%,就業增長1.5%,都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同時,亞太地區不少國家的基礎設施較為落后,亟需提高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可以說基礎設施的落后極大地制約了亞太地區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也給該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帶了很大的不確定性。據世界銀行估計,東亞一年對基礎設施投資的需求高達6000億美元,南亞在未來10年也有巨額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需求。在此背景下,中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該倡議有利于亞太地區進一步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區域互聯互通。而亞洲地區的互聯互通有利于發揮基礎設施建設的“乘數效應”,帶動相關企業發展,為資本和技術提供發展機遇,這對于亞洲乃至世界的經濟增長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一帶一路”金融合作面臨的政治挑戰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治不確定性極高,因為國情各異,差異化過于明顯。
中東是從亞洲到歐洲、非洲的一個重要節點,無論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還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都必須經過中東。例如利比亞、敘利亞和也門,在這幾個國家本來資源比較豐富,經濟上看是投資合作的潛在伙伴,但是沖突與戰爭卻是一直不停歇,完全無法提供穩定的環境供經濟穩定發展。中國在這些國家進行的項目和大規模投資,會一直面臨無法收回資金的風險,一旦所在國政治安全形勢反復,必然是血本無歸。endprint
中國建設海上通道面臨的主要安全威脅包括以下幾方面:一個是美國因素,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也是全球范圍的海洋大國,在印度洋海域以及西太平洋有著巨大的影響力,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和“新絲綢之路”倡議,都會對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產生實質影響;二是印度、日本作為區域大國,與中國一直有著海洋利益的爭奪,日本在太平洋海域海上力量依舊強大,綜合海上勢力不容小覷,印度一直視印度洋為自己的禁臠,海洋力量逐漸從近海向遠海發展,對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拓展構成有力競爭;三是在印度洋沿岸的海盜襲擊依然是層出不窮。海上通道建設過程中是必須要考慮這些潛在風險因素的。
通過二戰和冷戰,美國引領建構了當今世界的全球格局,與之相比,中國的崛起雖然強勢,但是從崛起之初開始,直到現在成為世界大國,所經營的時間還是太短暫。我們要建設好“一帶一路”,就要切實發揮“共商、共建、共享”精神,就必須團結更多的“鐵哥們”,多一些巴基斯坦這樣的兄弟國家,也需要沿線諸國共同分擔安全與義務。
“一帶一路”金融合作的經濟挑戰
區域金融發展不平衡。“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要位于亞洲地區和歐亞地區。大部分都是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的特點就是金融系統由政府主導市場化程度較低,對金融資源的調動能力不足,和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差距很大,所以很難適應金融行業的高速發展。“一帶一路”金融合作對于各國的金融協同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沿線國家金融發展水平不一致,金融政策不對接,會極大地阻礙“一帶一路”金融合作。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權信用等級跨度較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涉及中東等長期動亂的國家和亞洲一些深受三股勢力危害的國家,它們的主權信用狀況都不高,而且隨時面臨主權信用級別下調風險。國家主權信用級差跨度大,容易形成主權債務危機和銀行危機之間的惡性循環,這不利于“一帶一路”金融合作的發展。
債務國違約風險較高。“一帶一路”最重要的依托就是各類重大項目,也就是說資金問題就是關乎“一帶一路”建設成敗的問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是發展中國家,整體上投資環境不如西方發達國家,中國“走出去”的企業無論是投資基礎設施還是其他產業,其回報率都不會很理想,尤其是面臨著各類風險,不可能保證所有投資都能夠收回來。一些國家經濟基本面表現較為不好,有著巨額的經常項目赤字,這樣的國家對于投資者來說就是高風險債務人。這意味著如果中國向這些國家提供資本和融資項目,將很有可能面臨違約,無法收回投資。如果債務國無法償付銀行貸款,項目無法收回投資,中國經濟將遭受額外的巨大損失。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