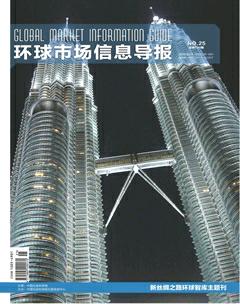論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司法控制
薛梓倩
新《行政訴訟法》的相關規定
《行政訴訟法》修正案于2014年11月1日正式表決通過,這是該法頒布25年以來的第一次修改,其修改的亮點很多。但是對于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控制方面,可以說其仍然沒有太大的突破。新《行政訴訟法》第70條將舊法的“顯失公正”改為“明顯不當”,并且不再限定僅在行政處罰領域,范圍上有所擴大。盡管在用語上有所修改,其二者在司法運用上仍屬于不確定的法律用語,在司法實務中仍然因為存在較大爭議而無法適用的困境。
司法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存在的問題
合理性審查原則的缺失。《行政訴訟法》第6條的規定是人民法院在審理行政案件時,對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結合第13條第2項和第53條之規定可以發現,我國目前可以進行司法審查的行政行為的范圍只包括具體行政行政和行政規范性文件,且司法審查的內容僅包括審查上述行為是否合法,而未將具體行政行為的合理性以及行政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的合理性納入審查范圍。這就導致一些行政機關在法律規定的裁量幅度內進行的不合理裁量行為逸脫司法審查的監督。
法律用語的不確定性。《行政訴訟法》第70條的規定是:人民法院對主要證據不足、適用法律、法規錯誤、違反法定程序、超越職權、濫用職權、明顯不當的行政行為有權判決撤銷或部分撤銷,并可以判決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為。其中,后兩項的“濫用職權”和“明顯不當”含義比較模糊。法院究竟能否審查、是否應該審查行政行為的合理性一直是行政法學界爭議的焦點話題,“明顯不當”這樣的規定顯然不僅僅處于“合法性”的范疇。(史筆、曹晟.新<行政訴訟法>中行政行為“明顯不當”的審查與判斷[J].法律適用,2016(8):24.)
司法機關監督職能受限。行政訴訟法盡管賦予了司法機關可以審查“濫用職權”、“明顯不當”的行政行為,賦予其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監督職能,但是卻又規定了其只能進行合法性審查,其監督職能大大受限。人民法院以“濫用職權”和“顯失公正”(修訂前的說法)為由對行政自由裁量權進行規制的判例占極少數。這同時也是因為合理性判斷標準十分模糊,操作起來容易產生侵入行政權的越界行為,因而法官在審理過程中都十分保守和謹慎。
完善行政自由裁量權司法控制的對策
筆者認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
明確合理性原則的適用。筆者認為,只運用合法性原則來審理案件本來就與用司法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相矛盾。同時,70條的“濫用職權”、“明顯不當”等規定的用語來看,也顯示出法律條文背后蘊藏的合理性原則的適用過程。只有確定了合理性原則在司法審查中的正當性,才能使得相關的法律條文不“形同虛設”,才能真正起到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控制作用。
細化“濫用職權”、“明顯不當”的內涵和外延。是否構成“濫用職權”,可以考慮以下幾個因素:1.行政行為是否符合立法目的。立法在設置行政自由裁量權時肯定有其目的,看是否違背了這一立法目的。2.行政行為的動機是否符合行政目的。自由裁量權的行使目的是為了完成行政處罰等具體行政行為,看是否達到了該具體行政行為想要達到的效果。例如:規范行政相對人的行為。3.是否考慮了不相關因素或者不考慮相關因素。(應松年.行政訴訟法律制度的完善、發展[J],行政法學研究,2015(4):5.)
是否構成“明顯不當”,考慮以下幾個方面:1.是否違背了比例原則的要求。包括是否妥當、必要和是否符合法益相稱性。(伺海波.論行政行為“明顯不當”[J].法學研究,2016(3):71.)。2.是否符合公平公正。包括符合慣例、前后一致。3.程序是否違法。有無告知、聽證、回避、重大事項集體討論決定等。
發布典型司法判例。在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司法審查過程中,如果有先例可以遵循,則大大減少法官自由裁量行為的任意行使,這樣不僅有利于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司法控制,也能形成相對統一的判決標準和依據。避免因依據行政法原則進行判決的裁量空間過大的問題。
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控制需要的是一種多元化的、綜合的監督和控制。(湛中樂.《行政訴訟法》的“變革”與“踟躕”[J],法學雜志,2015(3):24-25.)。司法控制作為一種事后控制手段,若對其審查原則進行細化,明確“濫用職權”、“明顯不當”的內涵和外延以及發布典型判例,司法對行政裁量權的控制也必將逐漸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法學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