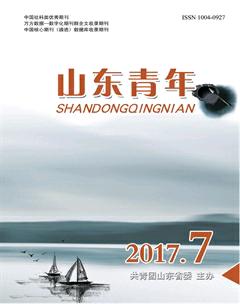元好問與金源文學生態
肖陽
摘要:元好問獨特的精神風貌和藝術個性,離不開涵育它的金源文化背景。金初至中葉的幾位國君較為通脫和大度的治國態度,以及他們對先進文化采取的積極而寬容的吸收態度,客觀上促進了金源文化的發展,為游牧文明向農耕文明的轉向導引了方向。“金源一代文物,上掩遼而下軼元,非偶然也”,正是這種崇文重士的風尚,為女真人的百年基業打下了基礎。統治者對文事的身體力行對文人階層產生的積極而深遠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元好問亦深受當時文學生態的沾溉。
關鍵詞:元好問;金末元初;文學生態
元好問作為金源歷史上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不僅以詩文見長,更是一位器識超拔的詞人。所作《遺山樂府》,存詞370余首,其數量之眾多、藝術之高邁,為當時之罕有,比之南宋詞人毫不遜色,堪稱金代詞壇之翹楚。在藝術風格上,其矯異不群而雄豪勁健,蕭散閑舒而悲涼淡遠;在表現手法上,類型多樣、兼收百家,融“豪放”與“婉約”為一爐;在內容抉擇上,較為廣泛地反映了金元之交的歷史禍結與社會生活;在內涵主旨上,真實而深刻地揭示了壯懷磊落、抑郁難伸的憤懣心理,抒發了懷想故鄉、憂念國是的深沉情感,流露出對故國傾覆、恢復無計的無限悲慨。總之,遺山樂府以自己的藝術風貌,贏得了后世的關注。元好問獨特藝術風格的形成,深受當時文學生態的沾溉。統治者對文事的身體力行,對文人階層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一、金源文化何以“上掩遼而下軼元”?
金朝是由游牧民族建立起來的,但是統治者卻能適時收羅大批漢族士大夫協助統治新征服的州縣,并迅速接受了中原地區的先進文明,還運用進步的工藝技術,努力發展生產,以至在世宗(公元1161—1189年在位)至章宗(公元1190—1205年在位)年間,經濟、文化均出現了繁榮局面:“當此之時,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余。……時稱小堯舜”(《金史·世宗紀》)。
可以說,這種局面的產生有著一定的歷史根源。金初及至中葉的幾位國君較為通脫和大度的治國姿態,以及他們對先進文化采取的積極而寬容的吸收態度,客觀上促進了金源文化的發展,為游牧文明向農耕文明的轉向導引了方向。在這一點上,誠非遼所能比肩。誠如史家所言:“金用武得國,無以異于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金史·文藝傳》)
下面,讓我們先來看一下金朝中前期歷代君主的文治:
金太祖完顏旻:“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金史·文藝傳》)、“金初無文字也,自太祖得遼人韓昉而言始文”(清莊仲方《〈金文雅〉序》)、“天輔五年十一月戊申,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并先次津發赴闕”(《金史·太祖紀》)。
金太宗完顏晟:“金天會元年,始設科舉,有詞賦、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等”(李世弼《登科記序》,《金文最》卷二三)、“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圖,宋人多歸之”(《金史·文藝傳》)、“遼太宗入汴,載輅車、法服、石經以歸”(《金史·劉彥宗傳》)、“太宗入汴州,取經籍圖書,宋宇文虛中、張斛、蔡松年、高士談輩后先歸之,而文字煨興,然猶借才異代也”(清莊仲方《〈金文雅〉序》)、“天會五年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余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金史·宗翰傳》)。
金熙宗完顏亶:熙宗完顏亶,少小即為韓昉等儒士教習之,“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弈棋戰象”,被舊大功臣目為“宛然一漢家少年子”、“徒失女真之本態”(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六六)。平日里“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或以夜繼焉”,更有著“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的文治思想,亶提倡尊孔,曾“親祭孔子廟”,并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為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金史·熙宗紀》)熙宗說是這樣說的,做也是如此做的。《金史·文藝傳》說他“款謁先圣,北面如弟子禮”,可見一斑。
海陵王完顏亮:海陵王完顏亮(1122—1161),字元功,本名迪古乃,皇統九年(1149)弒熙宗取而代之。歷史上雖然名聲不佳,但卻“頗知書,好為詩詞”,詩作也是“語出則倔強,矯矯有不為人下之意”(《桯史》)、“一詠一吟,冠絕當時”(《大金國志》卷一五),又設國子監、張揚文教。亮雖系篡權奪位,但卻繼承了前代君王的文治傳統,又力排眾議,遷都中都(今北京),以中原天子自居,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大大促進了女真民族漢化的進程。究其思想的根源,其父完顏宗干又進入了我們的視野,史載:宗干執政,大力革新女真舊俗,“始儀禮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興庠序,設選舉,治歷明時,皆自宗干啟之”(《金史·宗干傳》),這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極大地推動了金王朝的封建化,同時又促進了封建文化的發展,更對完顏亮奪取政權后的施政策略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金世宗完顏雍:“金代九君,世宗最賢”(清趙翼《廿二史剳記》卷二八),世宗完顏雍在位期間,大力倡導漢文化,置太學、詔京府設學養士,并認為“五經”是“仁義道德所在”,將用女真文翻譯的儒家經典頒行天下,為女真人學習漢文化提供了有利條件。其時一文學家指出:“大定間,天子留意儒術,建學養士,以風四方,舉遺湮,興廢墜,曠然欲以文治太平”(金黨懷英《重建鄆國夫人殿碑》,《金文最》卷三五)。
金章宗完顏璟:章宗完顏璟(1168—1208)天資聰穎、雅好詞章,又能詩善書、“詩詞多有可稱者”(劉祁《歸潛志》卷一)。史載:“章宗性好儒術,即位數年后,興建太學,儒風盛行。學士院選五六人充院官,談經論道,吟哦自造。群臣中有詩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擢居要地,庶幾文物彬彬矣。”(《大金國志》卷二一)《歸潛志》卷一二說他“聰慧,有父風,屬文為學,崇尚儒雅,故一時名士輩出。大臣執政,多有文采學問可取,能吏直臣皆得顯用,政令修舉,文治燦然,金朝之盛極矣”。世宗大定(1161—1189)和章宗明昌(1190—1196)年間,金與南宋達成了和議,“朝廷清明,天下無事”,“承平既久”,統治者“留意稽古禮文之事”(金趙秉文《尚書左張公神道碑》,《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一二),為文學繁榮提供了必要的條件。endprint
除了以上列舉的帝王,皇室宗親、達官顯貴篤好文物者更是彬彬可觀。如宣孝太子完顏允恭(1146—1185),乃世宗子,章宗父,雖未登大寶便溘然而逝,但也是“好文學,作詩善畫”(金劉祁《歸潛志》卷一)。劉祁評價他說:“宣孝太子最聰明絕人,讀書喜文,欲變夷狄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歸潛志》卷三)其他如完顏勖少時即好文學,國人呼為秀才,凡宴游輒作詩以寄意。宗翰、宗雄身為武將,卻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令人驚嘆。密國公完顏璹以書畫傳世,文章更是名重一時……
通過以上的引述,我們可以發現:“金源一代文物,上掩遼而下軼元,非偶然也”,蓋因“帝王宗親,性皆與文事相浹,是以朝野習尚,遂成風會”(清·趙翼《廿二史剳記》卷二八)。可以說,正是這種崇文重士的風尚,為女真人的百年基業打下了基礎。統治者對文事的身體力行對文人階層產生的積極而深遠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二、“借才異代”與特重科舉
金源王朝重視科舉選官,“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金史·選舉一》)。自金太宗天會元年(1123)至金哀宗正大六年(1229),包括特賜,共舉行了四十四次科舉。雖然后期隨著吏治的腐敗,科場之弊叢生,但還是應該說,其作用及對文人的影響不容忽視。大部分統治者對知識分子的器重和照顧態度,也是金源文化走出“荒漠化”的關鍵。史載:即使是在衰世,官學也不廢廩給。
宣宗興定元年二月,尚書省請罷州府學生廩給,不許。
自章宗泰和元年九月,定贍學養士法。生員給民佃官田人六十畝,歲支粟三十石。至是省臣以軍儲不足,請罷之。帝曰:“自古文武并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況今日乎?”其令仍舊給之。
文人待遇之優渥,于此可見一斑。當然,這里并不存在為了證明什么而刻意抹殺一些歷史真實,金源一些士人也曾因文致禍,以致遭殺戮。任何一個朝代的統治者的政治舉措都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不管科舉還是其他方略,都只是為了更好地鞏固自身的統治,根本目的并不是為了使文人才有所用,抱負得以伸展。
金源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北宋文化,建國當中,女真族的不斷南侵,迫使宋廷南渡,而一部分文人則在兵燹之亂中被帶入北方(我們不應忽略這樣的事實,宇文虛中、吳激、蔡松年、高士談……,這些金源文壇上聲名顯赫的人物,都是由宋入金的,他們的聲望、地位足以引導整個金源文學史的走向),他們的加盟加速了先進的農耕文明的傳播,提高了北方地區的文化水平。而北方的雄山巨川又壯闊了他們的襟懷,使得這些士人的文脈里又多了幾分貞剛質實的骨力。戰爭帶來的是創痍,但在兵燹交接的同時,文化也在交融。
從某個意義上說,金源文化是嫁接的產物,是在戰爭與遷徙中不斷成長起來的。“中原文獻實并入于金”(《〈全金詩〉提要》)以及開國之初的“借才異代”,使它有了不容抹殺的北宋血統,比起偏安一隅的南宋兄弟,它的文化又由于自身的特質而呈現出簡單、質樸、本色而交融的品性。元好問作品中的兼容并蓄,其實也是金源文學生態影響下的一種反映。
[參考文獻]
[1]姚奠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集(增訂本)》[A],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2]趙興勤,《元遺山研究》[M],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
基金項目: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遺山樂府〉與金末元初文學生態研究》(項目批準號:2015SJD49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徐州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前與特殊教育學院,江蘇 徐州 2210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