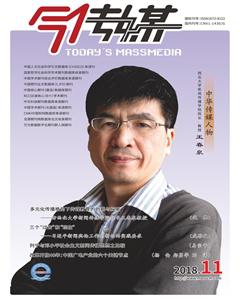文徵明《洛原草堂圖》的藝術(shù)價(jià)值探析
韋喬丹
摘要:《洛原草堂圖》是文徵明為白悅所作,保存完整,附有大量題跋,書(shū)畫(huà)俱佳,具有極高的研究?jī)r(jià)值。《洛原草堂圖》載于《故宮已佚書(shū)籍書(shū)畫(huà)目錄四種》中,清代溥儀皇帝退位后,以賞賜溥杰為由將此畫(huà)轉(zhuǎn)運(yùn)出宮。幾經(jīng)流轉(zhuǎn),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本文通過(guò)對(duì)《洛原草堂圖》的畫(huà)面表現(xiàn)內(nèi)容和題跋進(jìn)行分析,以及闡述其流傳情況,初步探析《洛原草堂圖》的藝術(shù)價(jià)值。
關(guān)鍵詞:文徵明;洛原草堂圖;題跋;流傳
中圖分類(lèi)號(hào):J205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672 - 8122(2018)11 - 0151 - 03
一、《洛原草堂圖》的圖與記
《洛原草堂圖》為手卷式,縱28.8厘米,橫94厘米,絹本設(shè)色,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著錄于《石渠寶笈續(xù)編》¨。文徵明款識(shí)云:“嘉靖己丑七月四日,徵明寫(xiě)洛原草堂圖”,鈐印:文徵明印(白文),停云(朱文,圓形),徵仲(朱文)。嘉靖己丑即為1529年,這一年文徵明60歲,此畫(huà)是文徵明為白悅所畫(huà),白悅別號(hào)“洛原”。
從表現(xiàn)內(nèi)容來(lái)分析,《洛原草堂圖》所畫(huà)的是一座莊園,有家舍和耕植活動(dòng)。畫(huà)面以中間河流為分割,小橋前的一小塊陸地和過(guò)橋后的屋舍形成兩排,遠(yuǎn)處有山巒瀑布,分為前景、中景和遠(yuǎn)景。前景中,兩位文人雅士出現(xiàn)在畫(huà)面右側(cè),像是從畫(huà)外走向畫(huà)中。前面一位身著素衣,手指著橋的對(duì)岸,頭回向身后的文士,像是在引領(lǐng)紅袍文士過(guò)橋人園。身后有兩位仆童,一位捧書(shū),一位攜琴。前景陸地上的四棵松樹(shù)高大突出,與河對(duì)岸的中景形成空間構(gòu)圖上的呼應(yīng)。中景的內(nèi)容貫穿了畫(huà)面的對(duì)角線(xiàn),展現(xiàn)出了園林的規(guī)模之大。茂盛的樹(shù)林掩映著屋舍,中間的堂屋中有位身著紅衣的小僮站立等待主客的到來(lái)。在畫(huà)面左方的水榭中,再次出現(xiàn)了前景人園的兩位雅士,紅衣士人側(cè)著身子像是在與仆童說(shuō)話(huà),也像是在觀魚(yú),素衣文士坐在右側(cè)。一位仆童端著水果準(zhǔn)備進(jìn)入水榭,另一位紅衣仆童也在往水榭走去。畫(huà)面右方還有位老農(nóng)扛著鋤頭正準(zhǔn)備過(guò)橋。畫(huà)中人物活動(dòng)不是簡(jiǎn)單的點(diǎn)景人物,而是巧妙地表現(xiàn)了兩個(gè)時(shí)空,具有強(qiáng)烈的敘事意味,展現(xiàn)出了白家接待賓客的場(chǎng)面,閑適的生活氣息。遠(yuǎn)景山巒之間有一條瀑布垂流直下,穿過(guò)水榭,匯人中間的河流,使前景、中景和遠(yuǎn)景緊密結(jié)合。楊仁愷在《國(guó)寶沉浮錄》中稱(chēng)贊此畫(huà)是少有的名品。
從筆墨和色彩的形式分析,《洛原草堂圖》屬于文徵明的細(xì)筆小青綠山水。筆墨受元人影響,山石用淡干墨皴擦,有小披麻皴和小斧劈皴,但用筆簡(jiǎn)潔,弱化了皴法的表現(xiàn)[2]。樹(shù)干用筆道勁,樹(shù)葉有勾勒而成的夾葉和攢點(diǎn)積聚的點(diǎn)葉。山石設(shè)色用赭石染石腳,再施石綠,赭石和石綠色的調(diào)和形成整體的黃調(diào)子,溫雅蒼潤(rùn)。這樣弱化皴法,以短線(xiàn)和干擦表現(xiàn),并使之融人大地色塊形成一個(gè)統(tǒng)一的整體,是文徵明青綠山水的顯著特點(diǎn)。這與元人山水營(yíng)造的荒疏冷寂之意境不同,《洛原草堂圖》透露出文徵明對(duì)生活的熱忱和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描繪,同時(shí)暗含了文徵明探求新的青綠山水審美形態(tài)的歷程。
從題跋和記文來(lái)看,畫(huà)幅的后面是文徵明撰寫(xiě)的《洛原記》,卷后還附有眾多同時(shí)代人的詩(shī)文題跋,按順序排列有許宗魯?shù)馁x《洛原之什》,劉儲(chǔ)秀、李濂、康海、王九思的詩(shī)文,唐龍撰寫(xiě)的《洛原記》,許成名、薛蕙題詩(shī),楊慎撰寫(xiě)的《洛原草堂記》,馬卿撰寫(xiě)的《洛原》以及趙時(shí)春撰寫(xiě)的《洛原賦》,另外有白悅的信札一通和清人張照的跋文(1735年)。文徵明在《洛原記》中寫(xiě)到白悅家世鼎貴,是一個(gè)不忘故土,合乎仁禮之本的人。希望白悅績(jī)學(xué)厲行,考取功名,名揚(yáng)家世。三年后白悅中進(jìn)士,出仕為官。白悅拜訪(fǎng)友人,向友人展示《洛原草堂圖》,講述“洛原”來(lái)歷,邀友人題跋。這些題跋者都是官員,共同講述了“洛原”的由來(lái)和白悅的家世與德行。
二、《洛原草堂圖》的流傳
《洛原草堂圖》由白悅家族所遞藏,但帝王的天下不會(huì)萬(wàn)世一統(tǒng),士大夫家也很少有“五世其昌”,因此所藏之畫(huà)不能保證數(shù)十年、百余年不易主。在明末清初,社會(huì)動(dòng)蕩不安的情境下,民間鑒藏家大力搜求流落各地的名跡,其中包含許多貳臣從明末就開(kāi)始搜尋,收藏情況逐漸從分散的鑒藏家歸入到幾家巨富之手。
關(guān)于《洛原草堂圖》的收藏情況可以從畫(huà)上的收藏印和鑒藏寶璽中尋出端倪。“蕉林書(shū)屋”“蒼巖子”“蕉林鑒定”“梁清標(biāo)印”“河北棠村”“冶溪漁隱”“秋碧”“蒼巖”這些印都是梁清標(biāo)的收藏印,由此可見(jiàn)此畫(huà)曾在梁清標(biāo)的手上收藏。梁清標(biāo)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藏書(shū)家,字玉立,一字蒼巖,號(hào)棠村,一號(hào)蕉林,名列“貳臣傳”。明朝滅亡后,清順治元年降清,補(bǔ)原官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累遷禮部侍郎。由梁清標(biāo)收藏的繪畫(huà)作品多為重量級(jí)的稀世珍寶,且數(shù)量非常之大。不過(guò)在梁清標(biāo)逝世后,他的藏品就開(kāi)始流出,后來(lái)大部分進(jìn)入清內(nèi)府,收入乾隆時(shí)期編纂的《石渠寶笈》。據(jù)楊仁愷《國(guó)寶沉浮錄》記載,清宮所藏書(shū)畫(huà)到了乾隆九年二月開(kāi)始進(jìn)行第一次鑒別整理,編成《石渠寶笈》,主要負(fù)責(zé)的官員有張照,梁詩(shī)正,董邦達(dá)諸人。張照正是《洛原草堂圖》最后一位題跋者,他的題跋與前人不同,他考證了此圖為文徵明真跡,提到此畫(huà)曾經(jīng)梁相公鑒定。另外數(shù)方是勵(lì)宗萬(wàn)的收藏印,勵(lì)宗萬(wàn)字滋大,號(hào)依園,又號(hào)竹溪。康熙六十年進(jìn)士,歷官刑部侍郎,以畫(huà)侍奉內(nèi)廷,同張照齊名,稱(chēng)“南張北勵(lì)”。此名跡中他的收藏印分別為“臣宗萬(wàn)”“教忠堂”“衣園居士”“子孫寶之”“衣園審定”“衣園”“衣園珍藏”“竹溪居士”“滋大”“雙清閣書(shū)畫(huà)章”“雙清鑒賞珍藏”“衣園滋大”“竹溪逸史”“竹溪”“竹溪秘玩”。
鑒藏寶璽有”“乾隆御覽之寶”“乾隆鑒賞”“石渠寶笈”“石渠定鑒”“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寧壽宮續(xù)人石渠寶笈”“樂(lè)壽堂鑒藏寶”“寶笈重編”“嘉慶御覽之寶”“無(wú)逸齋精鑒璽”和“宣統(tǒng)御覽”。從這些御印中的我們可得知,此畫(huà)在乾隆時(shí)期第二次鑒定整理書(shū)畫(huà)時(shí)著于《石渠寶笈續(xù)編》,后來(lái)經(jīng)嘉慶遞藏,加蓋了“嘉慶御覽之寶”。“無(wú)逸齋精鑒璽”和“宣統(tǒng)御覽”是末代皇帝溥儀的鑒藏印,他在“小皇宮”當(dāng)皇帝時(shí),曾經(jīng)盤(pán)點(diǎn)過(guò)一次清內(nèi)府的藏品,加蓋了此兩方印。
末代皇帝溥儀退位后,利用“清室優(yōu)待條件”的庇護(hù),在北京“閉上家門(mén)作皇帝”,做出了監(jiān)守自盜的事情。根據(jù)溥儀提供的材料,他們把宮中最值錢(qián)的字畫(huà)和古籍,以他賞溥杰為名,盜運(yùn)出宮外,存放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溥儀在被趕出清官后,逃到天津,后又從天津出走,和他的全班人馬進(jìn)入長(zhǎng)春偽宮,這些盜出的書(shū)畫(huà)通過(guò)日本特務(wù)人員運(yùn)到長(zhǎng)春偽宮,存放在一棟毫不起眼的小白樓里。抗日戰(zhàn)爭(zhēng)勝利,日本宣布無(wú)條件投降,偽宮內(nèi)部紊亂,溥儀倉(cāng)皇逃走,除了帶走的百余件書(shū)法名畫(huà),剩下的千件被當(dāng)時(shí)接管皇宮警衛(wèi)的“國(guó)兵”搶劫一空,這幅《洛原草堂圖》就在這場(chǎng)洗劫中流人“國(guó)兵”金香蕙手中,后來(lái)存放在劉賢國(guó)處。后來(lái),劉賢國(guó)在東北文化部工作人員的多次說(shuō)服下,終于將此件作品交給了原東北博物館,其后上調(diào)至北京故宮博物院[3]。
三、《洛原草堂圖》的功能性及其藝術(shù)價(jià)值
文徵明的《洛原草堂圖》單從畫(huà)面內(nèi)容上看,近似于書(shū)齋圖,但整體分析,屬于別號(hào)圖。傳統(tǒng)的書(shū)齋圖有詩(shī)文或者題跋,這些詩(shī)文和題跋都是以畫(huà)為中心,然而通觀《洛原草堂圖》后的題跋,除了最后清代書(shū)畫(huà)目錄整理者、藏書(shū)家張照在跋文中評(píng)價(jià)了文徵明的書(shū)畫(huà)“秀逸淳古”,其他人的題記都僅是圍繞白悅的別號(hào)“洛原”展開(kāi),未提及文徵明的《洛原草堂圖》和他所撰寫(xiě)的《洛原記》。由此可見(jiàn),此圖不單是對(duì)自然景觀的描繪,供他人賞悅的一幅畫(huà),它更大的作用是通過(guò)白悅友人的賦詩(shī)和題記,加上文徵明的圖文,共同解釋白悅別號(hào)的寓意,塑造白悅的形象,是白悅名揚(yáng)聲譽(yù)的一個(gè)媒介。
從《洛原草堂圖》的鑒藏印和收藏者身份來(lái)看,此圖的歷史地位和藝術(shù)價(jià)值都是極高的。吳門(mén)畫(huà)派的中堅(jiān)力量文徵明的作品在當(dāng)時(shí)需求量極高,有很多繪畫(huà)作品都是由文徵明的子弟代筆,根據(jù)資料記載,此圖經(jīng)徐邦達(dá)、楊仁愷等人考證為真跡,保存的也非常完整,具有極高的藝術(shù)價(jià)值。進(jìn)入清內(nèi)府后,編入《石渠寶笈續(xù)編》,乾隆將其視為上等品,加鈐“乾隆御賞”“宜子孫”和“三希堂精鑒璽”。這張畫(huà)里有太多的內(nèi)容值得挖掘,它見(jiàn)證了白悅的一生,反映了文徵明與白悅的交際,友人的題跋成為重要的歷史文獻(xiàn)。從明代覆滅,清初流人宮中,在清朝末代皇帝退位后又被偷盜出宮,幾經(jīng)輾轉(zhuǎn),現(xiàn)在完好無(wú)缺地展現(xiàn)在世人的眼前,可謂極其可貴。
參考文獻(xiàn):
[1] 江西美術(shù)出版社編.石渠寶笈名人卷·文徵明[M].江西:江西美術(shù)出版社,2017:30.
[2] 李家治.文徵明[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60.
[3]楊仁愷.國(guó)寶沉浮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35 - 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