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邊樓”和薛濤詩
何青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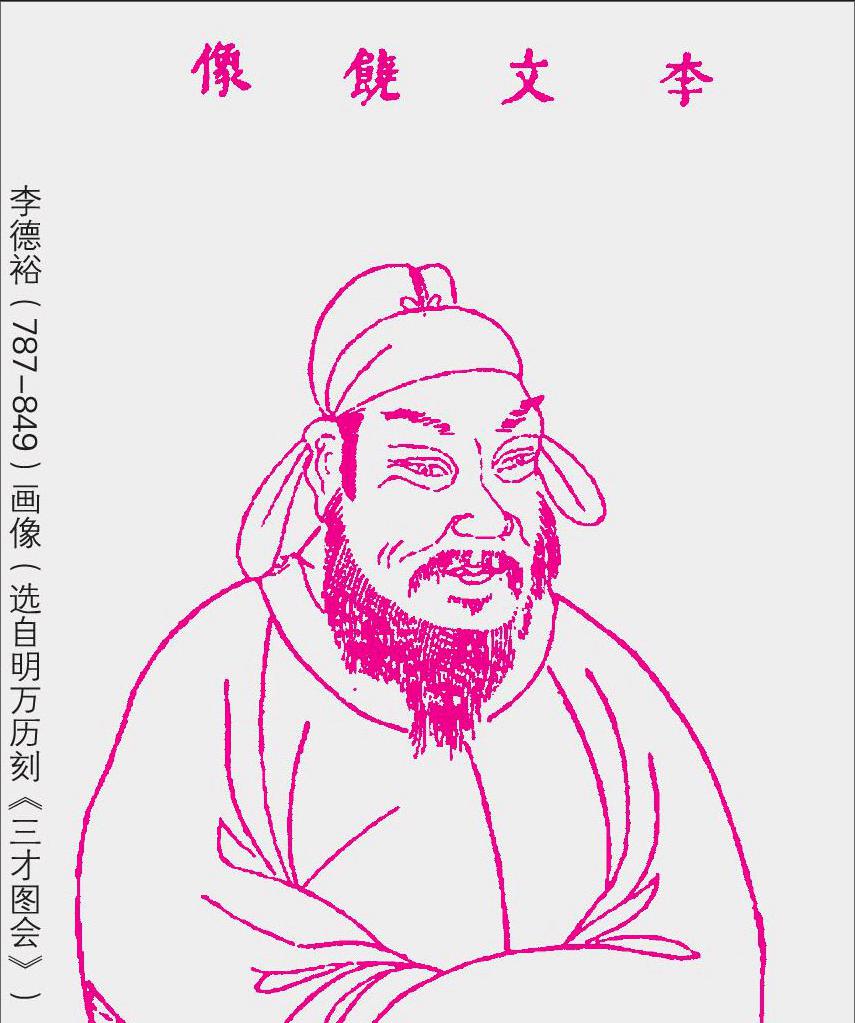
理縣薛城,在岷江上游一大支流雜谷腦河與孟屯河交匯處。它歸屬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管轄,歷來是藏、羌、漢族雜居之地。雜谷腦河與孟屯河在這里合流后便東向匯入岷江。
“籌邊樓”修建在兩河交匯的河谷邊,這是一座木框架抬梁穿榫結構、有典型的漢民族殿堂風格(重檐歇山式)的二層閣樓,通高18.5米。樓的基座狀似一座城堡,堡壘上再建閣樓,在河谷側畔尤顯挺立壯觀。樓的周邊群山環繞,有狀似筆架之筆架山,有山頂尖似熊耳的熊耳山,還有大、小岐山以及南溝后山,真個是環樓皆山也。
樓的附近,還修建有一些配套建筑,如回廊、雨亭和陳列圖片資料的展廳。當地主管部門力求把“籌邊樓”及周邊環境打造成一個整體的旅游景點。目前,“籌邊樓”對外開放,免費參觀,是當地民眾和外來游客憑吊古人、休閑觀光的一個典雅清靜去處。順著城堡石砌步梯就可登臨“籌邊樓”頂層。如果憑欄四望,四周皆是險峰危巖,遮斷云天。
樓閣內供奉有“籌邊樓”的唐代初建者——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的塑像,供人瞻仰。園內陳列室還有文字介紹他修建“籌邊樓”的詳細情況,特別是引證了唐代女詩人薛濤詠“籌邊樓”之詩,確證此樓建造精美,歷史悠久,是邊陲民族和睦團結的象征。
歷史上薛城是邊陲之地,特別是到唐王朝時期岷江上游之松茂地區全部為吐蕃民族武力占據。唐王朝鞭長莫及,控制不了這些地方。因此,其時西川節度使顯然不會遠離治所成都,跑到薛城前線來修造“籌邊樓”的。不過,當時,蜀中著名詩人薛濤倒確實有一首題作《籌邊樓》的詩來評說“籌邊樓”。詩云:
平臨云鳥八窗秋,壯壓西川四十州。
諸將莫貪羌族馬,最高層處見邊頭。
這首詩看似明白淺顯,但實際寓意相當深刻。詩句一開頭就描寫閣樓的雄偉壯觀,其高度可及白云飛鳥;而也只有這樣高大壯美的空間狀態,才可能控扼西蜀局面(時劍南道有州三十八,縣百八十九。這里“四十州”,乃舉其成數言之)。當時,女詩人對當局修造“籌邊樓”的舉措十分理解。她深諳李德裕“持重安邊”的深遠意義,告誡“諸將莫貪羌族馬”,不可貪立戰功,更不要貪婪地掠奪吐蕃人民,輕易地挑起戰爭。只有這樣,才能切實保持邊境的穩定和平安。這其實是對先前邊將目光短淺,輕啟戰端的沉痛回憶與反省。詩的末句“最高層處見邊頭”,其“邊頭”當指岷江上游的松茂前線,自然包括了薛城地區。這一句有著重大的警示意義,提醒諸將:此處是戰爭最有可能發生的邊境之地,是吐蕃最有可能進入成都平原的關口地帶,切不可對其掉以輕心。薛濤這首《籌邊樓》詩,情真意切,充分顯示出她不是一個只知道吟詠風花雪月,奉答應酬的“樂妓”,而是一個熟知政治、深諳國事民情的杰出人才。這首詩音韻平仄規范,讀來瑯瑯上口,看似平常,卻是撫時感事,憂患元元,一腔愛國愛民正氣,令人感慨系之。而該詩直呼“諸將”的語氣,已沒有早年那種唱合或奉答之作的謙恭,而顯出飽經歲月滄桑的凜然大氣、硬朗風骨。資料顯示,女詩人在公元832年的夏天去世,享年63歲(《蜀箋譜》謂其卒時年七十三)。《籌邊樓》詩應是其去世前夕之作,確切說是在李德裕劍南西川節度使任內或剛離任時之作。李德裕出身官宦世家,是唐憲宗時宰相李吉甫之子,入蜀前曾官至御史中丞,后因受政敵排擠,先是外放為浙西觀察使,旋為義成節度使,文宗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入成都為西川節度使。他到成都后,認為“今瘢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遂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眾寡,饋遠邇,曲折咸具。乃招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新唐書·李德裕列傳》)可見這“籌邊樓”乃是一座作為西川節度使的李德裕展示邊防布局,與軍將、僚屬商議邊防大事的參謀部,決策、指揮中心,是西川抗擊吐蕃的軍機要地。這樣一個軍事中樞、決策要地,是不可能直接置于戰役最前線的。那樣太冒險了。
清同治五年《直隸理番廳志》說,李德裕曾在維州(治今理縣薛城鎮)建籌邊樓,或是誤傳。因其時地屬吐蕃,李德裕短暫收復維州(旋復歸吐蕃),是籌邊樓建成之后的事。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的有關專家依據新舊《唐書》《資治通鑒》及陸游筆記,認為李德裕初到任,即在成都西川節度使府署附近建“籌邊樓”。《成都城坊古跡考》說節署在今四川科技館東一帶(參見該書第291頁,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成都時代出版社2006年版)。這就是說,薛濤所詠贊的樓閣其實就是成都節署附近的這座“籌邊樓”。它與今天理縣薛城古鎮的“籌邊樓”在修建時間、地點和規模上都不相同。
那么,薛城這座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查資料顯示: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雜谷腦河、孟屯河洪水泛濫,沖毀了整個薛城古鎮。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當時的保縣(現汶川縣)知縣陳克繩才重修了整個古鎮及周邊建筑。南溝邊這座“籌邊樓”或有可能就在此時托名仿建。
有清一代,為了地方經濟的繁榮,祈求文風之倡盛,往往托名仿建古跡。當時的地方官場,鄉紳、大戶們相互炫耀、攀比,成為一時風氣。光緒十五年(1889年),成都錦江之畔的玉女津起造高樓“崇麗閣”(俗呼“望江樓”),也是這樣自然地和女詩人薛濤扯上了關系。薛城之“籌邊樓”應是當地民眾仰慕前賢、尊重文化和歷史的產物。而在藏羌漢多民族雜居的薛城能夠托唐代之名重起“籌邊樓”,則無疑反映出這個民族雜居地區的人民對和平、安寧與幸福生活的向往與渴望。薛城的“籌邊樓”建造距今已有二百七十多年,雖歷經歲月的洗禮,仍舊巍然屹立(2005年,國家按照“修舊如舊”原則,進行過一次保護性維修)。它本身就是一篇頗具歷史分量和人文情懷的史詩,值得后人細細品讀。
去年我曾游走在雜谷腦河畔寫生,再次登臨過“籌邊樓”。當時對岸熊耳山下穿山隧道正加緊施工,河谷中不時傳來低沉的作業轟鳴聲。黃昏時節,我匆匆畫出殘照中巋然挺立的“籌邊樓”(見封二彩圖)。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