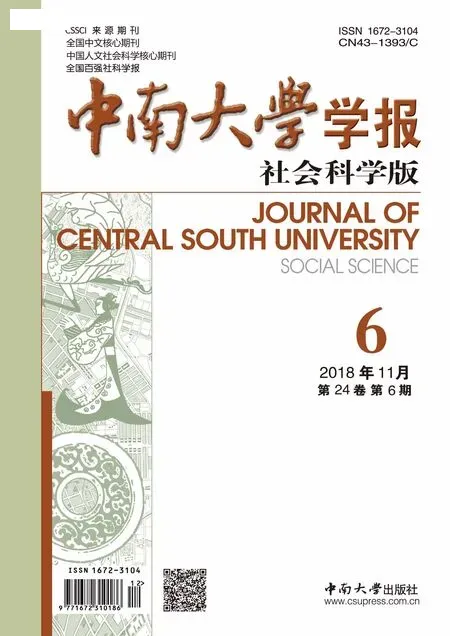邊緣人的聲音:《饑餓的女兒》與《紫色》的女性身份構建
(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重慶,400715)
虹影的《饑餓的女兒》與艾麗斯·沃克(Alice Walker)的《紫色》是表現女性角色身份構建的中美當代女性主義成長題材小說,兩部小說都表現出饑餓寫作的意識:微觀層面上,主人公飽受因階級、膚色、性別、畸形的出身背景而帶來的憎惡和歧視,日積月累,形成生理與精神饑餓;宏觀層面上,個人的饑餓與國家、民族的劫難緊密相關。由此,私人化的家庭敘事空間延展到了家國背景,饑餓表達與救贖可被理解為邊緣人身份的構建。同時,兩部作品都試圖創造出帶有理想色彩的新女性形象,她們通過表達女性欲望和個體生態訴求為邊緣人發聲。《饑餓的女兒》和《紫色》都著墨于女主人公對自身身體與身份的思考。提倡性別述行理論的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認為“‘身體’絕非僅僅是生理層面的血肉之軀,也是同樣受權力話語鉗制,在內外壓迫中成形的社會概念”[1](76);埃萊娜·西蘇(Hélène Cixous)嘗試從女性主義角度解釋女性作家的寫作,故而提出“書寫女性身體,女性用身體書寫”[2](26)的主張,強調女性身體書寫具有雜糅性、流動性、多義性。在《紫色》一書中,艾麗斯·沃克結合婦女身體與身份的物質性和話語性塑造出女性真我,比如以一群獨立的黑人女性取代傳統文本中男性父權代表作為啟蒙者形象;再比如,將同為工業男權社會從屬物的自然和女性聯系到一起,創造出萬物平等、性別平等的泛神世界。而虹影則在自傳體小說《饑餓的女兒》中直接勾勒出少女對身體與身份的困惑、憤怒與激情。此類身份思考,盡管多以質疑、反叛、挑戰、沖突等方式展開,但其目的不在于讓男性淪為他者、女性成為獨裁者,而在于讓女性重返自己的身體,重塑自己的身份,畢竟舊有的身體場所是父權所定義、壓制下的表達空間。她們的寫作不僅討論女性處境,還在探索身份的同時引入了族群關懷和尋根意識。
一、饑餓表達:邊緣人身份構建
社會身份的概念被簡·斯崔克(Jane Stets)和皮特·巴特(Peter Burke)定義為“個人在不同社會活動中扮演的不同角色”[3](228)。也就是說,身份會發生變更,而“自我”作為多重身份的疊加與重組,是通過身份交替得以體現的。換言之,身份的流動性決定了身份構建必須多元且具有一定的變化。因此,身份之構建并不等同于身份堆積的結果,而是包含建構、解構、重構在內的動態過程。在《饑餓的女兒》和《紫色》的文本中,表面的身份構建表現為女性群體對自身認知的改變;內在的身份構建則表現為女性人物對文化、歷史、民族等一系列微觀政治符號的探索,具體表現為她們追尋身世,擁有旺盛的求知欲,甚至質疑自我與他人存在的意義。虹影和沃克從“饑餓”入手來構建身份,包括生理饑餓、精神饑餓、性與愛的饑餓,從而挖掘出邊緣人的痛苦。
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并未誕生過獨立的女權革命。女性主義作為一門學說被介紹到我國,其中就包括沃克實踐的黑人女性主義(Black Feminism)和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虹影作為英籍華人女作家受到女性主義的感召,但是《饑餓的女兒》是基于個人生命體驗的獨立創作,因此,這部小說中的女性意識是潛性的、朦朧的,卻也直觀表達出最為迫切的女性訴求。《饑餓的女兒》以主人公六六的成長故事喚醒大眾關注歷史中的性別文化,特別是“文革”以后邊緣人文化的殘缺。盡管虹影在《饑餓的女兒》里提及諸如“出走”“身體”“看不見的父親”等傳統西方女權話語,但作品更多的是藝術地還原了中國父權制和儒家文化對底層人的權力滲透,即她在沉默中爆發出一個當代弱女子的饑餓怒吼。
六六出生于后饑荒時代(1962年)的重慶南岸貧民區,“饑餓”如同基因一樣被刻印在她的血肉里。她出生時便因為遇上青黃不接的全國大饑荒而發育不良,后來又因為食物短缺而身材瘦小,雖好食肥肉,卻如何都胖不起來。生理饑餓似燈光下膨脹的影子,六六平日里全靠忍耐度日,然而長期營養不良的身體生出“逃離饑餓”的欲望,于是她進行了嘗試:要了兩個大肉包當作十八歲生日禮物,借與歷史老師隱秘的親密行為宣泄積攢了十八年的激情。事實上,母親把“大肉包”污蔑為“死人肉餡填塞的包子”,并被勒令扔掉;六六對歷史老師無望的愛在書中被解釋為“原本只是同病相憐”[4](219)。自此,逃離生理饑餓宣告失敗。與此同時,她意識到精神世界的荒蕪或許才是導致饑餓的根本原因。六六在全家反對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學習,反映了她渴望社交、渴望外面世界的心理。在小說的后半部分,六六的私生女身份被證實,文本也因此回歸身份思考的原命題——“我是誰”。
“我是誰”被禁錮在生理和精神的束縛中,精神饑餓是生理饑餓的根源,生理饑餓則是精神饑餓的延續。“非婚子女”“女性”“下等人”等標簽綁縛著她,內心的叛逆和外部強加身份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導致結尾處六六毅然出走。然而,“出走”不是將過去種種拋之腦后,而是源于“自己患上了弱者才有的逃離病”[4](227)。此時的二度逃離是為了逃離精神饑餓,而精神饑餓被虹影置換為“一種精神病癥”,通過“出走”這一病理表現,六六將多重身份統一為“我是我”。如瘋如魔的病患形象是作者對自我本質的認知,經由寫作而成為擺脫權力約束的性與愛的欲望化身,即該角色表達出女性(無論是何種身份)被壓抑的欲望訴求——不為人知,也無法被男權解讀。此處的“性”不是指她對與異性接觸的渴望,而是對自我身體、性別、性需求的了解欲。由于營養不良,六六的第二性征并不明顯,全無二元論標準下的女性美感。但她樂于審視身體,并關注家中其他女性的身體。最終出現在文本中的是他者對他者、女性對女性凝視下真實的胴體——多次生育的母親,“乳房如干癟的布袋,腰臀因為常年工作已變形,手腳卻像個男人”[4](93),病態的自己“蒼白,消瘦,嘴唇無血色”[4](94)。除此之外,母親的逃婚、出軌以及六六的通奸、墮胎都因為復雜而合理的緣由在故事中呈現為一種女性處于弱勢地位時理所當然或被逼無奈的舉動。盡管這些是男權社會中的婦女悲劇,但也是女性逃離婚姻、生育、家庭的方式,歸根到底,是短暫逃離“饑餓”的手段。正如生理饑餓來自精神饑餓,性欲望也來自愛欲望。愛欲望不僅是尋求情感的完滿或彌補童年與少年的家庭缺憾,也是求知、求同、求理想的實現。六六的結局是離開家鄉后再度回到家庭,短暫停留后又一次離開。虹影并未說明六六的饑餓是否得以解決,但她卻表示“文本自身便能拯救生來饑餓的心靈”[4](322)。更泛化地說,《饑餓的女兒》就是解救饑餓女性的方法,因為它傾訴出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生理饑餓與精神饑餓的現實,表達了女性的性欲和愛欲,回應了饑荒年代以及在此之前的女性饑餓感。
《紫色》中的饑餓概念除開物質上的貧窮與精神上的焦慮,還包括因膚色和種族而產生的困惑。有別于《饑餓的女兒》混沌狀態女性意識的表達,沃克在撰寫《紫色》前已明確提出婦女主義(womanism)這一主張。她認為:“婦女主義者有別于女權主義者,專指有色人種女性主義擁護人士,也指潑辣、敢做敢當,充滿好勝心和行動力的黑人女性。”[5](407)在酷兒文化里,“紫色”本來象征女性私處和同性戀愛,但在沃克的表達中,“紫色”被作為婦女主義的代表色[5](408),寄托了解決兩性沖突和化解種族矛盾的愿景。《紫色》中的女性人物困于黑人父權的束縛,后者一方面認為白人的種族剝削十惡不赦,另一方面又模仿白人父權制對女性進行壓榨,以此為自己獲得無實際作用的“權威”,即使“權威”的獲取方式只是毫無人性地打罵、強奸、買賣家庭中的婦女和兒童。“家庭”在文本中喻指施暴場所,家庭中的女性作為生育承受者和勞動承擔者以及被施虐對象,茍活于父權和種族的雙重陰影之下。
女性被要求常年累月地隱忍和服從,盡管這種父權標準一開始屬于強制性思想灌輸,但到后期,已經被內化為女性主動接受的價值輸入和集體記憶,因此西麗已默認從屬身份并試圖將既有價值觀傳遞給下一代。例如,當繼子向西麗抱怨自己無法管好老婆時,經歷過繼父和丈夫家暴的西麗建議繼子采用毆打的方式來馴服兒媳。但當西麗給出建議時又深感不安,并在致上帝的信里懺悔自己的言行。此時的西麗處于渾渾噩噩的失語狀態,她無從表達亦不知如何表達。但隨著朋友對她的啟蒙,之前所感知到的難以名狀的不安在獨立意識覺醒的過程中尋找到了發泄口——不安源于自己所處的邊緣位置。西麗意識到“我非我”,所謂的“我”只是父權制思想捏造的理想女性奴隸,這樣的奴隸身份不僅源自白人至上的奴隸制度和殖民主義,還源于男性給女性貼上的工具標簽,即女性被規訓為失聲的勞作者和生育機器。而男性作為“主人”,有權交易自己的女兒或妻子。“我非我”是一種饑餓表達,或者說,饑餓是自我認知的表現。因為生理饑餓,西麗希望賺錢補貼家用,而在賺錢時察覺到黑皮膚女人也可以走出家庭;因為精神饑餓,西麗偷偷摸摸地讀書寫信,從而加入了真誠、自愛的女性社群;因為性和愛的饑餓,西麗和莎格墜入同性戀愛,建構了女性在經濟、感情、身體上彼此獨立又互助的親密關系。
“紫色”意指全新的西麗,也象征為達成平等有愛的男女關系而進行的溫柔變革,有別于推崇暴力反抗。沃克將黑人女性的主體性放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進行討論,嘗試走出單維的抗議表達,從而獲取更開放的女性視角。饑餓促使西麗跨越“邊緣”和“中心”的邊界,尋找到完整性,并成為破壁者。邊緣感產生于對身份的模糊認知,西麗的三重身份——美國人、黑人、女人——彼此之間的欲望需求可能互相隔絕甚至沖突。這樣的矛盾要求美國黑人婦女在內部群體中尋求身份認同以便形成自我,于是,通過姐妹互助傳遞的女性對女性的啟蒙,成為身份轉換的關鍵,并賦予了她們挑戰的勇氣。單一社群的獨立王國看似自由,但是其神秘和抽象的本質仍未逃脫被他者化的宿命,因此讓黑人婦女從容走進現實勢在必行。沃克在堅定自我立場的基礎上,主張采用淡化政治意識、突顯人性復雜性、剖析群體的潛在話語等途徑在小說層面解決饑餓問題,由此可以推理出:《紫色》旨在強調性別、階級、種族、信仰的融合而非割裂。綜合來看,《紫色》著重描寫黑人婦女性別與種族層面的三重饑餓,可被細化為因食不果腹和挨打受累而產生的生理饑餓,因追求知識和追求獨立而產生的精神饑餓,其中“追求獨立”意指書寫一部純粹的黑人女性崛起史,以及因尋找平等而產生的性與愛的饑餓。
二、饑餓拯救:邊緣人身份強化
《饑餓的女兒》《紫色》這兩部小說均以成長故事為依托,對具體時代、地域背景下的女性群體進行身份構建。《饑餓的女兒》并非僅僅刻畫女兒(六六)的饑餓,而是借一個女孩的自我身份思考來追溯民族的饑餓記憶。《饑餓的女兒》在顯性層面詳敘了“無法維持生計的貧民現實生活,并以此鋪展開家國大事的潛文本”[6](2)。六六一家的相逢與離別,記錄了她們如何從國共內戰走到“大躍進”,又是如何從大饑荒過渡到“文革”,最后走向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由此,饑餓表達不再局限于女性欲望,而是人的自我拯救。六六本就是饑餓的化身,置于小家層面,她代表在尷尬境地中無法自救的一家人,她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忍受,繼而泄憤,然后麻木,最后又回歸到忍受狀態;置于國民層面,當饑荒降臨時,吃成為頭等大事,卻又因為物質資源匱乏和家人流散,人的精神上的創傷再度加深,陷入情感荒蕪和安全感缺乏的境地。規則、尊嚴消失,謊言、私欲盛行,饑餓讓人們舍棄曾經被奉為圭臬的倫理道德。西麗的饑餓屬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生活在美國南方保守鄉村的黑人女性,彼時她們整日操勞并忍受著白人的種族歧視和黑人男性的性別壓迫。而第一次女權主義運動中涌現的諸多權益主張僅僅關注受教育的中產階級白人婦女,并未惠及黑人女性。《紫色》的創作背景則是20世紀70年代,受第三次女權主義運動、黑人運動和生態運動的影響,《紫色》不僅揭露困境,呼吁改變,還借西麗的人生故事理性地還原了誕生于 20世紀初的下層黑人婦女如何走向新生,以此啟發當下的黑人女權思考。
饑餓代表被壓抑的食欲、色欲、權欲、渴望、追求等,呈現為因吞食無用的“精神食糧”而產生的苦悶心理,以及為尋找另種物質或非物質的食糧而產生的反叛行為。為解決“大躍進”及“文革”期間的危機,誕生了諸如樣板戲這樣政治意味強烈、美感單調、思想浮夸的文化產物,而這類原本用以填補心靈的文化食糧反而因為不切實際和過于強權而對國民形成精神高壓,讓人陷入因飽受挫折而更加壓抑的窘境。活下去的本能和活不下去的現實喚醒了饑餓感,也驅使人逃離多重饑餓,構成了《饑餓的女兒》“圍困→逃離→回歸→再次出走”的敘事邏輯。與之相似,《圣經》和傳統美德無法解救20世紀初的美國黑人婦女,并將她們拋入自暴自棄的境地。以西麗為例,她在小說開頭默認自己的商品屬性,保持沉默,畢竟順從才是黑人家庭婦女的美德,因此她把《圣經》名言“在患難中要忍耐”奉為真理。但忍耐并未給予她回報,相反,強化了一種自我認知——過于軟弱,無法與夫權、父權相抗衡。由此可知,女性身份的定位一直存在,但當民族記憶與其定義和自我定義產生沖突時,定位則顯得飄忽不定。受外界影響,對定位的妥協態度或逆反心理轉變為饑餓感。即便身體饑餓得到滿足,精神饑餓的創傷卻難以彌合,這就導致人處于后饑荒狀態,即超我為本我讓步,肉體歡愉取代食物來填飽口腹,秩序或將消亡,狂躁抑郁的官能感受主宰個體行為。這與父權文本反復刻畫的歇斯底里的女性氣質不謀而合。當顯性和隱性的反叛行為、身份煩惱、時代困局一致時,女性的顛覆性言說,譬如“神經質”和“情緒化”的表達,一方面可以洗凈男權對女權的污名,另一方面足以沖擊男權理性規范,并指明是什么創造了男權邏輯,為人們走出饑餓提供解決之道。因此,婦女在苦難背景下已經被潛移默化為“與饑餓、文學政治、身體政治、革命相關聯的群體”[7](241)。
饑餓給予六六和西麗的啟示是不一樣的。對前者而言,正是意識到饑餓,才需要逃離饑餓,所以逃離心態在開篇便顯示出來,而之后的文本是追溯六六為何迫切想離開原生環境,這才引出對三重饑餓的具體描述。對后者來說,西麗在接受啟蒙后才意識到自己的饑餓,并以此為轉折點,在后續敘事中塑造獨立的性別身份。兩者的差異與中美同主題小說的歷史、文化背景有直接關系,《饑餓的女兒》描繪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饑荒年代,其物質水平之低下和全民情緒之恐慌是《紫色》難以相提并論的,這樣的背景促使六六逃離。再看《紫色》所表現的20世紀初期美國社會對黑人婦女的身份的異常敏感,長期以來的貧困與暴力讓女主人公怯于表達,因此西麗對饑餓的認知是無聲的、滯后的、片段式的。兩位主人公逃離饑餓的方式卻大相徑庭,六六逃離的初衷是遠離政治文化氛圍進而成為完整的人,所以她從內部走向外部,此外,表露饑餓亦是表達對整個時代宣傳的失望和指責,但不見得是批判某一階層或具體人物;西麗踐行從外到內的逃離途徑,并不向主流觀點過分靠攏,而是追溯民族傳統,形成獨特話語體系,建立平等的對話關系,這就避免了被男人或白人代言的可能,也有利于黑人婦女走出邊緣區。
三、父權祛魅:女性欲望言說
欲望與身份、物質、本能相關聯,在文學作品中成為一種敘事角度。但有別于單純停留在“肉身顛覆終極意義”[8](304)的純欲望表達,或“以個體經驗反撥宏大敘事”[9](25)的激進寫作方式,《饑餓的女兒》和《紫色》將欲望看作身份思考的線索,并考察各種泛政治概念與社會制度中的女性欲望。六六和西麗作為欲望言說的主體,借欲望表達進行著政治實踐和批判反思。我們姑且將兩部小說中的欲望表達分為生理和精神兩大方面,其中生理欲望主要反映女性個體或群體的生命體驗,展現為大篇幅且細致的性器官(子宮、乳房)審視和性經歷描寫,被遮蔽的女性原欲也就在文本中顯山露水;精神欲望側重于強調成長過程中女性意識的萌發、蛻變和定型,以及影響她們欲望表達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解構父權神話,創造女性文化,回歸母權話語。下文將探討兩部小說中關于父權祛魅和女性親密關系塑造的欲望表達。
傳統父權文本傾向于將人默認為男人,女性隱身在字里行間,要么超脫為無情無欲被神圣化的“圣女”,要么墮落為多情多欲被動物化的“欲女”,要么成為只擁有單一情感的“惡女”“怨女”“癡女”等。總之,現實女性在父權神話書寫模式中被排除在文本之外。女性欲望表達旨在顛覆神話,撕碎偽裝,摧毀附著于女性的父權話語,于是,《饑餓的女兒》和《紫色》通過“無父→尋父→弒父→與父親和解”的書寫路線祛魅父權。
孤兒意識根植在六六內心,她終日掙扎于“無父”狀態。結合六六的身世看,生父和母親的婚外情帶給她恥辱,養父與她保持著陌生人般的距離,歷史老師這個心理上的父親以自殺的方式與她告別,三位“父親”均加深了六六的心靈創傷。而在六六的理解中,父親的缺席導致她失去庇護,遭受凌辱,于是開啟了“尋父”的旅途。“尋父”的目的不完全是為了彌合“無父”的創傷,也是為了彰顯她的欲望,所以六六所尋的并非血緣層面的父親,而是精神父親,確切地說是能平息其內心恐懼的“父親”。生父是六六回答“我是誰”問題的關鍵,十八歲生日當天的父女相見使她了解了自身精神焦慮的根本原因,完成了形式上的身世探尋。歷史老師是六六的秘密情人,同時也是六六潛意識中的父親替代人。換句話說,歷史老師在與六六的親密關系里存在著被凝視、被估價的嫌疑,在戀父情結的作用下,后者視前者為“救命稻草”[4](168)。相對于后者而言,前者只是被動的傾聽、安撫、親吻行為的施與者,從沒承認過情人或“父親”身份。隨著歷史老師毫無征兆地自殺,精神父親的形象土崩瓦解,六六重返“無父”困境,這意味著六六“尋父”的努力歸于徒勞,同時陷入另一極端——“弒父”。處于“無父”狀態時,六六曾聲嘶力竭說“讓親屬悲痛欲絕悔恨終生,我卻不給他們任何補救贖罪的機會”[4](72);遭遇歷史老師身亡后,她再次說“這個世界,本來就沒有父親”[4](224)。六六以宣判性話語對“父親”進行消解,呼應了弗洛伊德“弒父”理論闡釋的反權威精神[10](84)。精神父親作為男性權威的象征之一,在《饑餓的女兒》的前期欲望表達中發揮了引導功能。但伴隨“尋父”和“弒父”矛盾的加深,女性意識開始占上風,后期敘事逐漸消解父親權威,父親形象也得以重建。當六六重新回到家鄉,對著生父的墓碑,終于找尋到父與女最原始的親情關系,六六完成了實質性的身世探尋。
“父親”在《紫色》中既指社會概念上的父親也喻指上帝(天父)。西麗的生父原是一位安分守己的黑人商人,后因生意興隆遭到白人的仇視,被吊死在樹上,導致寡母弱女輾轉他鄉。為了養活一家人,西麗的母親改嫁給流氓阿方索,而這位繼父霸占財產,強奸繼女,又在西麗喪失生育能力后用以物換物的方式將她轉手給鰥夫。作為一名基督徒,為了擺脫“無父”的心理困擾,西麗向天父尋求幫助,委屈、愿望、憤怒等都借用書信告訴全知全能的上帝,并相信唯有遵循《圣經》的指引才能獲得慰藉。上帝的現實原型就是傳統上流白人家庭中的父權領袖,投射到西麗心中形成一個“白人老頭”的智慧形象。可是,和上帝同面孔的白種男人正是造成西麗悲劇的始作俑者。那么黑人男性是否能夠充當上帝?事實上,西麗蒙受的最大苦難恰恰來自自詡為黑人女人庇護神的黑人男人。繼父和丈夫掌控她的自由,甚至決定她的生死。因此,上帝既不是有著征服者、掠奪者、教化者面貌的白人男人,也不是信仰強權,言行粗暴,冷酷無情的黑人男人。“尋父”計劃宣告破產,寫完55封致上帝的書信之后,西麗意識到上帝并未予以回應,反倒“像認得的其他男人一樣:輕薄、健忘而卑鄙”[5](121)。西麗放棄追逐男性上帝,反而轉向女性親友尋求幫助,與女友們的通信讓西麗把改變命運的希望寄托于自身,并最終完成從樹狀態向人狀態的過渡。“弒父”的實質是西麗實現了自我價值,父權及上帝光暈的消失意味“弒父”行為的結束。此時,西麗揭開內心崇拜對象的真面目——上帝是自然界中一切光輝的體現。臨近尾聲,黑人男性也擺脫了種族及性別約束,丈夫主動要求重建平等的夫妻關系,自此,男權與女權之爭得以和解。
四、同一與分裂:女性關系塑造
父權神話遭祛魅,原定義的主客體關系被改寫,女性不再僅僅是他人欲望的俘虜。拉康提出假想:男人在進入男權世界時,以生理“陰莖”為犧牲交換到象征男權的“陽具”,因此,男人經歷了“殘缺”,而女性因為沒有“陰莖”,不必經歷犧牲、交換,所以女性更為適應無性別體系,且此體系無損女性氣質[11](164)。《饑餓的女兒》和《紫色》以女性親密關系為切入點,解構千百年來約定俗成的男女性別政治,發揮女性特質,主要表現為六六母女反叛精神的繼承和西麗與莎格的姐妹情誼。
母親是六六唯一的血親,六六對母親的天然依賴投射出近似“前世今生”的情緣,換言之,女兒是母親的過去而母親是女兒的將來。母親經歷過三次逃婚,分別是包辦婚姻、與袍哥的不對等婚姻、為了愛情的短暫出軌,演繹著為人妻、母、情人的角色,背負著整個家庭的經濟重擔和道德枷鎖。母親是饑餓的母體,并將饑餓從心理上與身體上傳遞給六六:母親作為大饑荒的親歷者,見證了親人的死亡、社會風尚的荒唐和國家的貧弱,生理饑餓和精神饑餓成為不可磨滅的傷痕;作為萬夫所指的偷情者,陷入無感情婚姻和有性愛情的矛盾漩渦,性和愛的饑餓讓她無法走出無物之陣。女兒繼承了母親的饑餓,也繼承了張揚的自我表達,卻也如同母親一樣陷入身份認知的困境。但不同的是,母親的解放具有局限性,三次逃離婚姻的目的都是為了追尋幸福,但尋找到幸福時她又縮回婚姻殼子,到頭來破罐破摔,屈服于父權的道德高標。而永恒饑餓伴隨著六六,她的自我不曾被生活的艱辛本質覆蓋,反而更為鎮定地表達欲望,以“尋父”和“弒父”的悖論來批判父權,進而與父母、饑餓、自我和解。“母親-女兒”是一切女性親密關系的根源,對虹影而言,女兒始于母親,終將歸于母親。
姐妹情的極端化體現是女性的同性戀情,是“對男權統治秩序的根本批判,是婦女組織的一種原則”[12](118)。《紫色》中的姐妹群體有著烏托邦式的友誼:毫無芥蒂,彼此信任,互相扶持。阿爾伯特的前妻莎格和現任妻子西麗走到了一起,她們從對方身上獲得關愛、尊重。在以姐妹情維系的親密關系里,莎格和西麗互為“信徒”和“上帝”,前者引導后者走出奴性怪圈,熱愛自己的身體,獲取性的歡愉,后者漸漸形成完整人格,并協助前者完成音樂夢想。異性關系中性與愛的缺失在同性關系里得到補償,進一步打造出堅不可摧的婦女聯盟,黑人下層女性基督徒們逐漸意識到“上帝”并非是形象單一的至高無上的拯救者,而是愛與美的平凡載體,是同伴、愛人、自立又自強的萬事萬物。
女性親密關系不僅顯現出不同女性角色的同一性,也反映了作者自身的身份分裂,恰如虹影的意識游離于母親和六六之間,或者如沃克將西麗和莎格均塑造為婦女主義的代言人。兩組角色一方隱忍、怯懦、卑躬屈膝(母親、西麗),另一方瘋狂、激憤、富有創造力和毀滅性(六六、莎格),同時雙方特質又存在轉換的可能。譬如母親宣稱家中無需男人,與六六控訴三個父親負了自己所表現出的推翻父權的沖動十分相似;再譬如西麗在故事后期咆哮著索取自己對身體和生活的支配權,只有確認要求得到保證后才變回往日溫柔形象,與莎格逃跑時義無反顧的傾覆性姿態一致。分裂體現作家所構建的女性身份的矛盾性,默認理性形象的背后潛藏著威脅與危機。
五、尊重與平衡:女性生態訴求
生態女性主義這一術語由法國作家弗朗索瓦·德·歐本納提出,她認為“女性所受剝削與自然所受壓迫有天然的直接的聯系”[13](319),其實質是將女性與自然放置到特定的語境當中,體現個體生命欲望探索與反思的過程。虹影借用長江確認六六的文化身份并彰顯生命力;沃克在《紫色》的前期敘事中通過男性對黑人女性的奴役、人類對自然生態的破壞概括出女性與自然共有的被動身份,在后期敘事中,女性走上獨立道路,而自然也恢復往日生機,投射出兩者之間共生共榮的特殊關系。兩位作家借用自然體現女性延續的生命思考、鄉土情結、民族情懷,并以此幫助構建人物身份。
《饑餓的女兒》英譯本題目為Daughter of The River,意為長江的女兒,長江在虹影的小說中無疑代表著母親。水近似永生概念,蒸騰化氣,氣冷騰云,云散降雨,雨落為水。由此可見,水是生命的起源也是生命的歸所,昭顯了虹影輪回式的母女觀。水的聚集體長江多以女性形象出現在小說中,生理方面,河道形似產道;精神方面,汛期旱期對應女性情感的悲歡離合。長江賦予人新生和重生的意義,一旦踏進長江,便是看天吃飯、看水行事,再不論舊有身份,而長江也對人類一視同仁。《饑餓的女兒》中母親前兩次逃婚都選擇沿江乘船從縣城奔到重慶,爾后每每望向長江都會思念故里,仿佛走進長江便是遠離塵世重回母體;六六則從長江母親處汲取女性之愛,當她孤獨無依時想象長江環繞著自己,當她揮灑激情時感到長江在頭頂蜿蜒激蕩。
長江在文本中還被賦予其他文化意義。一方面它是精神故鄉的縮影,無盡江水等同于無限回流的生命力,像極六六永不饜足的饑餓;另一方面它是混雜了個人訴求的文化想象,江水的循環往復與六六的徘徊不定是一致的,引導六六從寄宿原罪的家鄉/此岸去往充滿未知的遠方/彼岸,蘊含了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的尋根意識和西方宗教概念“原罪-救贖”。小說中,自然給予六六的歸屬感不局限于性別認知,而是對邊緣身份的包容和再塑,過程中反映出的焦慮也不僅是因為女性身份,還緣于作者作為饑餓兒童和跨文化個體對于平民和精英文化、東西方文化認知的深層矛盾。
沃克早期專注于黑人寫作,后期受生態女性主義影響,轉而在作品中融入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辯證思考,并得出父權制是女性、自然、有色人種的牢籠的結論。《紫色》正是這一思考的產物。《紫色》講述的不僅是一位下層黑人婦女的獨立史,也是違背自然規律發展的鄉村毀滅史。在敘事方面,隨著情節推動,西麗從性別覺醒走向思想徹悟,贏得了平等和尊嚴。反觀另一條敘事線索,小說開頭繁榮的非洲農村因為歐洲殖民者的野心,過度負擔種植業,最后陷入絕望。兩條敘事線索相交織,警告世人,人類必須尊重自然,正如男性必須平等對待女性一樣。在符號方面,以樹木為例,西麗被繼父強奸后自喻為木頭,并將身體被侵犯之苦痛類比為樹木被砍伐之痛楚。通過擬人化描寫,樹與西麗一樣經歷了變化:從干枯瘦弱的垂死形象發展為嫩芽滿枝的新生形象,對應了主人公由依附到獨立、由壓抑到自由、由悲觀到樂觀的變化。樹與女主人公的關系折射出作者的理念,即熱愛自然會讓女性變得無所畏懼,凸顯了女性與自然聯盟的必要。
沃克認為自然與黑人族群也有著特殊的羈絆。西麗吟唱的布魯斯(blues)被稱為黑人文化的靈魂體現,它代替具體言說,成為黑人女性特殊的情感表達。西麗的夢想家園是一棟樹林里的圓房子,其雛形來自非洲黑人的建房習慣,與象征規章、律法的“方”相對的“圓”代表同等、和諧,體現了沃克的民族自豪感和自我肯定。《紫色》借助自然,將黑人女性的身份觀延展為全人類的身份討論,即共同參與搭建無暴力和無等級的話語空間,尊重不同社群、自然及自然界中的生物,不企圖占有、操控或指使他人,保障各社群間的平等互利,維持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平衡關系。
六、結語
從女性主義角度探討《饑餓的女兒》《紫色》中的邊緣人物身份構建,可以發現,兩部小說均通過對大動蕩時代背景下邊緣女性的饑餓和欲望的描寫,還原出她們的現實困境,刻畫出人生百態。在此基礎上,將女性與人性、自然相聯系,私人情感與民族喜悲相融通。以多方面身份構建來呈現人物變化的性別認知,已成為成長題材小說的特定敘事路線。這一路線在美國黑人小說《紫色》中鮮明地表現為西麗從怯弱的家庭婦女到獨當一面的社會女性的變化。《饑餓的女兒》描寫了背負著私生子、女性、貧民三重“原罪”身份的六六如何成長為一位掙脫枷鎖的女青年的過程。通過梳理兩篇小說的人文情懷、女性立場以及女性生理體驗和內心體悟等內容,我們發現,中美當代女性主義成長小說的重點旨趣,都在于描摹以主人公為首的人物的情欲糾纏、精神奮斗與心理掙扎。通過分析文本,我們還看到東西不同文化政治背景下大體相似的女性訴求,其中亦有西方女權對中國創作的影響。毫無疑問,這樣的闡釋有利于讀者和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中美寫作中女性人物尤其是邊緣女性人物的身份構建方式。
總的來說,圍繞中美兩部女性主義成長小說進行平行研究和影響研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這種意義大致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通過《紫色》與《饑餓的女兒》的比較,可以增強對美國女性成長小說及其理論資源的認識,并能夠發現中國女性成長小說的角色構建方式及其對歐美理念的本土化吸收。其二,有利于發掘中美女性主義成長小說敘事的獨特話語及身份構建方式,為當下中國女性文學創作提供某種參考。其三,有助于了解中美特定時期的女性尤其是邊緣女性的真實需求、復雜經歷和自我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