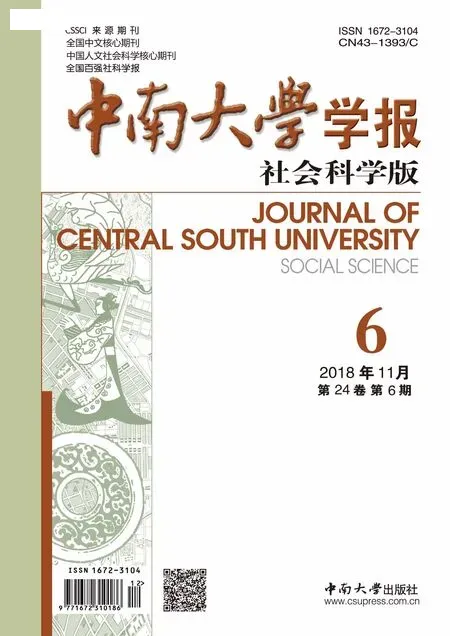構建王權的專權:諾曼征服到亨利二世時期英國森林區制度的歷史變遷
(北京大學法學院,北京,100871)
王權是政治史研究最為核心的內容之一,學者對中世紀英國王權的研究也頗為全面。20世紀30年代小杜塔伊斯提出了封建王權的概念,西方學界之后對封建王權的性質進行了諸多爭論。中世紀英國的封建王權模式大體上分為“憲政主義”“封建分裂”“法律有限王權”和“權威王權”四種模式。國內學者如孟廣林先生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強調王權的公共權威性,較好地梳理了中世紀中期英國王權的理論和事實問題[1](1-49)。近年來,學者雖然對中世紀政治史研究進行了一定拓展,如強調共同體公共性[2](13-19),以“領主權”代替封建概念[3](117-136),但總體上沒有其他理論取代封建王權理論范式。
已有的政治史研究基本認同封建王權既包括國王的私人權利,也包括國王的公共權威[1](38-39)。但這些研究更關注王權公共性的一面,國王的私人權利一定程度被忽視了。事實上,這種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的國王個人權利在英國有一個特定的稱呼,即專權(prerogative)。布萊克斯通認為該詞源于“prae”(在……之前)和“rogo”(我請求),意味著國王基于國王尊榮(regal dignity)享有的高于其他任何人的不受普通法一般程式約束的特別優越性(special pre-eminence)。雖然布萊克斯通認為專權受到憲制的限制,但他也強調專權的必要性。國王當然享有專權:“專權在本質上就是獨一和反常的,它只能應用于國王獨享的權利和權能,不同于其它權利,不同于他與臣民共同享有的權利。”[4](155-156)
正是基于此定義,我們進一步討論“prerogative”的翻譯問題。毫無疑問,“prerogative”是一種特權,最常見的對譯也是“特權”。如約翰·洛克《政府論》(下篇)第14章名為“prerogative”[5](374-380),葉啟芳與瞿菊農將其譯為“特權”[6](98-103)。不過,李猛在《洛克與自由社會革命政治:洛克的政治哲學與現代自然法的危機》一文中辨析了“專權”的性質,強調“專權”是執行權的自由裁量使用,進而以“專權”翻譯取代了“特權”[7](1-97)。這種翻譯也為部分學者所接受[8](17-31)。此外,“特權”的常見對譯是“特權——privilege”,在中世紀還有“特權——liberty”對譯[9](185-186),所以具有區分性的“專權——prerogative”對譯是最為合適的選擇。
專權貫穿英國歷史之中,森林區①是封建王權頗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專權,12世紀晚期的《財政署對話錄》提供了非常清晰的證據:
森林區的組織,以及對森林區內違法人士的處罰和赦免,無論是罰金或者肉刑,與王國內的其他判決相分離,只從屬于國王的自由裁量(discretion)或者一個為此專門任命的副手。因為森林區有自己的法律(laws),據說它不基于王國普通法(communi regni jure),而是基于國王愿意的制度(voluntaria principum institutione),因此種法律實施的據說不僅是絕對的,而且是僅依據森林區法律的[10](455)。
森林區是實施森林法的區域[11](171-208),其目的是為了保護國王的狩獵權。森林區不只包含森林②,而是包括多種土地類型,如森林、荒地和草地。國王占有森林區,但并不意味著必然占有森林區內的所有土地,只不過區內他人所有的土地被禁止狩獵和開墾。《財政署對話錄》認為森林區是為了國王的愛好而建,為了國王在其中狩獵和休憩,森林區中的違法行為專屬國王管轄,并受到國王處罰。
在中世紀的英國,森林區的發展基于王權和專權,牽涉到行政機構、財政收入和法律體系等諸多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議題。
森林區也是現代研究者較早注意的議題。19世紀的研究者對森林區屢有提及并將其看作諾曼暴政的一部分。愛德華·弗里曼(Edward Freeman)是牛津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他在1873年提到威廉征服帶來了殘酷的森林區法律,并認為這是對英國人自由傳統的破壞[12](414)。20世紀初小杜塔伊斯發展了這一觀點,認為“森林區是諾曼征服暴行的決定性證據,證明了諾曼安茹諸王的殘暴統治,引起了男爵和高級教士對王權的反抗,導致了民眾對王室官員的仇恨”[13](147)。這一時期的歷史研究為牛津學派所壟斷,森林區被視為諾曼暴政的一部分。
20世紀50年代,奧斯丁·萊恩·普爾批評了上述學術論斷,認為森林區是“國王休憩的場所,通過狩獵擺脫世俗紛擾”,“并非所有的林區長、林區文書和林區巡查都殘忍專斷”[14](29-34)。在70年代,查理·楊進一步關注森林區制度的發展及其經濟意義。他梳理了森林區發展過程,認為森林區制度在13世紀到達頂點,是“行政制度研究的轉折點”。楊特別強調森林區制度的經濟意 義[15](vii),認為土地價值的上升而非暴政是森林區消失的主要原因[16](177-178)。近來,學者開始關注森林區的政治文化意義,強調狩獵是貴族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國王鞏固權力的手段。馬文認為“諾曼征服將森林法帶給英國,改變了延續幾個世紀的狩獵文化。壟斷狩獵權達到最大規模,狩獵技藝充滿了貴族氣息”。但是他也認為“國王威廉專橫統治,損毀教堂驅逐民眾建立新森林區”[17](1)。目前,國內研究關注森林區的環境、收入、法庭、法律和政治意義,但更側重制度形成之后的運作模式,森林區的建立和形成、森林區的專權性質,以及專權與王權的關系等方面仍待繼續研究。
一、反抗國王專權:森林區制度的私欲
提起森林區,最為現代研究者熟悉的恐怕是《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對威廉一世的批評:
他陷入貪婪和他所鐘愛的口腹之欲中。他開辟鹿苑并在其中設立法律,(規定)捕獵雄鹿和雌鹿的人將被刺瞎雙眼。他禁止人們捕獵雄鹿與野豬,他如父親般愛憐高大的鹿。他亦下令野兔應當自由奔馳。這使得富人哀嘆,窮人發抖。但國王專橫非常,不顧眾人的怨恨。因為眾人若想獲得生存、土地、財產或和平,就必須遵從國王的意志。啊,竟有人如此夸大自矜,凌駕眾人[18](142)③。
這段文字出自《威廉王之歌》(Rime of King William)[19](131-144),是最早指責森林區是國王“暴政”的記載。在編年史家筆下,威廉一世創建森林區的暴行遭受了諸多報復。編年史家弗洛倫斯[20](44-45)認為這一暴政導致了威廉二世的死亡。他指出在懺悔者愛德華和其他英國國王統治時期,土地肥沃,人口眾多,信眾虔誠,教堂密布。威廉一世驅趕民眾,搗毀房屋,毀棄教堂,留出空地給獵物。上帝的憤怒與復仇是威廉二世狩獵身亡的原因[21](178)。12世紀的編年史家奧德里克(Orderic)則將受害者擴展到威廉一世的兒子諾曼底的理查德以及孫子理查德④。漢普郡曾有密布的村莊和稠密的人口。為了建設森林區,威廉一世搗毀了60多個教區,趕走居民,安置野獸并肆意狩獵。上帝震怒于自己的教堂(consecrated buildings)被野獸占據,不僅威廉一世不能獲得救贖,威廉二世和兩個理查德也因此喪命[22](282-285)。
12世紀末戰場修道院(Battle Abbey)編年史將創建森林區的罪惡歸于威廉二世,威廉一世則搖身變為偉大威廉(great William)。編年史家指責威廉二世耽于狩獵,創建森林區,制造恐怖,臭名昭著。上帝以其神秘而不可知的意旨,使威廉二世被提瑞(Tirel)“意外”射死。在亨利將威廉二世埋葬后,上帝預定亨利登基為王[23](107-109)⑤。隨著時間推移,人們的森林區記憶有所變化,但編年史家依舊認為創設森林區的人逃不過上帝的審判。
森林區是國王難以割舍的專權,國王往往不惜食言而肥。亨利一世甫一登基就宣稱廢除之前的苛捐雜稅和邪惡習慣(evil customs),承諾僅保留威廉一世時期的森林區[24](432-434)。但他食言而肥肆意建立森林區。亨利一世途經萊斯特郡瑞茲鎮時,只因看到5只雌鹿就將該地劃入森林區,并留下隨身侍從監管[25](45)。他聲稱在英國唯他有狩獵權,并將森林區周圍的狗都弄殘,只勉強允許極少數貴族在他們的森林中狩獵[22](101)。
安茹王朝建立后,亨利二世繼續發揚上述傳統開辟森林區,在他統治時期森林區占英格蘭1/3的面積。亨利二世新建森林區的行為沒有受到有效限制。但是憤怒的修士想象了亨利二世死后受罰的場景。1196年一位修士見到了地獄中的亨利二世,亨利二世騎著口鼻火花四溢、周身煙霧臭氣的烈馬,披掛著炙熱熔融的盔甲,被馬鞍上的長釘刺入肝臟與腹部。亨利二世所犯重罪之一就是嚴苛地執行森林法[26](610)。
通過編年史家的敘述,我們發現在諾曼征服后的一個半世紀里,英王沉迷狩獵,欺凌百姓,民眾苦不堪言。森林區專權起于貪欲,迫害民眾,難以限制。不過漫天指責中也偶有反駁之聲。杰弗里·杰瑪(Geoffrei Gaimar)提到弓箭手與獵狗因進入森林區受到處罰,認為對這一行為處罰是公正的。在杰瑪筆下,提瑞的無心之失變成了蓄意謀殺。威廉二世則在眾人的哀悼聲中,領受圣餐,回歸上帝的懷抱[21](181-189)。理查德·菲茲·尼爾認為國王通過狩獵進行休息和娛樂,在森林區中逃避宮廷的紛擾,呼吸大自然的自由空氣。森林區是國王的宮室(king's chambers)和快樂之源。國王因而應該按照自己的意志處罰侵犯林區的人[27](60)。
盡管有杰瑪和尼爾的辯護,20世紀前后的史學家普遍認為這些指責是真實的。愛德華·弗里曼認為《威廉王之歌》既反映了被征服的英國人對異民族習慣的憤怒,也體現了諾曼貴族的憤慨。亨利·威廉·卡利斯·戴維斯(H.W.C.Davis)更進一步認為《威廉王之歌》主要是英國人民對森林法的憤慨[19](132)。看上去森林區只是為了國王的私欲而建立,這種基于國王私人權利的專權只是暴虐的權力。筆者認為,對森林區專權的討論需要從森林區的形成談起。
二、專權的行政化:維護國王尊榮的森林區
森林區制度是從諾曼底引入的,融合并取代了盎格魯撒克遜時期英國的森林管理制度。英國很早就開始了森林開墾,5世紀圣布里厄(Saint Brioc)就看到人們砍倒大樹,拔除灌木,粉碎荊棘,使密林變空地。人們還平整木材做建房之用。時人哀嘆“荊棘之根何其壯,每每辛勞手受傷”[28](36-37)。7世紀末的《伊恩法令》(Laws of Ine)已經開始限制砍樹的方式,用斧子偷樹,每棵處以罰金30先令,最多賠償90先令,而用火偷樹,每棵處以罰金60先令。阿爾弗雷德大帝在9世紀重申了該規定[24](398-416)。到10世紀,新開辟的土地可以及于相鄰的森林,不過村莊共同體還沒有確定相鄰森林的所有權[29](285-286)。《卡努特法典》⑥規定人人皆有在其森林和土地狩獵之權利[30](12),不過侵犯國王狩獵地將被處以罰金[24](467)。盎格魯撒克遜時期國王的狩獵特權已然形成,但沒有形成專門的森林區專權、森林區法律和森林區制度。
在歐洲大陸,查理曼統治前期通過開疆擴土來保持國家的團結,硝煙退去后他需要更加細膩的管理來維持帝國的統一。查理曼通過伯爵來保證法令的實施。806年的一份手稿顯示,查理曼的信使勸誡地方伯爵重讀法令并思考自己的職責,以獲得皇帝的恩寵。伯爵致力于維護皇帝利益,詳列地方信息給信使,并就不懂的命令詢問信使。伯爵持有皇帝的信件以便按其內容執行,查理曼的答復也被伯爵記錄在案并在伯爵法庭上執行[31](159-160)。
查理曼發展完善了森林管理制度,并在《莊園敕令》中作了詳盡規定:
應好好保護森林和朕禁伐的密林;如果那里有適合清除的地方,則加以清除,使田地不致長滿樹林;如果那里應有樹林,決不容許把它砍伐和毀滅,在朕禁伐密林中的野獸,應小心保護,也應為朕關心鷹和雄性蒼鷹,又應認真收集這項該征的租稅。
其他規定包括:管理人和他們的狗不得寄宿在國王的森林中;如何在森林中放牧豬群;保證御園的修葺以及幫助國王的狩獵長[32](8-20)。查理曼還對地產進行了登記,促進了 9世紀財產清冊 (inventories)制度的形成。該管理方式在教會地產中比較常見并延續下去[31](160)。查理曼的后繼者將森林區作為一項王室制度繼續使用下去。877年大膽查理禁止自己的兒子路易在某些特定的領域狩獵,并讓大臣記錄路易捕獲的獵物。974年的一張特許狀也顯示虔誠者路易將一片皇家森林獻給了修道院[21](166-172)。
10—11世紀,隨著查理曼帝國的崩潰,高盧地區的公爵和伯爵在各自的區域中管理森林。羅伯特一世公爵在一份特許狀中曾規定將森林中1/10的收入授予他人。1080年利來伯恩(Lillebonne)會議重申過去的規定,教士因森林內違法繳納給國王和男爵的罰金,不必與主教分享。1180年諾曼底地區的卷檔顯示森林被精心管理,罰金多集中在砍伐林木而非違法狩獵[33](420,430)。不過諾曼底公爵在授予臣民的森林中仍保有狩獵權,可能存在限制砍伐樹木的規定[34](114-128)。諾曼底地區存在制度化的森林法和森林訴訟。理查二世公爵治下農民起義的目標就是自由利用樹木,不受國家法律(jus ante statutum)的限制[13](166-167)。
在介紹諾曼王朝森林區制度之前,我們先對諾曼征服后的英國森林進行簡單回顧。經過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開墾和耕種,到1086年英格蘭的定居點已頗具規模,在大部分地區,旅行者往往走不到半日就會碰到住宅區。但英格蘭地區仍布滿了不可計數的小片森林和數量可觀的大片森林。橡樹是最常見的樹木,其他樹木有白臘木、榛樹、椴樹、冬青樹、榆樹、楓樹、樺樹和荊棘[35](78-79)。弗蘭克·斯坦頓認為所有森林區域都有小村莊(hamlet)[29](284)。
威廉一世將諾曼森林區傳統引入英國。與我們對諾曼底森林制度了解的模糊性相比,我們清楚地知道在《末日審判書》中森林區是司法特區(jurisdictional area)。森林區是為了保護野獸而建立的并在其上實施森林法的區域。森林區內有多種土地類型,如森林、荒地和草地。國王雖然占有森林區,但并不必然占有森林區內的所有土地,不過區內他人所有的土地也被禁止狩獵和伐樹[25](x)。
新森林區(New Forest)是英國森林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末日審判書》中專列一部。新森林區位于漢普郡,以伊靈(Eling)、林德赫斯特(Lyndhurst)和布羅肯赫斯特(Brockenhurst)三個莊園為中心,分別包括林伍德(Ringwood)、霍頓赫斯特(Holdenhurst)和溫克頓(Winkton)三片森林和狩獵區。這些土地在諾曼征服前屬于托斯提格伯爵(Earl Tostig)⑦,如今順理成章地歸國王所有。新森林區還侵占了白徹姆斯利(Battramsley)周圍的帶狀土地。上述國王所有的土地之外是貴族所有的土地,但貴族土地也被劃入森林區內,負責提供食物和服務。其他地區的森林區也把周圍的土地劃入,《末日審判書》中就有“在森林區中”(in the forest)和“處于保留中”(in preserve)兩種兼并方式。總體上,英格蘭高地地區的森林區甚多,中部要略少些[33](422-423)。
威廉一世時期森林法和森林制度的內容語焉不詳,按照《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的記載,新森林區內的刑罰是刺瞎雙眼。威廉二世曾在令狀中禁止林區長(forester)干涉拉姆齊修道院的森林,除非牽涉“狩獵和開墾森林區”,這意味著林區長已經在森林區中進行管理。威廉二世曾準備使用死刑處罰誣告的人,但根據神判法,后者因觸摸烙鐵不受傷而免于刑罰[33](421)。
亨利一世時森林區已廣為人知。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在1127年完本的《盎格魯國王史》(Gesta Regum Anglorum)中抱怨森林區里“野獸傲慢行走”。漢丁頓的亨利則觀察到新森林區是野獸的棲息地[19](137)。此時森林區制度已比較成熟,森林區以固定價格包租給林區長,后者負責林區管理并多由家族世代相承。林區長下屬稱為林區小吏(minuti forestarii),尚不清楚其是負責日常行政,還是幫助審理森林訴訟。至于林區守衛(woodward)、林區文書(verderer)、林區代牧(agister)以及林區巡查(regarder)都還沒有提及[36](128-130)。
國王在森林區內享有諸多權益并受到嚴格保護。按照《亨利一世之法》的記載,森林區訴訟涉及開墾森林區(assart)、伐木、縱火(burning)、狩獵、于森林區中攜帶弓與矛、弄殘獵狗、不幫助國王狩獵、放縱家畜亂跑、森林區中亂建、不聽森林訴訟傳喚、林中攜帶獵狗、家中發現皮毛與獸肉。森林之訴的主要目的是保護國王的獵物,森林區的經濟價值尚未凸顯[30](12)。郡長可能審理了森林區的司法事務,但也只有零星提及。
為保證國王利益,王室法官分赴各地,審理森林區內訴訟。1130年卷檔記錄了5名巡視各郡的王室法官處理了包括森林訴訟之內的各類訴訟。沃克林·維斯德洛普(Walkelin Visdelop)曾在薩里郡和伯克郡專門聽審森林區訴訟[36](220-225)。朱迪斯推測森林區外的居民也被傳喚(summoned)來作證和進行訴訟[33](426)。1130年卷檔和國王的特許狀表明監禁和罰金是主要的處罰方式,而非編年史中常見的死刑和肉刑。亨利一世在授予達勒姆主教瑞納爾·弗萊姆巴德夫的特許狀中禁止別人侵犯主教的森林,違反者的處罰方式與在新森林區違法狩獵相同,即處以巨額罰金[14](34)。這意味著即使最嚴重的偷獵行為可能也只是處以罰金。
國王專權代表著國王尊榮,因此森林區罰金數額巨大且不避權貴。鮑德溫·德·雷德弗斯(Baldwin de Redvers)因在新森林區狩獵被罰 500銀馬克。沃爾特·埃斯佩克(Walter Espec)是王室重臣,曾任王室法官,也受到兩次處罰,共繳罰金250銀馬克[33](426)。相較罰金收入,森林區的經營性收入極少。1130年卷檔顯示森林區訴訟收入是1 416磅18先令6便士,森林區經營獲利是164磅3先令5便士。總體上,森林區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不高,1130年國王總收入是68 767磅 7先令 4.5便士,森林區收入約占2.2%[36](220-226)。這表明在諾曼時期森林區是國王的尊榮性專權,而非經濟利益的源頭。
總之,在諾曼王朝統治期間,征服者們基于歐陸傳統創設了森林區。森林區是關于國王尊榮的特權,是諾曼時期最典型的國王專權。為了維護國王專權,森林區初步形成了專門的管理制度、森林法和官員,但沒有證據表明各森林區內的管理是一致的[10](466)。森林區刑罰存在肉刑,但主要是數目極高的罰金,總體上刑罰漸趨文明化。森林區并不關注經濟利益,經營性獲利很少,主要收入來自森林罰金,同時罰金比例也不高。但是,高昂的罰金帶有明顯的報復意圖,目的是保護國王在森林區獨享狩獵權,以此維護國王專權。
三、行政專權司法化:尊榮與收益并重的森林區制度
1154年亨利二世加冕為王,采取各種措施重振王權。由于森林區邊界模糊,豁免森林區管轄(exemption)以及地方秩序的混亂,森林區遭受嚴重破壞。重建森林區成為維護國王專權和王權的重要內容。亨利二世時期的森林法罪名與亨利一世時期的相差不大,主要罪行已在《亨利一世之法》中提及。這既是因為亨利二世主觀上要恢復亨利一世之法,也是因為森林區官員多系家族繼承[24](451-453)。亨利二世不只在英國發展了巡回審判,也在森林區內改革了司法制度。1154年亨利二世對被開墾的森林區進行了調查,并處以大量罰金。1166年亨利二世繼續往森林區派出法庭。1184年亨利二世頒布的《伍德斯托克法》將上述司法實踐進一步系統化[13](180-181)⑧。
森林法具有排他的管轄權。相較普通法對教士管轄權的諸多爭議,《伍德斯托克法》重申了森林法對教士的排他性管轄。早在1175年,亨利二世就與教皇代表簽訂協議,確認森林法對教士的管轄,亨利二世同年審訊了大批教士。相較于貝克特與亨利二世的授職權之爭,森林法管轄權沒有爭議。《伍德斯托克法》第9章規定砍伐樹木和偷獵野獸的教士將被逮捕,第13章規定在森林區內擁有土地的教士要宣誓維護“國王和平”。為了保證森林區訴訟的進行,所有大主教、主教、伯爵、男爵、騎士、自由保有人以及其他人將聽從林區總長(master-forester)的傳喚,參加森林區訴訟。森林區對普通人的管轄也超出了森林區,日趨擴大。按照《伍德斯托克法》,森林區周圍鎮區都要派出代表出席調查。森林區法庭傳喚最遠可到森林區外2里格。這不僅耽誤民眾時間,更讓他們因不出席而受到處罰[37](270-273)。
森林法保護動物和森林。除非有保證人,否則禁止任何人在森林區內攜帶弓箭和獵狗。同時,夜晚狩獵野獸、破壞野獸巢穴、以動物為餌作陷阱狩獵都是犯罪行為。砍伐自己林地中的樹木需在林區長的監督下進行,以保證沒有毀損森林區(waste)⑨。森林區開墾由國王決定并須及時調查面積大小,侵占森林區(purprestures)也在處罰之列。森林區內的狗被處以殘肢之刑,制革工和漂白工不得居于森林區內。
罰金和監禁是森林法的主要刑罰。按照《伍德斯托克法》第1章的規定,亨利一世時期的肉刑被保留下來[38](67)。第 12章規定侵入森林區(transgression)將繳納保證金(pledge),第三次侵入將被監禁。第16章規定夜晚狩獵野獸、破壞野獸巢穴、以動物為餌作陷阱狩獵,都處1年監禁并處罰金。但是第1章的肉刑和第 16章的監禁刑相互矛盾,小杜塔伊斯認為第 1章來自亨利一世時期的法令,第16章則為亨利二世所創[13](175,181)。編年史家迪賽托的拉爾夫(Ralph of Diceto)的記錄顯示,亨利二世時期森林區的懲罰主要是罰金與監禁[26](184)。克魯克分析了所有現存卷檔,沒有發現因違反森林法而處以肉刑的案例[38](69)。
不過,司法化是在原有行政制度的基礎上進行的,即賦予行政長官以司法職能。亨利二世時期的森林區管理者是林區總長和林區長,他們負責日常管理并參加森林區法庭的審理。林區總長經常在各地之間來回奔波。艾倫·德·內維爾(Alan de Neville)作為林區總長游走英國諸郡,進行無數調查。艾倫的管轄權及于教俗兩界。他曾對森林區內的戰場修道院進行了一系列壓榨,從3名修士手中分別榨取了20先令、半馬克和半馬克。這些錢由郡長收集起來交給財政署,后者將錢存到國庫中。戰場修道院的修士無奈偽造令狀,到財政署向首席政法官和財政署男爵抗議,最終得以收回錢財,財政署的賬目也被劃掉。艾倫處心積慮的盤剝并沒有讓亨利二世滿意,艾倫死后他的財產歸于國王[23](221-223)。艾倫的惡名也繼續存在后人的記憶中,1229年在牛津郡的一次調查中,居民仍然記得艾倫擴張森林法的行為[33](425)。地方森林區法庭也已經存在,違反森林法的人會被林區官員和平民起訴。
《伍德斯托克法》規定了林區長和其他官員的權責。林區長是森林區的實際管理者。林區長宣誓維護森林法,且不得騷擾林區內的騎士和顯貴。若森林區遭受損害而林區長沒有正當理由,林區長將被逮捕。不過,林區長雖對王室森林區內他人所有的森林有照看之責,但對他人森林的損失卻不需賠償。此外,森林區內有森林之人應任命自己的護林管家(forester),保證不侵害國王的利益。凡有鹿之郡,郡中需選出12名騎士看護鹿與森林區,其中4名為林區代牧,負責牧牛放豬諸事。唯有在國王完成放牧后,其他人才得以放牧。林區巡查調查土地是否存在耕種、侵占和毀損的情況,同時調查森林區的礦井、鷹巢、冶煉場以及圈地內的干草情況[25](lxxv-lxxvii)。
林區總督(warden)也在森林區管理中承擔重要責任。根據瑪格麗特·貝澤麗的研究,亨利二世時期的林區總督已經負責迪恩(Dean)森林的管理。林區總督理論上管理所有森林區的事物,如執行森林法和國王命令,林區長則負責具體實施。郡長有時會幫助林區總督,如收繳罰金和迫使被告出席[39](140-172)。亨利二世統治前期,郡長就已經負責收集森林訴訟中的小額罰金。艾倫·德·內維爾曾將罰金列表交給郡長,郡長再將罰金收集后上交財政署和國庫。
王權需要巨額財政支持,中世紀的英國國王一直面臨財政壓力。亨利二世時期森林法關注的重點從保護狩獵轉向增加財政收入。1175年違反森林法的罰金總額高達12 305磅,而在此之前,王室的年收入不過21 000磅,王室的郡包租才10 000磅。森林區經濟地位占主導的另一個佐證是開墾王室森林被處以罰金并征收租金,而非搗毀開墾的土地以恢復森林。查理·楊分析了亨利二世時期的卷檔,其中對偷獵行為的處罰極少,主要是處罰毀損森林區的行為,盡管考慮到拖欠和赦免,實際處罰可能沒有這么多[15](34-55)。森林區經濟價值愈加凸顯,森林區事實上被允許一定程度的開發。
森林區行政和司法制度的發展使其專權特色更為凸顯。森林區是國王個人行使的專權,完全由國王專門任命的官員負責,連首席政法官都無權干涉。亨利二世時期森林區的管理者是林區總長和林區長,他們負責日常管理并參加森林區法庭的審理。林區總長不對首席政法官負責,有獨立賬目,直接對國王負責。理查德·德·盧奇(Richard de Luci)是亨利二世出國時的攝政,掌管財政、軍事大權,權威不遜亨利二世。但盧奇無法暫停森林法的執行,因為唯有國王才能決定森林法[40](49)。森林司法也直接處于王室命令下。埃莉諾王后曾在亨利二世死后大赦天下,其中所有違反森林法的人都當即釋放,而犯有其他違法行為的人則要經過一定的程序才能釋放[15](23)。亨利二世時期森林區制度基本形成,在強大有效的行政和司法制度的保障下,森林區達到最大規模,占英國領土的1/3。
與此同時,亨利二世時期森林區管理的加強也加深了森林區內的壓迫。自由保有人的財產權在森林區中受到嚴重限制。他們不能開墾森林區,不能開墾荒地和草地,不能建磨坊,不能取泥灰和石灰,不能建魚塘和圈地。因為以上行為都侵犯了國王的權利。自由保有人每次放豬都要讓國王先放2周,通行森林區還要交通行稅,更要擔心砍伐樹枝所犯的毀損森林區罪。森林區邊界模糊,開墾者往往“侵占”森林區而不自知。盡管按規定窮人可以從森林區獲得食物、燃料和建筑材料,但是只有在林區長的監管和盤剝下才能進行。未經允許開墾森林區一般按其種植的作物進行懲罰,1英畝小麥罰 1先令,1英畝燕麥罰 6便士[27](86-89)。不過在亨利二世一朝,最重要的矛盾仍是授予職權之爭、王位繼承、邊界爭端,森林區沒有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
森林區在亨利二世時期體現出更明顯的專權性質。在教俗權之爭中,亨利二世作出了教士犯罪不由世俗法庭審理的讓步,但仍然保留了兩項例外,即侵占森林區和涉及封君封臣義務的案件,仍由國王管轄[1](249)。可以看到,這里保留的是封建權力和個人專權。森林區在當時的政治理解中并非王國的公共事務,而是國王的個人事務,屬于國王的專權,不受教會、貴族和平民干涉。但是國王的個人利益不足以解釋森林區制度的發展延續,森林區專權實際上是構建王權的重要資源。
四、構建王權:理解專權的私欲與公益
毋庸諱言,森林區引發了諸多的矛盾與憤慨,但是現代史家的研究證明,許多指責并不確切。諾曼征服之后,威廉一世毀農田開辟森林區的行為缺乏證據。英格蘭地區主要是十分貧瘠的第三紀土石(tertiary sands and graves),這些土壤難以支持繁榮的農業經濟以及供養稠密的人口。森林區中有大片的土地長期無人居住。《末日審判書》也證明在森林區建立過程中并沒有編年史描述的諸多動亂[15](7-8)。政府卷檔中也少有肉刑和死刑處罰,理查森和賽爾斯都認為森林區和森林巡回法院的主要目的是獲得財政收入[41](46-47)。
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我們需要重新考察森林區建立和發展的原因。雖然喜愛狩獵的國王甚多,懺悔者愛德華甚至在起義爆發時仍在狩獵,但建立森林區絕不僅僅是因為國王的貪欲和愛好,這種持續性的國王專權僅憑私人偏好無法解釋。而且狩獵具有很大的危險性,如882年路易在騎馬時摔死,2年后卡洛曼(Carloman)也在狩獵中去世[31](137)。而經濟利益也不足以解釋森林區的發展。諾曼時期對森林區土地并沒有需求,記錄顯示森林區遭砍伐后,土地多遭棄置而非開墾。森林區提供木材,木材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但并非國王的核心利益[15](8)。可見,這些解釋都難以令人滿意,即森林區的建立不僅是國王的娛樂與偏好,亦不僅是搶奪木材資源。
首先,森林區展示并塑造了王權。國王的森林區專權服務于國王狩獵。國王巡游各地,通過狩獵展現自己的勇武與謀略,塑造自己的個人形象,也為王廷餐桌提供豐盛野味。狩獵還能增強體能,培養戰斗意識。狩獵也有軍備意義,是實戰的演練。有人甚至認為戰爭不過是更大的狩獵[42](76)。最為根本的,國王通過森林區專權壟斷了狩獵活動,在這種壟斷的狩獵場景中展示自己的最高權力。因此,專權不僅僅是國王個人意志的展示,更是國王公共權威的塑造和操練。
其次,國王通過森林區形塑了貴族團體。貴族文化是表演(display)文化,借助于狩獵,貴族形塑他們的等級并展示他們的權力。狩獵既需要身份也需要財富。馬匹價格昂貴,獵狗成群結隊,訓鷹所耗不菲,狩獵需要專門的訓練和相應的財富支撐。因為狩獵的獨特內涵,狩獵成為貴族集團的核心標志和重要手段。索爾茲伯里的約翰哀嘆道,貴族的學問是由狩獵術語組成的。為此,國王極力壟斷狩獵權,阻止貴族群體的自行狩獵。1066年威廉一世允許伍斯特主教在摩爾文(Malvern)森林牧豬、伐薪和伐木修屋,卻禁止其狩獵[33](423)。國王繼而通過賦予狩獵特權來籠絡貴族,并在活動中培養自己的貴族親信。在狩獵活動中,國王既可以籠絡大貴族,也可以任命中小貴族。加洛林王朝時期的狩獵者就比其他侍臣(courtier)享有更多權力[17](95-96)。國王通過集體狩獵形成了一個小的武裝集團。
再次,違反森林法往往會被迅速處以高額罰金,并且難以獲得司法救濟,貴族不得不向國王獻媚以求減免。可見,免除高額罰金也是國王籠絡貴族的有效手段。
最后,森林區是國王重要的政治籌碼。1088年威廉二世為應對叛軍,允諾實行“過去存留在這塊土地上的最好的法律,禁止不義的行為,恢復人們的森林和狩獵權”[18](145)。亨利一世在加冕誓言中宣稱僅保有威廉一世時的森林區。1136年斯蒂芬王也承諾只保留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時期的森林區,亨利一世時期的新設森林區將歸還教會[24](434-436)。1142年瑪蒂爾達免除了埃塞克斯伯爵開墾森林區的處罰,亨利(未來的亨利二世)在1153年允許利奇菲爾德在王室森林區開墾土地[15](16)。亨利二世也曾為了應對反叛授權理查德暫停森林法執行。
因此,森林區成為王國行政和司法制度的重要部分,森林區專權也成為王權的重要基礎。在諾曼征服及在這以前,國王的戰爭角色十分關鍵,狩獵體現了國王的戰斗技藝,彰顯了國王的戰斗勇氣。諾曼君主采用“巡游王權”實行統治,國王率領王廷巡視各地,既督促地方貴族,又便于在莊園就食。這種王權是“個人王權”,國王的聲威、意志、策略和精力是統治的關鍵因素[1](280-287)。國王巡游各森林區狩獵,體現出國王的勇氣、財富與權力,貴族集團也跟隨在國王身后。12世紀下半葉,人們還記得狩獵在森林區建立中的重要作用。理查德·菲茲·尼爾認為“foresta”(森林區)源自“feresta, ferarum statio”(野獸棲息地)[27](60)⑩。森林區專權是“個人王權”必不可少的部分。
森林區和國王駐地多有重合。一條森林帶自新森林區(靠近溫徹斯特和去往法國的港口)向北,到牛津郡森林、羅金厄姆森林和舍伍德森林。這條森林帶上點綴著克拉倫敦、伍德斯托克、格丁頓和克里坡斯通(Clipstone)等王室駐地。而沒有森林區的郡,如東南諸郡和東盎格魯亞郡,則沒有王室駐地。森林區是狩獵之地,也是行政之地,國王在這里彰顯武力,行使權力[26](138-139)。1127年亨利一世在森林區等待適合渡船的天氣去諾曼底,并在此期間審理了諸多森林訴訟[33](427)。
森林區的許多規定明顯針對貴族的狩獵權利,國王借此強調自己遠高于貴族。以殘肢獵狗為例,中世紀狩獵動輒需要十幾數十條獵狗,貴族是主要的養狗者。國王剪斷森林區內獵狗腳趾的行為主要針對貴族,并使貴族怨恨非常。狩獵表明國王與貴族之間的關系,既是命令與服從,又是合作與互惠。誠如編年史家所言,森林區的目的是保證國王的狩獵權利。
我們可以如是理解一個由亨利二世代表的標準國王形象:
戰爭時時爆發帶來威脅,他(亨利二世)馬不停蹄地解決這類事物。和平期間他不耽于寧靜,不安心休息。他極度沉溺于狩獵,黎明即騎馬狩獵,穿過荒地,深入森林,登上山頂,如是度日[15](58)。
五、余論:以專權構建王權
專權是一個傳統概念,是王權公共性之外私人利益的部分。國王的“肆意專斷”是如何發展的?又是如何能夠發展的?森林區是中世紀英國的典型專權,建立初期就遭受諸多非議,被認為是諾曼暴政的一部分。這一觀點為牛津學派所堅持,并產生了深遠影響。諾曼王朝時期,“個人王權”需要國王的聲威、意志、策略和精力來維護。森林區壟斷的狩獵權凸顯了國王的勇氣、力量和權力。隨著森林區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亨利二世增強了森林區的司法性,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森林區制度。森林區不僅是王權的重要部分,也成為國王收入的重要來源。森林區的建立與歐陸傳統密切相關,是個人王權時期的重要政治手段,既凸顯了王權,又在一定程度上籠絡了貴族集團。隨著王權從個人王權走向制度王權,森林區專權也經歷了轉型,成為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國王是國家的代表,是公共權威的緣由,沒有強大的國王,就難以有超越封建結構的政治設計。森林區專權表面上是國王的個人喜好,實際上有豐富的歷史根源和現實需要,在發展中逐漸制度化,成為中世紀英國王權的重要基礎。
注釋:
① 在中世紀文獻中,“foresta”和“silva”表示不同意思,前者特指實行森林法的森林區,后者則與現代意義上的森林相同。文中將foresta譯為森林區,將silva譯為森林。
② 這也是翻譯為“森林區”而非“森林”的原因。
③ 這段名為《威廉王之歌》的韻文最早出現在彼得伯勒編年史(Peterborough Chronicle)1087年的條目下。最新的研究結果顯示這首韻文并非民間歌謠,而是博學之士的作品。
④ 兒子理查德,即諾曼底的理查德,威廉一世第二子。孫子理查德是諾曼底公爵羅伯特二世的私生子。奧德里克(1075—1142),本篤院修士。
⑤ 亨利一世應該沒有時間參加葬禮,威廉二世8月2日死于新森林區,而亨利一世8月5日就在威斯敏斯特登基。
⑥ 本章取自《卡努特法典》第80章和81章,而非12世紀編撰的《偽卡努特森林法》(Pseudo-Cnut's Constitutiones de Foresta)。后者的偽造十分明顯,斯塔布斯在《早期英國史講義》中早有提及,查理·楊認為《偽卡努特森林法》反映了亨利一世時期的一些森林習慣。
⑦ 托斯提格,即諾森伯利亞伯爵,高德溫伯爵之子,因暴政于1066年被兄長哈羅德殺死。
⑧ 據詹姆斯·C.霍爾特考證,森林法令有三個版本,分別是《首要敕令》(Prima Asisa)、《伍德斯托克法》和1198年法令。《伍德斯托克法》第1、2、3、5、6章重復了《首要敕令》,1198年法令重復了《伍德斯托克法》。小杜塔伊斯認為《伍德斯托克法》第1、4、6、7、8和16章是亨利二世制定,其他的可能來自亨利一世。
⑨ 按照菲茲·尼爾的描述,毀損的標準是站在一截樹樁上能看到5棵砍倒的樹。
⑩ 這個詞源學上的分析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卻反映了時人習以為常的兩者之間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