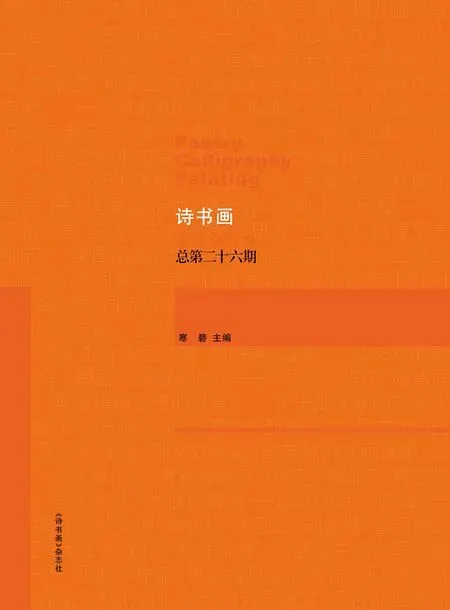漢宋傳心
——淺論清末民初時期幾位學者對理學學術史的解釋
余一泓
在清代乃至近代的學術史研究當中,“漢學”與“宋學”是一對繞不開的話題。前者是清代精英學者的主要學術風格,后者則是元明以來與廣大讀書人科試、修身密不可分的學術傳統,李帆認為:
清代中葉,漢學占據主導地位,理學相對衰微。不過漢學家也不是一味規避義理,畢竟程、朱思想某種程度上還是社會主導意識形態,亦為士人修身養性以及晉身之具,士人大都尊奉之。在這方面,漢學家自然也不例外。而且部分漢學家還有意識地在考據中求義理,甚至發展了義理之學,取得理學家所不及的成就。所以,漢學家的義理思想值得深入探究。①李帆《清代理學史》中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94頁。李帆在下文對戴震、焦循和程瑤田等人的性理之論做了介紹,包括本文要涉及的“性一而已”這個論點。
漢學雖然在江南,和在之后的湖南、廣東都聲勢頗盛,但與漢學對言之宋學,與考證對言之義理,與經學對言之理學,也都未淡出學術界,讀書人對此很有感受,繆荃孫(1844-1919)就有“能為漢學者少”之論。②繆荃孫《藝風堂友朋書札》,第361頁。轉引自桑兵《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文史知識》,1999年08期,第25頁。而在很多具體的讀書人身上,也并未表現出兩邊分住的對立。張循指出:
我們大體可以說,程朱系統之內能夠完全堅守尊德性傳統理念的人,正是那些無意對漢學“操戈入室”的人,換言之,對“漢宋之爭”不屑參合的態度,使他們避免了被漢學化的命運。③張循《道術將為天下裂—清中葉“漢宋之爭”的一個思想史探究》,桂林:廣西師范大學,2017年,第143頁。
張循認為,治“漢學”者除漢學家外,往往還有因卷入“漢宋之爭”而“漢學化”的宋學家。如果讀者疑“漢學化”之論過勇,不妨換句話說,學分漢、宋,往往僅僅是存在于那些本身有“漢宋意識”,強為之分的學者身上,如“漢學家”阮元(1764-1849)、“宋學家”方東樹(1772-1851)等等。若不存“漢宋之爭”,何來“漢學”、“宋學”?④章學誠、陳澧、錢穆和劉咸炘等不同時期的學者,多次指出過清代考證學的宋學淵源。如果說重視經傳、考證輯佚乃“漢學”獨有,那么朱熹、王應麟實為先導,而我們很難將朱、王等人也標識成“漢學”學者。這反映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清代相對于宋學而言的漢學本身不僅受其內容規定,更受其與宋學對言之關系規定,無“漢宋之爭”,何來漢學宋學?這是一個銳利的洞見。本文希望展示的,是幾位“漢學”背景深厚的學者,對“心”、“性”的概念在“漢學”、“宋學”當中如何使用,以及“漢學”、“宋學”之關系所作的討論。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漢學”的考證之風在如何介入學者對“宋學”義理的思考,以及和相關思考共生的一些學術史遺產。
漢宋論理,意趣相同:陳澧和陳漢章的觀點
“漢學”世家出身的劉師培(1884-1919),對于清世研治義理之學的“漢學者”有過兩段簡明扼要的描述:
近世以來,治義理之學者有二派:一以漢儒言理,平易通達,與宋儒清凈寂滅者不同,此戴、阮、焦、錢之說也。一以漢儒言理,多與宋儒無異,而宋儒名言精理,大抵多本于漢儒,此陳氏、王氏之說也。
夫學問之道,有開必先,故宋儒之說,多為漢儒所已言,……,“本原之性、氣質之性”,二程所創之說也。見《二程遺書》中,不具引。大約謂本原之性無惡,氣質之性則有惡。然漢儒言“性”,亦以“性”寓于“氣”中。……,《春秋繁露》亦曰:“凡氣從心。”此即朱子注《中庸》“天命之謂性”所本。惟宋儒喜言“本原之性”,遂謂人心之外,別有道心,此則誤會偽書之說矣。①劉師培《漢宋學術異同論·漢宋義理學異同論》,《儀征劉申叔遺書》第4冊,揚州:廣陵書社,2014年,第1586-1587頁。
本章所論從路數來說,是劉氏所言的第二路,即“漢儒言理,多與宋儒無異”而宋儒“多本于漢儒”;從著眼點來說,則是劉氏所言的“性”和“心”兩個概念,“漢學者”們如何看待漢、宋儒者因求二者于“氣質之中”和“氣質之外”而產生的不同思考,也是本文試圖敘述的。落腳到個人來說,則以“調和漢宋”的學者陳澧(1810-1882)為起點。
陳澧“調和漢宋”,闡述漢宋義理無異的觀點,在當時和后世都收獲了很多不同的聲音。于“漢學”學者之中,以批評的聲音居多,其中湘人葉德輝(1864-1927)曾經說過:
其時東塾先生遺書,尤為士大夫所推重。鄙人亦購置一冊,朝夕研求,覺其書平實貫通,無乾嘉諸君囂陵氣習,始知盛名之下,公道在人,眾口交推,良非虛溢。及讀《漢儒通義》一書,于此心始有未洽。蓋以性與天道,圣門且不可得聞,此事本非漢儒所究心,何必為之分門別類。②葉德輝《郋園論學書札·與羅敬則大令書》,《叢書集成續編》本,第88冊,第651頁上。轉引自張循《道術將為天下裂》,第192頁。然陳澧曾在《東塾讀書記·易》中明確贊同翁方綱認為“窮神知化”非常人可以想見的論點(參羅檢秋《嘉慶以來漢學傳統的衍變與傳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67頁),葉德輝卻在此批評《漢儒通義》妄議性與天道,又說漢人不講此學,這可以看到兩個問題。首先,講義理的尺度不好把握,說玄向上一分就難免妄論之譏,但也不能全然不論;其次,陳澧跟葉德輝也都承認講義理需要在“不可得聞”處止步,這是可以看出他們一致性的。
但細察陳澧之說,對于那些“不可得聞”的義理,以及不可“傅合”之事,他未嘗沒有明確的意識,他在記錄自家治學心得的《學思錄默記》當中提到:
自來老釋所傅合者,儒家義理之說,若訓詁之學、禮學、史學則無能傅合者也。③陳澧《東塾遺稿·學思錄默記》,《清代稿抄本續編》第77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第385頁上。
后儒見佛書高妙簡易之說而心羨之,乃于五經孔孟之書求高妙之說以敵之,而不知孔孟之書無高妙之說也。如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又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者,如此而已。豈謂人皆可以為堯舜之巍巍蕩蕩乎?④陳澧《東塾遺稿·學思錄默記》,第389頁。
宋賢以釋老為楊墨,說理高妙,導致“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⑤《二程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3頁。因有“反求諸六經”的對治之策。⑥小程說:“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滀,無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見 《二程遺書》,第194頁。其實,宋賢也并非一味務求精微,陳澧的批評未免攻其一點。后文可以看到,這也局限了他對義理的研究。但上舉兩段批評中的后一段,提到“見佛書高妙”欲從儒術“求高妙之說以敵之”,顯有針對理學之意。出入佛老,難免反蹈“傅合”之弊,而“訓詁之學”、“禮學”等等,又是樸學之士規避“傅合”的良方,如此看來,“漢”、“宋”門戶的界限在陳澧這里是隱然而彰的,陳澧在其筆記別處提到了他對宋明理學的看法:
宋諸賢求圣人之道于道經,其心之精,其力之大,真度越古人矣。然多取其高者、精者以為說,其所遺者正不少也,……,在孔子之后者,乃孔子之遺教也,精擇之、潛玩之,可以為修己治身之方者甚多。儒者欲求周公孔子之道,未可一切蔑棄之也。⑦陳澧《東塾遺稿·學思錄默記》,第406頁。
解釋辯論者多,躬行心得者少,千古如斯,良可浩嘆。雖圣賢復起,殆亦無如之何。宋明講理學如此,今人講經學亦如此,即晉之清談、唐之禪宗亦如此。⑧陳澧《東塾遺稿·學思稿通論》,《清代稿抄本續編》第77冊,第529頁上。
前引文中,陳澧強調,人人有向上之機,并非就是說人人可以干出堯舜一樣“巍巍蕩蕩”的事業,這正是一味于儒術求“高妙”的問題所在。結合本處所引,可知陳澧對理學的批評,還是著重于宋明以來理學意見紛起、淪為俗學的問題之上。但是在他看來,當時“講經學”的人們,未必也就高明許多。如宋儒末流之蔑棄古人善言,時人也有未得指出。因此,陳澧提出了一個積極的說法,亦即在古人之書中,發現求之過高的宋儒之所遺,也就是前文所說的“宋儒精理多本漢儒”。葉德輝看出陳澧所言“非漢儒所究心”,即使其說成立,后人欲求道,也未嘗不可在前人未必究心之處精擇潛玩。陳澧究心漢儒未究心處,正在于求宋人之所遺,以匡正今人少“心得”之弊。其《東塾讀書記》引吳派大師王鳴盛(1722-1798)語:
王西莊云:學者若能識得康成深處,方知程朱義理之學,漢儒已見及。程朱研精義理,仍是漢儒意趣,兩家本一家,如主伯亞旅,宜通力以治田,醯醢鹽梅,必和劑以成味也。澧謂昔之道學家,罕有知漢儒見及義理之學者,更罕有知程朱即漢儒意趣者。近時經學家推尊康成,其識得康成深處如王西莊者,亦不多也。①陳澧《東塾讀書記·鄭學》,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276頁。
因此,就有了《漢儒通義》這一陳澧自許為其學精要的著述,他在本書的序言中提到:
漢儒說經,釋訓詁、明義理,無所偏尚。宋儒譏漢儒講訓詁而不及義理,非也。近儒尊崇漢學,發明訓詁,可謂盛矣。澧以為漢儒義理之說,醇實精博,蓋圣賢之微言大義往往而在,不可忽也,謹錄其說以為一書。漢儒之書,十不存一,今之所錄,又其一隅,引申觸類,存乎其人也。節錄其文,隱者以顯,繁者以簡,類聚群分,義理自明,不必贊一辭也。竊冀后之君子祛門戶之偏見,誦先儒之遺言,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是區區之志也。若門戶之見不除,或因此而辯同異、爭勝負,則非澧所敢知矣。②陳澧《漢儒通義·序》,《續修四庫全書》第952冊,第383頁。對《漢儒通義》的研究有,楊思賢《論〈漢儒通義〉》,《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第113-120頁。曹美秀《〈漢儒通義〉析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0期,2007年,第267-309頁。曹、楊二文強調了陳澧編排分類的意義,但認為其意義有限。曹氏還承胡楚生之論,認為與《近思錄》的精心編排相比,《漢儒通義》的編排粗糙已甚。
這一著述宗旨是前引文的一個展開,其所以救時弊,一方面是祛除門戶偏見,這是人所共知的意思;另一方面,講“宋儒精理多本漢儒”的目的,正是補宋賢之所遺的、明白的“古賢之微言大義”。以下是陳澧摘錄的《爾雅》、《說文解字》和趙岐(?-201)的《孟子》注文、鄭玄(127-200)的《禮記》注文以發明漢儒論“心”、“性”之微言的部分:
趙氏《孟子章句》曰:圣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告子章句上
又曰:圣人受天性,可庶幾也而不可及也。萬章章句下③陳澧《漢儒通義·圣人》,第392頁。陳澧的“調和漢宋”,在當時和后代都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可參考於梅舫《學海堂與漢宋學之浙粵遞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231-249頁。作為陳澧本人“調和漢宋”的“精微之作”,《漢儒通義》自然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褒貶,張循簡要討論了這個問題,見《道術將為天下裂》,第192-195頁。
《釋名》曰: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也。
釋形體
趙氏《孟子章句》曰: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后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 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盡心章句上④陳澧《漢儒通義·心》,第400頁。
《說文》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從心,生聲。
心部
《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鄭《注》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
趙氏《孟子章指》曰: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相懸,賢愚舛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告子章句上章指
又曰:守正性者為君子,隨曲拂者為小人也。同上
又曰: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赤子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粗矣,孟子精之,是在其中。同上
又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章句》曰: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
《禮記·禮運》: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鄭《注》曰:言人兼此氣性純也。①陳澧《漢儒通義·性》,第401-402頁。
以《釋名》、《說文》中的單字訓解開始,然后分家條舉漢儒諸說作為解釋,與《孟子字義疏證》和《性命古訓》的研究方法略有不同,條理更為分明,陳澧的目的在于呈示各家漢儒各自“義理”,因而沒有雜引漢儒之言去陳述與“清凈寂滅”相反的“義理之正”。然《通義》所舉漢儒“心”、“性”之說很是簡略,真能使讀者見宋明“復性”、“良知”所本,且發明宋儒窮理之所遺嗎?且觀《通義》所錄“告子一之,知其粗矣,孟子精之,是在其中”,可知如非“精之”則絕不足以明“善性”之“天生”。依陳澧此處的擇取來看,宋儒專取“精者”為說的眼力,實未可以厚非。陳澧一方面認為宋儒因追求高遠、精深而遺落漢儒微言,但在類聚漢儒微言時又無可回避地要正視宋儒的思路,在《讀書記》論朱子談窮理、讀書的部分,可以看到他對這種張力的一個處理:
朱子既云窮理必在乎讀者,而此三說,則以讀書為第二事、第二義,……,窮理為第一事,第一義也。其云所以要讀書,又云圣人教人須要讀這書,即所謂窮理必在乎讀書也。然則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一義必在乎第二義也。②陳澧《東塾讀書記》,第321-322頁。
于老莊、明儒義理之學用力頗深的劉咸炘(1896-1932)譏之云:③劉咸炘的義理學思想,可參考拙文《論劉咸炘的學術思想與浙東學術》,《詩書畫》2017年第3期(總第25期),第60-73頁。
《論語》開卷學而時習之。此何學也,便當認明。陳蘭甫解之曰:學乃讀書。若學專謂讀書,則孔子亦何異于百工技藝,而徒言不行,且并百工技藝之不若矣。④劉咸炘《文史通義識語》,《推十書甲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070頁。
陳澧、黃式三諸人,則以調和漢、宋名世。或譏其模棱附會,然漢儒非不言義理,宋儒非不言訓詁,則固實言也。顧澧與式三仍是長于訓詁考據,于宋、明儒所究者,則置之不講,是固顯然為朱派之傳。前之兼采,后之調和,與其為之畸形,無寧謂之本相耳。⑤劉咸炘《近世理學論》,《推十書甲輯》,第1275頁。
漢與宋,考據與義理,大氐交互,有偏兼之異而非不相容,其不相容者,何耶?曰:斥陽明而已。此漢、宋兼采,漢、宋調和,與專宗漢師、專守程、朱之所同也。⑥劉咸炘《近世理學論》,《推十書甲輯》,第1276頁。
劉咸炘在強調學“不專謂讀書”的基礎上,指出這種以窮理為讀書的研究方式問題在于置宋、明儒所究義理于不講。也就是說,不僅以讀書、抄書的方式所類聚的漢儒微言未見大義,陳澧“不求宋儒高妙”的預設更關閉了他切實講論宋儒義理的可能。劉咸炘還提到,“斥陽明”是這種鳩合漢宋學風的一個問題表征,由此觀之,“程朱義理乃漢儒意趣”,正是陳澧不講義理、籠統排斥陽明學的地方。這樣,劉咸炘就把陳澧批評宋明理學“解釋辯論而無心得”的話回敬給了陳澧。
陳澧以讀書、抄書研究義理之學,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一種困境:漢學傳統的學者發現,陳澧所類聚者適為前人瑣細之處,稱不上“漢學”;此傳統之外的學者發現,陳澧不講宋明儒者所講之學,故稱不上“宋學”。在此,筆者倒是希望結合陳澧的語境作一折中:前文說到,陳澧之類聚漢儒微言,為宋學“正本清源”,一層重要的意思還在于救時人不講宋學,乃至不論一切義理的弊病,其所救非僅宋明理學之弊,還有時人不論漢學義理之弊,劉咸炘也承認“漢儒非不言義理”乃是實言。陳澧煞費苦心,在后人葉德輝眼中的“漢儒所未究心處”發現漢儒非不言之義理,正是《漢儒通義》的可貴之處。
陳澧逝世三十馀年后,在北大講授《中國哲學史》的陳漢章(1864-1938)為課程編寫講義,其發端如下:
中國哲學,惟宋元明有學案,宋以前并付缺如。前有日本人,今有四川謝君,各為之史,尚未及傾群之瀝液,發潛德之幽光。昔陳蘭甫先生嘗綜述漢以下至今學術,未成,止成三國一卷。不揣梼昧,意欲庚之。⑦陳漢章《中國哲學史》,《陳漢章全集》第5冊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頁。筆者對引文的標點,與《陳漢章全集》有一定出入。
陳漢章的漢學背景頗為深厚,《榖梁傳》名家柯劭忞(1848-1933)有“當代經學,伯陶第一”之譽。①牟潤孫《蓼園問學記》,《注史齋叢稿》,第540頁。轉引自桑兵《民國學界的老輩》,《歷史研究》2005年06期,第23頁。這里,他將“中國哲學”與中國“學術”等觀,因此作“中國哲學史”亦即承黃宗羲(1610-1695)所著兩《學案》、陳澧所著《讀書記》,述中國歷代之學術。相比以“道術”類比哲學、以理學眼光整理中國義理之學的同事陳黻宸(1859-1917),陳漢章的視野看起來更加開闊。②可參考拙文《論陳黻宸和他的〈中國哲學史〉》,《詩書畫》2017年第1期(總第23期),第2-16頁。在論述漢代學術時,陳漢章針對漢儒對“心”這一重要概念的認識,做出了與陳澧不同的判斷:
伏生作《書傳》四十一篇,非謹訓詁而已,……,又曰:“心之精神是為圣。”(《孔子集語》引。)為楊慈湖言心所本。《慈湖遺書》以心之精神是謂圣一語為道之主宰,明湛若水著《楊子折衷》辨之。紀昀謂《孔叢》偽撰先圣語,不知實出伏生書。與宋學可一以貫之矣。③陳漢章《中國哲學史》,第6-7頁。楊簡得力于《孔叢子》這一文句的問題,一直以來都為人所知,對其學術史的梳理可參考趙燦鵬《“心之精神是謂圣”:楊慈湖心學宗旨疏解》,孔子研究,2013年02期,第76-88頁。
《孔叢》偽書,獨此一段,讀之令人感憤不已。④陳澧《東塾讀書記·諸子書》,第233頁。這是在贊許《孔叢子》中的“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巳,則夷狄之用將麋于衣食矣。殆可舉棰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巳乎”一說。
紀昀(1724-1805)對《孔叢子》的判斷,是清代“漢學家”批評理學游談無根的常見形式:不過是抄書,還抄成了偽書。陳漢章此處正是從漢學的角度為理學做了辯護,但也充分體現了“宋儒精理多本漢儒”的清學思路:不過還是在抄書。相比之下,陳澧《讀書記》仍未論及《孔叢子》此語所本以及學術史意義。但陳漢章這里對“心”的討論著墨不多,不便進一步展開比較,茲再取陳氏《哲學史》述漢儒“性”論之說:
賈子隆禮法荀子,而言性不取荀子。《勸學》曰:“舜何人也,我何人也,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圣之名。”《保傅》曰:“胡亥視殺人若刈草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習道之者非理故也。”是賈子以人皆可以為舜,而性非本惡。《六術》曰:“道、德、性、神、明、命,六者德之理;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人有仁、義、禮、智、信、樂,謂之六行。教因人所有,以之為訓。《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謂之六藝。”《道德說》曰:“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為一氣。性,神氣之所會也。”其論性較董子為精。而又以氣有明有濁,故性之材不同,《連語》曰:“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不肖人必離。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則分性為二。”宋儒有氣稟之說,賈子已言及矣。⑤陳漢章《中國哲學史》,第12-13頁。
陳漢章以賈誼(前200-前168)《新書》的文本為基礎,較《通義》更為細密地陳述了宋儒論性如何本于漢儒。本段的重點是兩個論點:賈誼以為性非本惡,人皆可以為舜;賈誼認為人皆可以為舜之性,有人倫之理存乎其中,只是性雖然為神氣之聚、有本然之善存乎其中,但是因氣有明濁,各人才性不同,故賢不肖稟性非一。前者暗指賈誼論性講性善,與宋儒相近,后者明指宋儒“氣秉所拘”的通見其實漢儒已經言及,“兩家本一家”。然查《朱子語類》,可知漢、宋儒者的性論仍有微妙而不可忽略的差別:
漢儒董仲舒較穩。劉向雖博洽而淺,然皆不見圣人大道。賈誼司馬遷皆駁雜,大意是說權謀功利。說得深了,覺見不是,又說一兩句仁義。然權謀已多了,救不轉。⑥黎靖德《朱子語類·歷代二》,《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合肥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02頁。
或問:“董仲舒:‘性者生之質也。’”曰:“其言亦然。”⑦黎靖德《朱子語類·孟子九·告子上·生之謂性章》,《朱子全書》,第16冊,第1876頁。
童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圣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知自貴于物,然后知仁義;知仁義,然后重禮節;重禮節,然后安處善;安處善,然后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墻,不分明端的。”⑧黎靖德《朱子語類·戰國漢唐諸子》,《朱子全書》,第18冊,第4246頁。
“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董仲舒云:‘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性本自成,于教化下一‘成’字,極害理。”⑨黎靖德《朱子語類·莊子書·外篇天地第十二》,《朱子全書》,第18冊,第3915頁。
此處摘錄、排比了朱熹(1130-1200)對于漢儒論“性”的看法。從道學的觀點看(From a Neo-Confucian Point of View),即使漢人中最為“純儒”的董仲舒(前179-前104),也還是見道糊涂,不過時有嘉言而已。在性論的問題上,董仲舒不知“性本自成”,或者“性善本自成”,因此見得“性者生之質”,而不識其中有善。等而下之的賈誼、馬遷(前145-?)則被斥為只是“說一兩句仁義”,與“時而見得”的董仲舒都相去甚遠。陳澧不欲在儒書中“求之過高”,乃至認為“程朱義理漢儒已見及”,在朱子看來恐屬見之不明、求之不切。陳澧和陳漢章之“漢宋論理,意趣相同”,對宋儒之“道”正有隔膜,從道學的觀點看,正好可以用前引陳澧抄錄的趙岐之論批評,“告子一之,正見其粗”。
總的來說,正是沿著陳澧抄錄、類聚漢儒微言的研究路數,陳漢章發現了漢、宋儒者在“心”、“性”概念上更多的“一致”之處。然而細察宋賢之說,陳氏的調停,恰是展露了漢、宋儒者性論的沖突。作為“近人治義理者”的另一派,與陳漢章同樣具有深厚清代漢學素養的劉師培并未循“漢宋意趣相同”、“宋儒論理本漢儒微言”的路數進行思考。他對漢、宋儒者論“心”、“性”之說展開了更為深刻、獨立的反思,結論也更為精密。而“與之同術”的樸學名家章太炎(1869-1936),在晚年卻發展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解釋漢儒義理之學的道路。
正名論理和主觀之學:《國粹學報》時期的劉師培和晚年章太炎的觀點
在一九○五年,劉師培在《國粹學報》上先后發表了《理學字義通釋》和《漢宋學術異同論》。①劉師培跟章太炎在1902年相識,此文發表時,章太炎尚在獄中。他們的學術史議論有著不少奇妙的相似之處,雖說劉師培發論基本都更早,但是我們也不能就此斷定原創者是誰,這一問題有待另行研究。前者集中反映了他研治義理學的成果,而其研究宗旨則在后者當中表述得更為簡明。除了上章所引述的“近世治義理者有兩派”的文段外,還有一段平章漢、宋得失的話:
及宋儒說經,侈言義理,求之高遠精微之地;又緣詞生訓,鮮正名辨物之功。故創一說,或先后互歧;此在程、朱為最多。立一言,或游移無主。宋儒言理,多有莽無歸宿者。由是言之,上古之時,學必有律。漢人循律而治經,宋人舍律而論學,此則漢宋學術得失之大綱也。②劉師培《漢宋學術異同論·序》,第1586頁。
在“毋求之高遠精微”的原則之外,劉師培還強調了“學必有律”,并認為此乃漢人之得和宋人之失的大綱。《理學字義通釋》的序言恰好可以作為這一大綱的注釋來看:
夫字必有義。字義既明,則一切性理之名詞,皆可別其同異,以證前儒立說之是非。近世巨儒,漸知漢儒亦言義理,然于漢儒義理之宗訓詁者,未能一一發明;于宋儒義理之不宗訓詁者,亦未能指其訛誤。不揣愚昧,作《理學字義通釋》,《宋史》撰《道學傳》,然宋人之學,兼倫理、心理二科。若“道學”二字,只能包倫理,不能該心理也。若日本“哲學”之名詞,亦未足該倫理,故不若“理學”二字所該之廣也。遠師許、鄭之緒言,近擷阮、焦之遺說。《周詩》有言:“古訓是式。”蓋心知古義,則一切緣詞生訓之說,自能辨析其非。此則古人正名之微意也。③劉師培《理學字義通釋·序》,《儀征劉申叔遺書》第4冊,揚州:廣陵書社,2014年,第1333-1334頁。
藉助“倫理”、“心理”兩個新名詞,劉師培很好地認識到了宋儒的論域之廣泛,并感知到“理學”這一混全的概念,與新名詞“哲學”并不是重合的。那么“宗訓詁”的義理研究,能在近人的基礎上多做到一些什么呢?下面仍從“心”、“性”兩點切入,觀察劉師培的義理研究:
許氏《說文》“性”字下云:“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從心,生聲。”“情”字下云:“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從心,青聲。”……,人性秉于生初,情生于性,性不可見。“情”者,“性”之質也;“志”、“意”者,情之用也;“欲”者,緣情而發,亦“情”之用也。無“情”,則“性”無所麗;無“意”、“志”、“欲”,則情不可見,……,《禮記·樂記篇》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文子》、《淮南子》皆有此語,《說文》“才”字下亦有此言。“靜”對“動”言。“靜”也者。空無一物之謂也,未與物接,故空無一物。王陽明言“無善無惡,性之體”,即此旨也。
故性不可見,……,乃前儒之言“性”字者,或言“性善”,……,或言“性惡”,……,眾說紛紜,折衷匪易。乃律以《樂記》“人生而靜”之文,則“無善無惡”之說,立義最精。性無善惡,故孔子言“性相近”,“相近”者,無善無惡者也。《大戴禮》言“形于一之謂性”,言為人既同,則其性亦同。《孟子》以“同類者相似”為性善之徵,似未足為據也。而陽明王氏亦言無善無惡為“性之體”也。然孔子又言“習相遠”者,則以人有心知,與禽獸不同。有可以為善之端,……,亦有可以為惡之端,……,惟未與外物相感,故善、惡不呈。《告子》言“性無善惡”,本屬不誤,但誤其在于不動心。“不動心”者,即欲心念之不起也,已蹈宋儒滅情斷欲之弊。及既與外物相感,日習于善,則嗜悅理義之念生,……,此董子所由言“性必待教而后善”,《易》言“后以裁成,輔相左右民”,《書》言:“剛克”、“柔克”,《中庸》言“修道為教”,皆所以化民也,故《大學》以“止至善”為歸。而陽明王子復言“有善、有惡,性之用”也。但以“有善、有惡”為“性”用,則又不然,夫人性本無善惡。善惡之分,由于感物而動。習從外染,情自內發,而心念乃生。即“意”與“志”也。心念既生,即分善惡。是則有善有惡者,“情”之用,與“性”固無涉也,……,蓋中國前儒,多誤“情”為“性”,……,故東原以情欲不爽失者為“天理”也,乃秦、漢以降,異說日滋。漢儒以陰陽言“情”、“性”……,《說文》亦以陰陽言“性”。又漢儒以“性”為五常,見《白虎通》;又以仁、義、禮、智、信配“性”,謂其取象五行,見《禮·中庸》及《詩箋》;又以五常分合五藏,皆陰陽家言。近儒孫淵如《原性篇》引伸之甚詳。立說已流為迂誕;宋儒之說,尤屬無稽,……,近儒矯宋儒之說,然立說多偏。如東原“心知”即“理義”,其誤一。①劉師培《理學字義通釋·性、情、志、意、欲》,第1339-1346頁。

《理學字義通釋·性、情、志、意、欲》
陳澧先列字義,再排比舊說的規矩,劉師培予以嚴格貫徹。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劉師培將《樂記》的舊說跟陽明“性無善惡”的新說聯系到了一起,但他沒有強調陽明新說原本舊說而來,或者陽明新說等同于舊說,“宋明義理前人已言及”,這是他不同于前人的微妙之處。②例如黃以周(1828-1899)《德性問學說》認同“性必待教而后善”,但是也肯定性具五德之說,與劉師培此處不同。見黃以周《德性問學說》,《黃以周全集》第1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03頁。劉師培的判斷,建立在他對《說文》中“性”字義的理解,以及結合經驗,對“性”和“情”做的嚴格分別之上。劉師培肯定了董仲舒的“性必待教而后善”,這恰與朱熹的批評相沖突,因此他進一步指出,“中國前儒,多誤情為性”。如嚴肅性、情分別,那么陽明為性立一“體用”,以攝善惡的理學化思路也應該被判為錯誤。此外,前引《通義》所錄的《中庸》鄭《注》,同樣是荒誕之說,也是不明情之善惡與性無涉,而以五行強配性中五神,進而成立五常之德。陳澧說得好,漢儒論性,“性在氣中”,如果要進一步分析,將涉及漢儒自然觀與近代學者的差異,此處不贅。
需要注意的是,《傳習錄》論“無善無惡”的文句,其中心詞是“心之體”,而劉師培卻說“無善無惡”指的是“性之體”,這如何解釋呢?筆者發現,《理學字義通釋》中對“心”的討論,跟對“性”的討論非常相似,從義理的角度來說,他幾乎是在把二者當作一個問題研究:
蓋中國之言心理也,咸分體、用為二端。《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此指心之體言之也;又言“發而皆中節”,此就心之用言之也,……,思想者,所以本心念之發動,而使之見諸作用者也。然思想未起前,心為靜體,故宋儒體用之說,實屬精言,……,自《莊子》以“心”為“靈臺”,《庚桑楚》注云:靈臺者,心也。而宋代諸儒,又飾佛書之說,以為心體本虛,不著一物,故默坐以澄觀,重內略外;復飾《易傳》“何思何慮”之說,以不假思索為自然。不知心兼體、用而言,德亦兼體、用而言。使有體無用,即德存中心,又何由明顯其德,而使之表著于外哉?且《孟子》名言:“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心而不思,即孔子所謂“無所用心”矣,豈非宋學之失哉?①劉師培《理學字義通釋·心、思、德》,第1358-1362頁。
跟前文不同的是,劉師培在此非常認可宋儒“體用”之說。②文廷式(1856-1904)回憶,陳澧在看了李顒(1627-1705)和顧炎武(1613-1682)探討“體用”來源的書信后,認為“體用”二字必出釋典,并承認佛學入華使得中國的義理之學日趨細密。如果屬實,陳澧義理觀和“漢學”立場的微妙之處就更值得深入探討了。見文廷式《純常子枝語》,《續修四庫全書》第1165冊,第434頁上。但細看之下,可以發現,他說“體用”之說甚精,恰是因為體用之說客觀上部分起到了分別“性”、“情”不同的作用,跟他之前的說法相合。③承楊耀翔提醒,劉師培區分體、用和性、情,可能與王弼有關。這個猜想跟章太炎、劉師培對魏晉六朝學術史意義的重視也是相符合的。而宋儒對形下之用、情之善惡跟“德”的緊密關系看得不清,以致于他們徒務心體虛靜,“有體無用”。“有體無用”,正好又是程、朱批駁佛教的話頭。④一個明顯的例句是“惟明道語未明白,故或者錯看,謂是收拾放心,遂如釋氏守個空寂。不知其意謂收放心只存得善端,漸能充廣,非如釋氏徒守空寂,有體無用。”見黎靖德《朱子語類·孟子九·告子上·仁人心也章》,《朱子全書》,第16冊,第1919頁。再回到前面的問題,劉師培是否有囫圇“心”、“性”之處?筆者以為,劉師培對二者涵義的判斷,完全以漢人舊訓為標準,故徑直將陽明論“心”之說的看做他論“性”的材料,在他來看,這樣一種“囫圇”是完全有根據的。而明確反對“有體無用”的宋儒,由于在劉師培分別“情”、“性”的觀點下被審視,反而變成了“有體無用”。可以看到,劉師培并沒有走“調停漢宋”的道路,但說他一心發揮“漢儒平易通達,宋儒清凈寂滅”的路子,也不妥當。他指出漢儒“取象五行”同樣“流為迂誕”,與江藩(1761-1831)等人的態度已截然不同。⑤江藩把取象五行的“性有五”之說視為“七十子之微言大義”,跟劉師培完全不同。見江藩《書阮云臺尚書性命古訓后》,《江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4頁。不如說,劉師培在此是從一種絕對的“清代漢學”的觀點出發看問題,古訓明則古經明,不必株守某一前人遺說。⑥這與戴震相似,可參於梅舫《漢學名義與惠棟學統—〈漢學師承記〉撰述旨趣再析》,《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6年02期,第101-103頁。可能真如前文引述,劉師培認為僅僅“辨析其非”則能“心知其意”,而其意本身則可坐實到一詞一字的語義和語用上面。⑦在為《國粹學報》撰稿的時期,劉師培表達過他對“哲學”的理解:“大抵謂宇宙真理,無質無形,僅以不可思議之妙理,顯不可思議之作用而已,故以絕對之名詞,定物質之本體。”(劉師培《左盦外集·中國哲學起原考》,《儀征劉申叔遺書》第10冊,第4529頁。)這樣看仍嫌抽象,對比他在另一處說過的“要而論之,儒家之言‘無’,非指消極之意言,不以‘無’為禁止之詞,如‘無友不如己者’、‘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適,無莫’是。即以‘無’為簡約之詞,如‘無為’、‘無思’之類是。與道家之說殊科。”(劉師培《中國哲學起原考》,第4554-4555頁。)劉師培從語用角度考察儒家言無之辭,認為儒書中并不存在以“無”指涉宇宙本體的用法,因此判斷儒道兩家義理有所不同。這與本文所引內容都顯示劉師培是在通過研究字詞用法,來考察義理。這樣,調停的一條路固然不通,另一條路走下來,似乎不僅離宋儒,也在離漢儒的義理越來越遠。
“二叔”的另外一人章太炎,則走上了另一條不同的道路。章太炎的學術思想與現實政治的發展密切相關,在其人生中后期,有著“轉俗成真”、“回真向俗”和“顯諸用而敦乎仁”的不同階段。在清末民初,知識分子即使能適應急遽變化的社會、思想形勢,對于解決政治、道德問題的信心,也不一定能夠保持下來,思想從開始的激進,傳入保守一側的為數不在少,而章太炎正是其中一例。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對于儒學、尤其是宋明理學的重視是在不斷加深的。⑧可參考拙文《章太炎后期思想二題》,《詩書畫》2017年第2期(總第24期),第152-166頁。對于章太炎的學術尤其是玄學思想與時代精神關系的評論,目前仍以侯外廬《中國近代思想學說史》(重慶:生活書店,1947年)為簡明扼要。對于章太炎和宋明理學的思想因緣,時人李源澄論述最精,見李源澄《章太炎先生學術述要》,《李源澄著作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第1460-1461頁。在一九一七年與學生吳承仕(1884-1939)的通信中,他談到了自己閱讀宋明儒學的心得。開始認為宋明儒者并無“根柢”,論學浮泛,但在讀到了《慈湖遺書》后,有了一些不同的體會:
近更細繹宋明儒言,冀有先覺,然偶中者,什無一二。其于大體,則遠不相逮矣。其中亦有不諱言禪者,只為圓滑酬應之談,未必有根柢也。⑨章太炎《與吳承仕書》,《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2頁。
昨得明刻《慈湖遺書》,觀其論議,能信心矣,故于《孔叢》所稱“心之精神是謂圣”一語,無一篇不道及。蓋明儒所謂立宗旨者,實始于此。而又以“心本不亡不須存,心本無邪不須正”詆諸儒,此殆有壇經風味。其后羅近溪輩,大抵本之。然宋儒不滿思、孟,極詆《大學》者,唯慈湖一人。舉《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語以詆《大學》“正心”之說,此亦他人所不敢言者。然觀其自敘,則仍由反觀得入。“少時用此功力,忽見我與天地萬物萬事萬理澄然一片,更無象與理之分,更無間斷。”此正窺見藏識含藏一切種子恒轉如瀑流者,而終不能證見無垢真心。明世王學亦多如是。⑩章太炎《與吳承仕書》,《章太炎書信集》,第303頁。
楊簡(1141-1226)是章太炎晚年非常關注的一位理學家,太炎此處認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的斷句,展現了他跟近世論義理學者們不同的眼力。他并未像陳漢章那樣強調《孔叢》論心原本《尚書大傳》,所以慈湖立說有漢人為之先聲。太炎對慈湖之學的稱許落腳于慈湖自己的“反觀”實踐上,并用“藏識”這一唯識學概念確定了慈湖所證階位,這已非之前的“漢學家”論義理者所能知。在一九二○年的演講中,太炎將他治義理學的方法做了簡明的闡述,要在發揮理學家“驗心”之法、重視主觀實驗:
中國哲學,由人事發生,人事是心造底,所以可從心實驗,心是人人皆有的,但是心不能用理想去求,非自己實驗不可。中國哲學,就使到了高度,仍可用理學家驗心的方法來實驗,不像西洋哲學始可實驗,終不可實驗,這是中勝于西的地方。印度哲學,也如是。①章太炎《研究中國文學的途徑》,《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88-289頁。張永義已經點出了章太炎此說在方法論上相對于漢學的進步意義,見張永義《從〈東塾讀書記〉看陳澧的漢宋調和論》,《中國思想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12年。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章太炎這里雖然談到中國、西洋的哲學,但他重點是在強調中國義理之學的特殊性,并非完整闡述他對“哲學”概念的容受。
研究義理之學的主觀實驗之法,在太炎首次赴日之時的演講中,就已有端倪:
其書既為記事之書,其學惟為客觀之學,黨同妒真,則客觀之學,必不能就,此劉子駿所以移書匡正也。若諸子則不然,彼所學者,主觀之學,要在尋求義理,不在考跡異同。既立一宗,則必自堅其說,一切載籍,可以供我之用。②章太炎《論諸子學》,《演講集》,第49頁。
“一切載籍”可為我親證所得之說所用,《孔叢》是否原本伏生之書,自然就不重要了。其實早在一九一六年,經過數年來與太炎的書信過從,吳承仕就著有《王學雜論》,其中有如下論性之說,可以窺見太炎此期的義理學思想:
在昔言性者五家,各據一隅,未能契會中道。唯文成亦言,性無定體,亦無定論。有自發用處說者,有自源頭處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只是一性。但所見有淺深,執定一邊,便為不是。此誠眇達神旨之談,足以解紛齊物矣。然以是相徵,則又自成乖返。詳夫阿賴耶識,含藏萬有,為染凈依,局在一性,即無受熏持種之用。故無覆無記。文成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無善無不善,性原如是者,庶幾近之。而異時又言,性無不善,至善者心之本體。夫實性離言,無可遣立,假名至善,亦無大過,而文成故見不及此。
文成每以仙佛并稱,少時又致力于導引之術,是于邪正教理,且未能明辨。借使嘗讀內書,不過禪宗語錄之等,五法三自性之義,或未之前聞,……,而自性若何,行相若何,果為第八,抑為第七,是一是二,則釁聞罕漫而不昭察。③吳承仕《王學雜論》,《國故》1916年第1期。章太炎評論吳承仕此作:“略為紬繹,所見大致無差,……,至余姚所謂良知,大概與藏識相似。要之言自證分為近,但見暴流恒轉,未睹不生不滅之真如。”見章太炎《與吳承仕書》,《章太炎書信集》,第307頁。1917年。
吳承仕認為陽明言“性無定體”為不執發用、源頭和流弊的精論,是正確的。比起劉師培說“性無善惡”跟“人生而靜”的漢儒古義相契,吳承仕藉“藏識”概念之助,對性無善惡論的客觀價值做出了抽象但更為整全的評價。但看吳承仕下一段的分析,說陽明不讀佛書,不知五法三自性的概念,則使人有疑:各人的反觀親證,是否就能跟佛典所說聯系起來,導出確切而非“圓滑”的義理之學呢?如濫用“七識”、“八識”等概念泛泛而稱,不詳細論證,反成另一種讀書空辯,毫無意義。④方以智(1611-1671)評清涼澄觀(737-838)以唯識名相分別三教高下說:“清涼言儒止見及六識,老、莊見及七識,佛始見破八識也。將以虛空破八識乎?以空為宗,佛云外刀,有疑者乎?此論銷礦成金。繼父必孝,可信政府宰君民,財成收化育。破識用識,君臣道合。所貴家督,全在兒孫。止有一寶,何更嘵嘵生死有無支蔓哉?須信腐面,可成美醬。莫將燒酒,強灌罪人。”(方以智《藥地炮莊·總論中》,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年,第71頁。)方以智肯定了清涼澄觀所持唯識義理之精確,然不認為在義理問題上,高下精粗能代表是非,更不認為能夠代表人們就受用高者精者,不受用低者粗者。太炎在一九二一年回應呂澂(1896-1989)對其佛學研究的批評時,透露了他對“心體”的認識,以及如何能把“藏識”概念引入對心體的討論之中:
一,現量即親證之謂,所謂實驗也。各種實驗,未必不帶名想分別,而必以觸受為本,佛法所謂現量者,不帶名想分別,但至受位而止。故實驗非專指現量,而現量必為實驗之最真者。二,前書本云自心非意想所能到,誤書作意識,致啟爭端。所謂自心指心體言之,即藏識也。觸作意受想思五位,六七八識俱有之。欲證心體,不恃意中想位,而恃意中受位,(實則證外境亦然。證境出感覺,證心由直覺,感覺直覺皆受也。)若徒恃想,則有漢武見李夫人之誚。至于思則去之益遠矣。(凡諸辯論,皆自證以后,以語曉入耳。若無自證,而但有辯論。譬瞽師論文采,聾丞論宮商,言之雖成理,終為無當。)①章太炎《與李石岑書》,《章太炎書信集》,第725頁。
此處太炎明指心體即為藏識,劉師培那里還顯得不夠清楚的心、性、情和體用,太炎藉其“自證”的經驗道出。“現量不帶名想分別”、“恃自家所受不恃所想”,給了太炎以反觀自證的經驗來確定概念名義、判別不同名義異同的充分自由,但問題是這種自由在探討義理時應該表現到什么程度?探討義理仍然不能離開語言,但以此為例,在公共語言中,“觸”猶可解,但是并感覺直覺為一爐的“受”就不好說了。如果人人都藉口“反觀自證”,而自證的體驗又是無限的,不受語言制約,“怎么說怎么有理”,轉成“圓滑”之說,乃至被淺人竊取,徒生門戶辯論。②對于學術史的研究者來說,中國的“驗心”、“自證”概念,是徘徊在神秘主義和哲學思辨之間的,可說不可說,分寸不好拿捏,這是從馮友蘭(1895-1990)開始就產生的問題(實際上也許更早)。可參考劉保禧《陳漢生與牟宗三論直覺與神秘主義》,《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29期,2013年1月,第33-78頁。先按下此處不表,來看看太炎在一九二四、二五年間,研究宋明理學的一些實踐。太炎于一九二四年致信吳承仕說:
次則宋明理學,得精心人為之,參考同異:若者為摭拾內典,若者為竊取古義,若者為其自說,此亦足下所能為。昔梨洲、謝山,不知古訓,蕓臺、蘭甫,又多皮相之談,而亦不知佛說。③章太炎《與吳承仕書》,《章太炎書信集》,第320-321頁。整理文“蕓臺”誤作蘭臺。
由此觀之,吳承仕之前的《王學雜論》雖然“大致無差”,但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吳承仕此后未見發表有關宋明理學的研究著作,倒是太炎在次年親著《康成子雍為宋明心學導師說》,再次論及慈湖之學和“心之精神之謂圣”:
漢人短名理,故經儒言道亦不如晚周精至。然其高義儻見,雜在常論中者,遂為宋明心學導師。鄭康成說致知在格物,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于善深,則來善物。其知于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是乃本于孔子之言“我欲仁,斯仁至矣”,從是推之,我欲不仁,斯不仁至矣。其后王伯安為知行合一之說,則曰“知之篤實處即行,行之精明處即知”,其于鄭義無所異矣。王子雍偽作《古文尚書》及《孔叢子》,《古文尚書》所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乃改治孫卿所引《道經》之文,而宋儒悉奉以為準,然尚非其至者。《孔叢子》言心之精神是謂圣,微特于儒言為超邁,雖西海圣人何以加是?故楊敬仲終身誦之,以為不刊之論。前有謝顯道,后有王伯安,皆云心即理,亦于此相會焉。此皆舉其犖犖大者,非若陳氏漢儒通義,毛舉碎文以相附也。夫以康成純德高行,其中宜有所得者。子雍雖寡過,子雍與司馬宣王為婚姻,然未嘗為謀主。其后毌丘儉稱兵,略為景王畫策耳。世以為助晉篡魏,則誣也。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性嗜榮貴而不求茍合,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劉寔以為三反,其行不能令人無間,然所言能如是。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釋氏因有貧女寶珠之喻,豈不信夫?④章太炎《康成子雍為宋明心學導師說》,《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續編》,第50頁。原刊1925年《華國月刊》。鄭玄、王陽明“格物”說相沿襲的論點,亦見于同期刊出的《致知格物正義》一文,《太炎文錄續編》,第47頁。又,承趙朝陽指點,太炎在1924,25年給吳承仕的書信,以及1935年的演講當中,根據《尚書正義》引《晉書》的資料,將偽《書》經文的作者定為鄭沖(?-274),這提示我們也許應該把此文的創作放到24年之前。

《康成子雍為宋明心學導師說》
章太炎此文有兩處推論非常值得重視。首先,相對于劉師培“性無善惡,情有善惡”的論斷,章太炎更機敏地將目光投到鄭玄之“格物”與陽明之“知行”兩個概念上面,鄭玄對人之格物可以“來善、來惡”的注解,是一個很經驗的說法,章太炎巧妙地折入“可善可惡”之中,從一個不僅在經義上、也在常識上更直接、自然的角度為陽明的“無善無惡”之教找到了漢代的先驅者。①黃以周云:“前人咸謂鄭君注經,詳訓詁,略理義。予謂鄭注之理義,多函于訓詁中,引而不發,躍如也。能者從之,其鄭注之謂乎!”(王兆芳《儆季子粹語》,《黃以周全集》第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99頁)太炎此處所作發揮,使黃以周處之,其“引而不發”之義不一定相同。但是可以看到,太炎就漢儒名言論列宋賢精理,而非如陳澧《通義》“毛舉碎文以相附”,能與黃以周此論呼應。其次,章太炎在承認《孔叢子》、《古文尚書》文句乃王肅偽作之后,反而將之視為反映王肅(195-256)論心之說的材料。二者明面上并未越出清代漢學者辯正作者、考釋文義的范圍,畢竟鄭玄之解格物,王肅偽《尚書》、《孔叢》都是簡明易見的事實,但如前文所述,強調主觀之學在于自證自得的章太炎,對“性無善惡”、“心之精神”等問題,并不將之視為“高妙”而不可究詰者,因而其立言究竟與漢學家們絕不相同。既然是“自證自得之學”,那么王肅之品行又如何解釋呢?答案是極具佛教,或者說心學意味的“貧女寶珠”之喻。②《孔叢子》中“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圣”一語,是孔子對子思“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之問的答復,是在泛泛而論人的認識能力。楊簡的“某信人心即大道”則轉而將“心之精神”發揮為了更富道德意味的人之良能。章太炎以凡夫皆有佛性的譬喻對比,是抓住了慈湖用意的。在這里來講,就是說王肅雖品行有虧,但因為其仍有良知良能,所以仍有讜論善言,不可因人廢言。《孔叢子校釋·記問第五》,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96頁。
可以說,章太炎和前文述及的劉師培,是分別走了清季治義理的儒者“調停漢宋”和“以漢正宋”兩條不同的路,但又以各自的方式逾出了傳統的界限。章太炎以“反觀自得”的標準,以唯識的概念理解宋明理學,在創作《齊物論釋》之后又完善了自己對理學的認識,進而在漢儒的“常論”中發現了其自得之高義。劉師培則以“客觀”的古訓為標準,極力規避“主觀”、“自證”在義理之學中產生的問題,在批駁宋儒不遵古訓、字義不明之后,漢儒古訓中本身字義不明的部分也予以否認,但漢、宋儒學中可取之“義理”的范圍遂小之又小。相比之下,章太炎對“主觀之學”的認同似更能給義理之學帶來更多的生命力,但如前文所說,反觀自證所得的義理,表達在語言上總是很難清楚的,在同時提倡嚴密的唯識學概念的情況下,這種問題會暴露得更清楚:也就是說,主觀自得的義理之學并不一定要求特定的語言,更不一定要求唯識學帶來的“精確”語言。如果在避免“圓滑”談學的同時,憑借主觀自得帶來的自由、借取“精確”的唯識概念充實語言,恐怕適得其反。
及至一九二七年后,太炎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高妙的“無垢真心”,甚至放棄了從語言對自得之義理進行闡述的努力:
當晏坐時,胸中澄徹,不知我之為我,坐起則故我復續,齊死生尚易,破主宰最難,即孟子尚墮神我之見,況自此以下者乎?然胸中樂境,與匯節兩不相妨,即此已自可得。前書所謂不能學孔、顏,且學孟子、白沙,蓋亦自顧駑劣,不得已而求其次也。③章太炎《與徐仲蓀書》,《章太炎書信集》,第877-878頁。
上文中,太炎自述自己修證“無生”的工夫雖勤,但仍未造“無我”之境,表明他跟慈湖等人在伯仲之間。不過胸中樂境雖然不能登峰造極,但俗世節義無虧,也算是“自得”了,只是將主觀自得的胸中樂境全部置入靜坐的感受當中,則很難在語言上講有什么“主觀自證”的義理之學了。章氏在“義理之學”上的極限,似乎就只是在《康成子雍為宋明心學導師說》中,藉由“主觀自證”帶來的自由突破了清代漢學對宋儒乃至佛教和漢儒義理的隔膜而已。④一切也有天時的因素,如果讓龔自珍、魏源得見楊仁山從東國攜來的《成唯識論》、《瑜伽師地論》,他們會說些什么呢?回頭看看陳澧的話,“豈謂人皆可以為堯舜之巍巍蕩蕩乎”,說得相當不錯,人皆可以內證堯舜之所證,但也僅此而已。
慧命與共法:熊十力、牟宗三的觀點
章太炎一生從未在大學任教,而在北京大學任教過的陳漢章、劉師培兩人也沒有在中國哲學研究的學術史上留下很多痕跡。二十世紀第一代新儒家之一的熊十力(1885-1968),曾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執教有年,為今日“中國哲學”學術史當中的一個重要人物。⑤劉述先《現代新儒學研究之省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0期,2002年,第367-382頁。他對章太炎的評價經歷過一個有趣的轉變過程:
余曩治船山學,頗好之,近讀余杭章先生建立宗教論,聞三性三無義,益進討竺墳,始知船山甚淺。⑥熊十力《心書》,《熊十力全集》第1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頁。
聰明之士輒喜摭拾玄言,而不肯留心經論,求其實解。昔人如蘇軾之于禪,今人如章太炎之于法相,皆是也。⑦熊十力《十力語要》,《熊十力全集》第4卷,第84頁。后來的《體用論》中,也有對章太炎的類似評價。對于熊十力等人的這些批評,姜義華早已發現,見姜義華《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2-323頁。
遯初豁達大度。同盟會人皆暴徒,彼獨留心西洋政治制度等等,惜于國學欠留心。其時章太炎輩,皆考據文章之士,本無知本國學術者。⑧熊十力《與徐復觀 陳雪屏》,《熊十力全集》第8卷,第546頁。
儒家關于哲理方面,固稱義理之學。而諸子學,亦合入義理一科。即佛學亦當屬此,……,印度傳來之佛學,雖不本于吾之六經,而實在吾經學之可含攝。其短長得失,亦當本經義以為折衷。①熊十力《讀經示要》,《熊十力全集》第3卷,第560頁。
在熊十力未進入內學院之前創作的讀書筆記《心書》當中,章太炎有著很高的地位,是熊十力進討佛學的引導者。而在三十年后的《十力語要》和致徐復觀(1903-1982)書信當中,章太炎則變成了蘇軾(1037-1101)一流“圓滑”談玄的人物。即有學術,也不過考據文章之類,對于“國學”、“學術”全然不解。很有趣的是,章太炎自己也曾指蘇軾、焦竑(1540-1620)輩為“圓轉滑易”,又將內學院歐陽竟無(1871-1943)視為佛學研究者當中的“惠定宇、孫淵如”之流,能對治“圓轉滑易”的文士病,但絕不能適應“主觀之學”進一步發展的需要。②可參考拙文《章太炎后期思想二題》。又,《菿漢微言》云:“列子為魏晉間人偽撰之書,猶能解此。惠定宇、孫淵如輩所見,乃不逮魏晉清談之徒遠矣。”見章太炎《菿漢微言》,《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4頁。第一點被熊十力回敬給了章太炎自己,而第二點則由熊十力“接著講”了下去,以一種同樣主觀、自證、自得,但是又不完全一樣的方式。③《讀智論鈔》:“法身佛者,猶云宇宙本體。剋就其在人言之,即論語所言仁,孟子所云本心,宋儒云德性之知,陽明云良知,吾新論云性智,皆指目此也。”見熊十力《讀智論鈔》,《熊十力全集》第4卷,第596-597頁。太炎以為陽明之良知為阿賴耶識,可與參看。然熊子《新論》對阿賴耶識有所揚棄,是與太炎完全不同的,見熊十力《新唯識論(語體文本)·答問難》,《熊十力全集》第3卷,第485-486頁。
到了一九七四年,熊十力的學生牟宗三(1909-1995)先后完成了《才性與玄理》、《心體與性體》和《佛性與般若》,為《才性與玄理》的第三版寫了一篇短序,里面說:
此書除疏通人性問題中“氣性”一路之原委外,以魏晉“玄理”為主。魏晉所弘揚的玄理就是先秦道家的玄理。玄理函著玄智。玄智者道心之所發也。關于此方面,王弼之注《老》、向秀郭象之注《莊》發明獨多。此方面的問題,集中起來,主要是依“為道日損”之路,提煉“無”底智慧。主觀的工夫上的“無”底妙用決定客觀的存有論的(形上學的)“無”之意義。就此客觀的存有論的“無”之意義而言,道家的形上學是“境界形態”的形上學,吾亦名之曰“無執的存有論”。此種玄理玄智為道家所專注,而且以此為勝場。實則此種工夫上的無乃是任何大教、圣者的生命,所不可免者。依此而言,此亦可說是共法。依此,魏晉玄理玄智可為中國吸收佛教而先契其般若一義之橋梁,此不獨是歷史的機緣,暫作比附,而且就其為共法而言,盡管教義下的無與證空的般若各有其教義下的專屬意義之不同,然而其運用表現底形態本質上是相同的,……,吾人不能說佛家的般若智來自魏晉玄學,當然亦不能說道家的玄智是藉賴佛家的般若而顯發。這只是重主體的東方大教、圣者的生命,所共同有的主觀工夫上的無之智慧各本其根而自發,……,此非來自佛老,乃是自本自根之自發。此其所以為圣者生命之所共者。若不透徹此義,必謂陸王是禪學,禪之禁忌不可解,而“無善無惡”之爭論亦永不得決,此非儒學之福也。
讀此書者若真切于道家之玄理玄智,則最后必通曉其為共法而無疑。如是,則禁忌可解,而又不失各教之自性。若不真切,而視為浮智之玩弄字眼,則是自己之輕浮,必不能真切于圣者生命之體用也。夫立言詮教有是分解以立綱維,有是圓融以歸具體。“無”之智慧即是圓融以歸具體也。焉有圣者之生命而不圓融以歸具體者乎?分解以綱維有異,而圓融以歸具體則無異也。此其所以為共法。吾初寫《才性與玄理》,繼寫《心體與性體》,最后寫《佛性與般若》,經過如此長期之磨練,乃知義理之脈絡與分際自爾如此,故敢作如此之斷言,非如蟲蝕木,偶然成字也。④牟宗三《才性與玄理》第三版《序言》,《牟宗三先生全集》02卷,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年,第7-8頁。
此序與《圓善論》的關系,有待之后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哲學思想史的學者進一步探究。此處筆者想強調的,是其中“圣者的生命”和“圣者的共法”兩點,跟章太炎通過“主觀自證”的路徑發掘漢、宋儒者義理的努力頗可呼應。經過對唯識學和哲學的深入學習,熊十力、牟宗三擁有的探討中國“義理”的武器,看起來比起章太炎的“藏識”、“神我”等片段更加趁手,相應地,從古人的義理之學中提煉出的更加精確、細致的概念,也更加能為今天的中國哲學研究所吸納。可以說,先圣后賢兩不相知,無繼志述事之誼,但論學卻能冥會,正是研討義理之學的魅力所在。⑤《菿漢微言》:文、孔、老、莊是為域中四圣,冥會華梵,皆大乘菩薩也。文王、老、孔,其言隱約,略見端緒,而不究盡,可以意得,不可質言。見章太炎《菿漢微言》,第37頁。此語與章首所引熊十力“以經義折衷佛學義理”的論點,可以參看。雖說,章太炎那里有“胸中樂境”與義理之學的脫節,在熊十力,有“量論”之難成,到了牟宗三,也有無奈的“良知坎陷”。學人的思想經驗,總是難以表達成讓他們自己滿意的“義理之學”,然自得之意,卻不少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