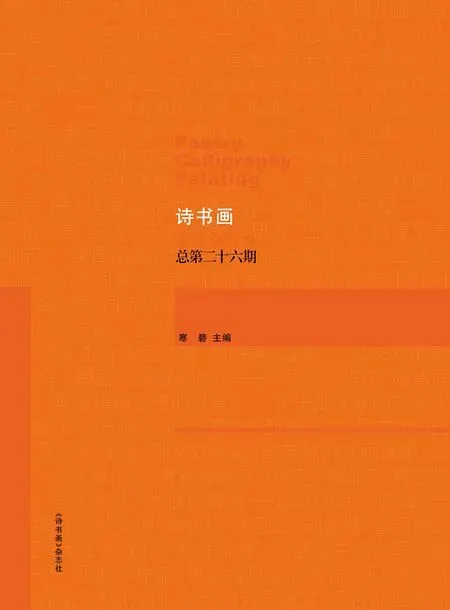紀念碑到文獻,蒙太奇到拼貼
——邵文歡的自我《界破》
姜 俊
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是一個重要的轉換,科學技術蓬勃發展,從而帶動了生產力的迅猛推進,自一八三七年達蓋爾(Louis Daguerre)發明攝影技術以來,圖像生產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同時也帶動了感知形式的更新。
技術復制(die techinische Reproduzierbarkeit)和感性形式變革的問題首先是由本雅明提出。惟妙惟肖的復制技術打開了藝術創作的新世界,直到今天還規定著我們的實踐。無論是機械復制還是今天的數碼復制,或者是基因復制都可以認為是對于既有圖形(像素、數列分布、DNA圖譜)的自由編輯、復制和傳播。它們被歸結到一個詞上—“collage”(拼貼)。
如果我們只是在中文“拼貼”的動詞下理解它,就顯得非常狹隘。除了拼和貼之外,collage的另一個意思是:多樣事物的任意結集(any collection of diverse things)。collage本質上可以被認為是從解構到重構的過程。在此,任意圖形都可以成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基礎模塊(module),然后便是進入“多元拼合、聚合或融合”之中,從聲音到圖像、從平面到空間,圖像的生成將因此進入無限加速之境。
在今天,這一邏輯幾乎出現于任何一門藝術的創作中。拼貼的運用代表了一種典型的當代性格,即自由、平等和高效。正是由于工業化復制的普及和成本的不斷壓縮,才使得拼貼能任意和加速運作,并從平面圖像擴展到空間造型之上。杜尚二十世紀初開創的“現成品”完全可以被理解為拼貼的一種空間形式。
在邵文歡的藝術作品中除了人們一直討論的跨媒介之外(攝影繪畫),還有一個維度并未被仔細審視—拼貼中的紀念碑性。在他的作品《跌水須彌之九十方》中,一方面我們不難看到北宋巨嶂山水的紀念碑式運用,另一方面同一座山水的不同時間、角度被并置和集結在一起,構成了一種文獻上的陳列。
十九世紀攝影自發明不久就被用于文獻記錄,無論是用于人物檔案,還是城市風貌采集、科學研究、案件記錄,它的確協助了福柯所謂的現代治理術的轉型—從前現代的紀念碑(monument)轉向現代治理的文獻化(document)、檔案化。
每一個人的生活都被歸入其中,在各種文件、檔案和證件中被自我標示,成為了活體管理的對象—生命政治。這也導致了感性層面和藝術創作方式的變革,同時代的印象派畫家莫奈反復地繪畫具有文獻意義的巴黎圣母院—呈現不同的時間和光線下的單一客體。我們必須知道,在攝影歸檔出現之前,這一創作舉動是不可被想象的。
在晚期傳統中國繪畫中,模塊化非常清晰的體現在《芥子園畫譜》中,這無疑和中國過于早熟的治理術也密切相關,在中國治史傳統中文獻化和檔案化由來已久。當文人畫成為了一種文人間高雅的交際手段后,迅速掌握一種有效的程式也成為了迫切的需求。
《芥子園畫譜》作為一種圖式辭典就應運而生。傳統山水畫中,既定圖像群的反復組合構成了山水藝術千變萬化的基礎。它們以一種有“過渡”和“渲染”的方式施行軟性的拼貼,從而達成有機的一體性,即我們今天所謂的蒙太奇手法(montage)。
如果說《跌水須彌之九十方》中的山水是攝影文獻式的、是拼貼的,那么《暮生園之八》就是典型的蒙太奇(montage)了。畫面的構圖讓人聯想到《游春圖》,蘇州環秀山莊的巨型假山體同樣也來自大量不同角度和時間拍攝的局部照片,在過渡和渲染下融為一體,構成了一種完整的統一體,有氣勢恢宏的紀念碑效果。紀念碑往往伴隨著一種浪漫主義情懷,如同德國浪漫主義作家諾瓦利斯所寫的:

邵文歡《暮生園之七》(攝影、明膠銀手工涂繪感光、丙烯繪畫)
“當我給卑賤物一種崇高的意義,給常物一副神秘的模樣,給已知物以未知的莊重,給有限物一種無限的表象,我就將它浪漫化了。”
如果拼貼是冰冷的現代理性,它有堅硬的分界線,就如同Becher夫婦著名的水塔系列攝影那樣,展現了一種文獻式的中立和客觀。那么相反,蒙太奇就是詩意的大敘述,并訴諸于情感維度,柔和的邊緣彌合了多個渺小視角的斷裂,它們共同組成的山水構成了某種崇高。
邵文歡的藝術創作回旋于文獻式的理性和紀念碑式的感性之間,在這兩極中存在著某種悖反和辯證。園林對于古典文人是一種桃花源式的逃逸,它補償著都市俗務的糾纏和面對生活瑣碎的茍且。儒家規制的房屋格局和道家園林的天馬行空構成了最為形象的空間對比,自然仿佛在微縮山水的象征中獲得了超越。在今天我們依然擁有著這一份懷舊,它以一種浪漫主義的形式構成了對于不堪的現代化生活之補償。如同福柯而言,現代社會是一種被監視和檔案化的監獄群島,那么我們同樣需要紀念碑,需要詩意,需要使得卑微之物被貿然幻化為崇高的升華。
而過度的浪漫主義卻終只是一種自慰,在邵文歡的作品中紀念碑似乎又物極必反的轉向了文獻,《暮生園之八》中央的深色長方形正打破了某種懷舊,使得紀念碑不再穩定,并擺向了在《跌水須彌之九十方》中對無數種觀看和時間的并置。它們層層疊疊,某些圖片不只是左右上下,甚至是前后疊加,山上的流水仿佛涓涓不息,讓人聯想到Eadweard Muybridge于一八八七年實施的攝影試驗—運動的過程。
一種北宋紀念碑式的巨嶂在導向對于自然崇高的贊美時就被打斷了,尖銳的拼貼代替了柔和的蒙太奇,反向訴說著機械式的觀看、多重感知下的時間。這是一重悖反,但隨即它又折向另一邊,瀑布在分裂的視角中輾轉匯集成為一個龐然大物,在支離破碎中又統一起來,重塑著流動的和時間差異的紀念碑。德勒茲在《什么是哲學?》中關于感性紀念碑說到:
“一個紀念碑無意于歡慶那些已經發生了的事件,而是把由這些的事件所形塑成的持續流傳的感性知覺托付給未來的耳朵。”
好的藝術回望著過去,過去在今天分解,卻在明天重塑。它構成了翻轉之翻轉的否定辯證,統一將永遠不會出現。我們可以把邵文歡的作品理解為一種反復的回旋運動—從紀念碑到文獻,從文獻到紀念碑,從蒙太奇到拼貼,從拼貼到蒙太奇。

邵文歡《夜空中星塵的光之一》(攝影、明膠銀手工涂繪感光、鋁金屬)

邵文歡《霉綠04》(亞麻布明膠銀手工涂繪感光、暗房沖洗、礦物色及丙烯繪畫)

邵文歡《暖冬》(攝影、負像繪畫、明膠銀乳劑涂繪感光、丙烯繪畫)

邵文歡《不明之一》(攝影、明膠銀手工涂繪感光)

邵文歡《浮玉No.01》(全數字虛擬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