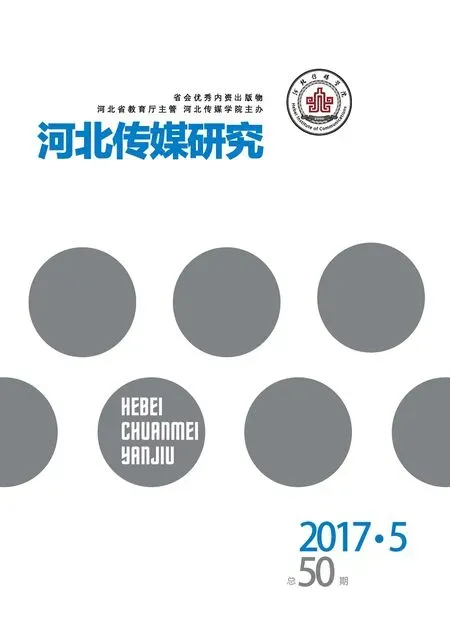《聊齋志異》中的諸神形象
岳文立
(河北傳媒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1430)
在遠古時期,我們的祖先生活于一個恐慌無所不在的社會里:那是一個食物極其短缺的時代,狩獵少、收成壞成為困擾人們的首要難題;那是一個疾病多發的時代,許多莫名的病癥折磨著先民們脆弱的身體和神經;那還是一個災難頻生的時代,洪水泛濫、久旱不雨等自然現象如一片揮之不去的陰影,時刻籠罩在先民們的心頭。對生存的渴望導致先民們開始求助于神明,試圖利用各種各樣的祈禱、獻祭來交通神明、打動神明,讓神明幫助自己減少恐慌、實現愿望。這樣一來,便興起了求神供神的風氣。這一風氣迅速席卷了華夏大地,并以其強勁的勢頭一直持續下來,歷經各個歷史時期,甚至直到現在的文明社會,依然是經久不衰。
我國民間所崇奉的神各種各樣,有雷公電母之類的天神、河伯土地之類的地神,也有閻王鬼判之類的鬼神、張飛關羽之類的人神,更有不計其數的動植物神。《說文解字》釋“神”字:“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1]8但是,這一概念顯然沒有涵蓋“神”的全部范圍。李劍國先生在《唐前志怪小說史》一書中這樣說道:“從廣義上說,一切天神地祇,世界的全部或某一部分的主宰者都是神。稟天地之氣而生者是神,人死之后亦可成為神,動植物也能成神。”[2]李先生的這種說法基本涵蓋了“神”的范圍,是一種比較準確的說法。
說起“神”這一概念,還有必要辨析一下和它相似的一個概念,那就是“仙”。雖然人們經常將“神仙”并稱,但實際上,“神”與“仙”并不相同。《說文解字》釋“仙”為:“仚(即“仙”——筆者注),人在山上貌,從人山。”[1]95顯然,這一解釋也未能概括“仙”的全部含義。
在談到神話與仙話的區別時,鄭土有先生這樣區分神和仙:
第一,神話中的神是萬物有靈、靈魂不滅觀念的產物,“而在神仙(按:即仙)身上體現的是靈魂肉體同時不死的觀念,肉體的意義得到了最充分的強調”。
第二,神之為神,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并非主觀所求,而神仙(按:即仙)由人升格,則要經過一番苦修苦煉。
第三,神格突出的是集體性,“他們的行為無不圍繞民眾的生存而展開”,“自我意識”在神的身上是不存在的。仙格“以自我為中心”。[3]
鄭先生的這一解釋對區分神與仙這兩個概念有很大的幫助。不過,在此基礎上,筆者還想補充一點,即神多受到人們的供奉和獻祭,而仙并不享受這些。因此,本文在談到“神”這一概念以及對《聊齋志異》中的神加以分類時,除了那些明確表明其神格的神以外,對那些身份比較模糊、似神又似仙的神仙,筆者就大致采用了鄭先生的解釋加以區分。
若對人們所奉之神加以分析,還應該從拜神運動的導火線——巫師的拜神活動開始論述。從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巫師實際上是多神論者,他們所崇拜的神并不局限于一種或一個,而是“雜取種種”為我所用。大體說來,巫師所崇拜的神可以分為五個類型:物神;人神;天神;地神;鬼神。那么,筆者就以這五種類型的神為基礎,分析《聊齋志異》①中所提及的神。
一、物神
所謂物神,包括動物神和植物神,其中又以動物神為主。古代巫師所供奉的動物神有狐、蛇、鼠、蟒、兔、刺猬、黃鼠狼等,如俞樾《右臺仙館筆記》卷十三中所說:“天津有所謂姑娘子者,女巫也。鄉間婦女有病,輒使治之。巫至,炷香于爐,口啯啯不知何語,遂稱神降其身,是謂頂神。所頂之神,有曰‘白老太太’者,猬也;有曰‘黃少奶奶’者,鼠狼也;有曰‘姑娘’者,狐也。又有蛇、鼠二物,津人合而稱之為‘五家之神’。”[4]除了這些動物神以外,其他一些動物或因生性兇猛、令人見而畏之(如鷹、虎等),或因人們時常所見、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如青蛙、蝗蟲等),或因其往往預示一些不好的事情而引起人們對其又敬又畏的情感(如烏鴉),這些動物也幸運地被人們選中,進入神的隊伍而享受人們的供奉尊敬和美食獻祭。
除了這些數目眾多的動物神外,還有一些植物神也進入了人們的崇拜領域,如《金枝》一書中就講到許多民族中都奉行的樹神崇拜、谷神崇拜等。在我國,后稷棄便是五谷之神,在“民以食為天”的社會中,他的職責至關重要,故世世代代享受著人們的供奉。
《聊齋志異》涉及植物神的篇目不多,只有《柳秀才》《絳妃》二文。《柳秀才》中談到柳神為救百姓而告知蝗蟲將興之事,并授人以避免之法,結果卻“引蝗上身”,柳葉都盡;《絳妃》中的絳妃乃是花神,為保護花兒生命而請聊齋主人撰寫檄文,以求合家平安。《聊齋志異》中涉及動物神的有7篇,分別是《鷹虎神》(鷹虎神)、《柳秀才》(蝗神)、《牛癀》(六畜瘟神)、《青蛙神》(蛙神)、《又》(蛙神)、《三仙》(蟹、蛇、蝦蟆神)、《竹青》(本為烏鴉,后成為漢江神女)等。這些神不僅具有非凡的本領(如《又》中的青蛙神借巫之口向人們討要修建關圣祠之資、《竹青》中之竹青使用法術從和氏處帶回兒子漢產等),而且還維護著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如《鷹虎神》中的神懲處偷兒、《柳秀才》中的柳神保護莊稼等)。除此以外,這些動物神還具有一些人的品格。它們或愛好風雅、以文會友(如《三仙》中的三仙),或與人相愛、真情流露(如《竹青》中的竹青、《青蛙神》中的十娘)。它們的愛情亦伴有喜怒哀樂,與人無二。這些形象亦神亦人,讓人們在崇敬它們的同時,又更多地了解它們類人的一面,從而拉近了它們與人之間的距離。
二、人神
所謂人神,多指那些生前為人們做出了貢獻、謀取了福利,因而死后被人們供為神的人。這樣,他們在接受人們供奉崇拜的同時,能繼續為廣大黎民百姓做出更多的貢獻。早期巫師所崇拜的人神多是那些被神化了的歷史人物,如神農、女媧、大禹、刑天等這些大巫兼大神之類的人物。后來,巫師又把另一些有杰出貢獻的歷史人物也納入了神的行列,如孔子、關羽、張飛等。再后來,一些生前地位低下、并經歷過許多磨難的人死后也能成為神,如著名的紫姑神。相傳紫姑為人側室,因被大婦所妒,于正月十五日氣憤致死(或說是被大婦殺死于廁間),死后成神。由于這些神都是從“人”升華為神,因此,他們很能理解民生疾苦,故靈驗頗多。《聊齋志異》中有不少篇章講到了人神的故事,見表1。
細細分析這些篇目,發現人們在崇拜這些人神的時候,其實也完成了人對自身的神化。正如黃倫生先生所說的那樣:“它使巫術行為的施行者保持這樣的信念:人與神有共同的屬性,故而不但能在此基礎上接受、探尋到神靈發出的種種信息,并且能夠以自身的努力來改變神靈的意圖和力量。”[5]正是由于人與神能夠溝通,神才能產生諸多靈驗,幫助人們解決種種難題,如《湯公》中的孔圣為湯公指點求生之路,《大男》中的關帝使大男迅速長大等。之所以有如許多的人神出現,是源于人對自身的神化,因為人相信自己與神有共同的屬性,這就為人成長為神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使人升華為神成為可能。如《李伯言》中的李伯言、《閻羅》中的李中之,都是既為人又為神的角色。另有《金姑夫》一篇也是如此。金生得近梅姑神,與梅姑神相戀,說明金生自身具有神性,這才使他依靠裙帶關系晉升為神。

表1 《聊齋志異》中涉及人神的篇目
三、天神
筆者以為,天神的出現應源于先民們對大自然中諸多變化的不理解:天空為什么會刮風下雨?太陽為什么要東升西落?月亮為什么有陰晴圓缺?流星為什么會一閃即逝?這些問題困擾著人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巫術之萬物有靈思想為人們打開了一扇思索的大門。走進這扇大門,人們恍然大悟,把這一切變化都歸結為天神的支配,于是,對天神的崇拜就此開始。后來,隨著階級社會的出現,人們自然而然地又按人間社會標準對天神進行排序,在人們的安排下,這些天神各有尊卑,專司其職,秩序井然地為他們的創造者——廣大百姓提供各項服務。先民對天神的崇拜非常虔誠,這也反映在了《聊齋志異》中,書中涉及各種各樣的天神,見表2。
天神不僅法力高強,而且有些還奉行巫術,如《湯公》中的菩薩折柳為骨、撮土為肉,顯然使用了模仿巫術。這說明,巫師在創造這些神的同時,往往以自己作為參考標準。這樣,在鼓吹這些神的同時,也變相地為巫師本身做了宣傳。另外,這些神雖然是天神,也主持一些諸如打雷降雹之類的日常工作,但他們更多的是作為人們的守護神出現的。他們為神正直、伸張正義,為生活在黑暗現實中的人們帶來一絲光明。如《菱角》中的菩薩,在戰亂紛爭、人民流離失所時,努力保全胡大成一家,使其夫妻聚首、母子團圓。《席方平》中,席方平在陰間經歷種種磨難仍不能為父伸冤,可謂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正是二郎神幫其除去惡鬼、昭雪冤屈。可以說,文中的地府正是陽世生活的再現。在這個弱肉強食、黑白不分的社會中,人們根本找不到出路。席方平是幸運的,得遇二郎神而一訴沉冤。可是,世間更有千千萬萬個“席方平”存在,他們是否也能得到二郎神的眷顧呢?因此,人們拜神供神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表2 《聊齋志異》中涉及天神的篇目
四、地神
在先民的意識中,地的重要性并不亞于天。它是人們賴以生存的資本,衣食住行等各種活動都離不開它。但是,它在給予人們生命的同時,又以各種災難考驗著人們,如洪水泛濫、糧食歉收等。因此,人們在對大地感恩的同時,又對其產生敬畏之感,并在萬物有靈的巫術觀念指導下,進一步將其神化,認為土地上的一切事物,如山川河澤、平原曠野、都城郡縣等各個地方,都由專司其職的地神掌管,他們就像人世間的官府一樣,統治著自己的轄區,造福(也可能是為害)著轄區內的居民。這些居民不僅包括眾多普通百姓,還包括轄區內的一切花鳥魚蟲、靈石草木。在《聊齋志異》中,就寫到了不少這樣的地神,其中不僅有山神水神這樣的專職地神,而且還有土地神城隍神這樣的轄區地神,涉及篇目如下:
山神:《山神》
水神:《汾洲狐》(河神)、《鄱陽神》《水莽草》
土地神:《王六郎》《土地夫人》《韓方》
城隍神:《考城隍》《李司鑑》《皂隸》《席方平》《王大》《老龍舡戶》《劉全》
在這些篇目中,大多數神是本來就存在的,并沒有提及其產生過程,如《山神》《鄱陽神》等,但也有一些神則是經過了某種考驗或事件而被選中,如《考城隍》中的宋公,就是在病中得以參加考試,最終因為文品出眾而當選。另如《王六郎》一文,王六郎本為溺鬼,出于惻隱之心,將本該溺死以代自己的母子救活,自己卻因此無法投生;正是這次善舉使其當選為鄔鎮土地,加入了神的隊伍。作者通過這些例子來表達老百姓對神的要求,但這不也反映了百姓對管理自己的父母官提出的要求嗎?也許正是現實社會中像這樣文品出眾、心地善良的官吏太少了,人們才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想象的世界中,在虛幻中滿足自己對理想官吏的構想。但是,即便是神,有的也沾染上了人世間許多官吏的惡習。如《席方平》中的城隍神,收受賄賂,顛倒黑白,昏官的嘴臉盡顯無遺,真可謂:世間本無凈土在,勸君莫再苦追尋。
五、鬼神
所謂鬼神,指人們在想象的地府中設置的神明。對鬼神的崇拜源于古人靈魂不滅的信仰,即人死以后肉體歸土而靈魂猶生,因此人之死亡并非真正的湮滅,而是生命形態的一種轉化形式。在佛教傳入之前,諸多游魂只是以一種散漫的狀態存在于各種文獻中,且多以祟人面目出現,于是便有了巫師驅鬼除祟的職責。佛教傳入以后,為人們帶來了地獄、輪回等新鮮觀念,于是,人們在遭受陽世政府統治的同時,又用豐富的想象力為自己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地府統治機構來收容管理這些游魂。這一機構的首腦是閻王,世人的生死大權盡歸其一人掌握,所以世間便有“閻王要他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的說法。另外,閻王還對人們生前的是非功過進行徹底清算,然后根據清算結果決定此人來世的命運。可以說,人們的前生、今世和來世,盡在閻王帶領的那一群地府神明的掌握之中。因此,對于閻王等地府神明,人們自然是又敬又畏,由此便產生了對鬼神的崇拜。但幽冥阻隔交流不便,于是人們便仰望巫師這種專門人才來傳達來自地府的各種指示,故“走無常”“視鬼神”又成為巫師不可推卸的責任。
綜觀整部 《聊齋志異》,涉及鬼神的篇目有18篇,其中有閻王、判官、鬼王、東靈使者、冥中使者等各種神明,分別為:
閻王:《考城隍》《三生》《某公》《閻王》《厙將軍》《考弊司》《劉姓》《閻羅宴》《席方平》《汪可受》《王十》《元少先生》《小謝》
判官:《陸判》《小謝》(西廊黑判)
鬼王:《席方平》
東靈使者:《酒狂》
冥中使者:《僧術》
在這些篇目中,作者用真實的筆法向讀者展示了一個陌生而又熟悉的地下生活環境。陌生,是因為這里充滿了想象中的場景,如油鍋沸鼎、鋸解人身、賞罰功過、投胎轉世等種種冥間活動;熟悉,則因為這其實也是陽世生活的再現。在這個統治機構中,閻王作為最高統治者,多是正義和公平的化身,代表著人們對陽世最高統治者的美好愿望 (《席方平》一篇除外),如《考城隍》中的閻王賞識文采,《元少先生》中的閻王重視教育,《考弊司》中的閻王剛正不阿,《王十》中的閻王賞罰分明。但閻王手下的各路官員卻呈現出另一種狀態,如《考弊司》中的鬼王貪暴不仁,文人無錢行賄竟強割髀肉;《僧術》中的冥中使者也以收受賄賂的方法來買賣陽世功名;《小謝》中的西廊黑判則強搶秋容,逼其為妾。這些鬼官的所作所為正和陽世如出一轍。這些描繪反映了所謂官吏在人們心目中的真實面貌。
注釋:
①本文以196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 《聊齋志異》為研究底本。
[1]許慎.說文解字[M].段玉裁,注.上海:中華書局,1963.
[2]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11.
[3]鄭土有.中國神話仙話化的演變軌跡[J].民間文學論壇,1992(1):27-37.
[4]俞樾.右臺仙館筆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
[5]黃倫生.東方天國的神秘之門——中國巫術文化探秘[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