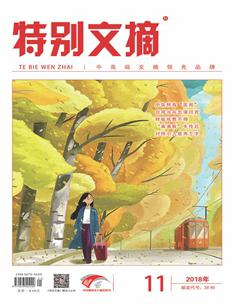香港有許多“社會主義”
錢鋼
香港多山,中文大學熊景明老師,邀好友去爬山。走到半路,熊老師摔傷了。正焦急萬分,山下上來一對年輕男女。那位女士趕緊上前,用襯衣做了個替代的繃帶。這時我們知道,她是一位護士。更巧的,男士竟然是警察!年輕警察于是請求派員上山。大約過去半個小時,聽見人聲。有7個消防隊員,從彎道那邊走出來。看見傷員,立刻檢查傷勢,動作十分嫻熟。我了解到,他們屬于附近鄉鎮的消防局。這個星期天,他們像往常一樣,在例行值班,嚴陣以待。一輛白色的小型救護車已在山腳等候。在把熊老師送去醫院前,是例行的填表、詢問、筆錄,程式刻板,卻瞬間完成。那瞬間,我吃驚地發現,旁邊還有兩輛紅色大消防車,車上另有8名全副武裝的消防員——一共有15個人來救我們熊老師!
香港政府的救險體系,包括飛行服務大隊、消防部隊和“民安隊”。遇到爬山人士報警求救,前兩者負責處置“有性命危險的情況”,后者處置“無性命危險的情況”。我猜想,那天我們在山上的緊張慌亂情形,令報警的男士提高了反應等級。通常情況下,上來的可能是“民安隊”。有時僅僅因為爬山者體力不支,接獲報警后他們也會派人趕到,陪同你安全下山。
剛來時,朋友說“香港有許多社會主義”,我大惑不解。后來有了日漸增多的近距觀察,明白那是指公共服務。今天香港的700多萬人口中,有近半數,或租住政府提供的“公屋”,或購買了政府為“居者有其屋”而提供的普通家庭“負擔得起”的“居屋”。公營醫院收費低廉,我的一位女同事生孩子,所花費用,總共是港幣四百多元。“公帑”——即政府財政支出,隨處可見。
香港的公共服務體系和社會福利政策(即“善治”)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基本定型。街市大樓里,必設公共體育中心;有供放學后的孩子來做作業的“修習室”;必有一個公共圖書館。香港所有的公共圖書館組成一個網絡,你在西環的街市借了書,可以在長洲島上的街市歸還。街市的正式名字是市政大廈,但不是衙門,是政府為市民提供服務的場所。
剛到香港時,我還親眼看見過一次區議會選舉。香港有18個區,沒有區級政府,區議會權力有限。更多的是一個表達民生需求的渠道。我饒有興致地徘徊街頭,看到那些區議員候選人(有的人非常非常年輕!)手持“咪”(即麥克風),一遍遍地詳細解釋如果他當選將有何作為。例如,游說交通管理部門將某路巴士延伸到某處;阻止開發商拆除某老人活動場所;保護某處的某一株古樹……在我住處附近的西環觀龍小區,選情激烈,一男一女兩位候選人難分高下。最后時刻,雙方都宣布“告急”,派出助選員到各幢公寓“洗樓”(挨家挨戶拉票)。結果,男候選人以微乎其微的劣勢失利。
當“民意”變得如此鮮活觸手可及,來自市民的壓力如此現實不可輕慢的時候,一位當選者,能不好好經營嗎?
(摘自《財經》 圖/子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