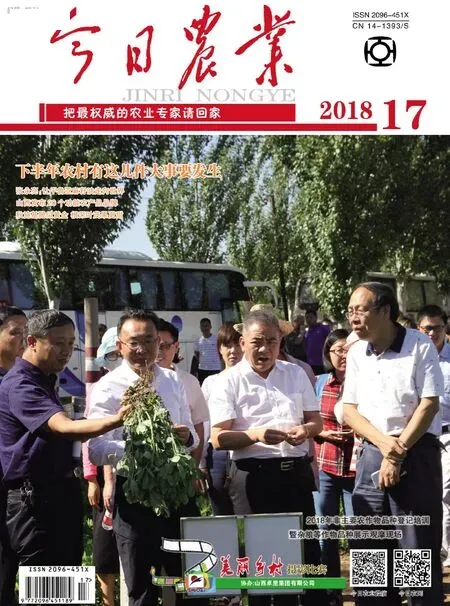一管就僵,一放就亂?
“管”也不是,“放”也不是
農村蓋個房,需要17個部門審批;村民蓋個章,要跑鄉里好幾次;環保督查要求清零禽類養殖場,到頭來變成了建設 “無雞村”“無雞鎮”……一些農村干部感到工作氛圍過緊、變僵,紛紛呼吁為基層“松綁”。
另一方面,在上級部門對村級管理較為松散的地區,村干部胡作非為的亂局,基層發生的微腐敗案件,大部分也與上級部門監管失職有關。
鄉村治理該“管”還是“放”?專家表示,破題的關鍵在于以村級組織為中心管放結合,提升村級治理能力,謀求組織振興。
“到了鄉鎮政府不知該上哪個辦公室,不知該找哪個人。”有群眾反映,一些村莊離鄉鎮政府較遠,為蓋一個村章,要往返幾十公里。有時遇上鄉鎮管公章的人員不在辦公室,還要多跑幾次。
除了“村章鄉管”“村財鄉管”等“強代管”,上級的其他種種“強管理”都讓村干部和村民無所適從。西北地區某村的村民吐槽:“本來是不讓搞禽類養殖場,但上級政府抓得緊,一只雞都不讓養,現在我們村都聽不到雞叫聲。”
同時,上面對村里的一些制度規定讓村民很無奈。有網友表示,一事一議制度,百姓很想執行,但流程很煩瑣:“這材料那材料,一個小工程都要設計、招投標、做決算,費用基本都花在前期和后期上,村集體根本負擔不起。”“路該修的沒修,公廁該建的沒建……一事一議基本成了口號。”
一管就僵的問題,能否靠放權迎刃而解呢?一些地方的村民告訴半月談記者,由于缺乏對村級垃圾處理的管理辦法和細則,村里的垃圾往往是河邊撂、路邊扔、坡上堆,然后等著一場大雨過后,河水上漲,把垃圾沖走。
對此,當地村干部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鎮上不牽頭,不考核,沒有充足資金支持,我們村集體經濟又很薄弱,只能對這種亂倒垃圾的現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鄉村自治,卡在哪兒?
半月談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一些基層干部認為,上級部門管束過多,容易給大家干事創業的積極性“潑冷水”,造成“一管就僵”。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對村級組織應當加強管理,建章立制,“放”則不利于村級組織有序運行。
長期從事三農研究的全國人大代表謝德體認為,村級出現“一管就僵,一放就亂”的不正常現象,根本在于我國鄉村自治能力仍然匱乏,具體體現在簡單粗暴的管理思維上。謝德體說,加強監管原本是為了讓村級組織運行更加規范,放權“松綁”的出發點則是給農村增加更多活力,但實際操作中,工作做得不實,造成效果有限,老百姓的獲得感缺失。
一些村干部反映,基層工作的“泛行政化”傾向對村里自治力提升有很大影響。大量工作在基層落實,各種事務、考核讓他們疲于應付,工作趨于簡單粗暴。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村干部對于如何提升鄉村自治能力存在本領恐慌。一名任職已有10年的村支書坦言,許多村干部還沒有完全跟上新時代的節奏,導致村務治理能力明顯滯后,一定程度上存在對上級部門的過度依賴。
組織振興關鍵靠做強支部
當前我國村級治理水平與實現鄉村振興的目標仍不相適應,亟待進一步提升。
專家表示,現在村民委員會決策有“四議兩公開一監督”,程序比較健全,鄉鎮政府應該進一步加強監督和規范引導,做大做強村級組織提升自治能力和民主程度,而不是把公章、村財政等作為農村治理的“牛鼻子”。
謝德體認為,實現鄉村振興、提升村級治理能力首先要靠組織振興作保障,只有村黨支部領導班子的能力強了,提升村級治理水平才不是一句空話。謝德體建議加大引入本土人才的力度,創造機會讓更多能人擁有施展抱負的空間。
提升鄉村自治力,還需要建立容錯糾錯機制,給真正能干事、愿干事的干部營造更加寬松的工作環境。黨的十九大代表、重慶市開州區長沙鎮齊圣村黨委書記熊尚兵說:“現在有些干部上級給項目也不敢接,怕做錯事受處分。我們倡導擔當精神,不能讓真正愿意干事的好干部蒙冤受屈。”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專家建議,村民自治要有法律法規、村規民約等規章制度作保障,在村級組織去“行政化”方面發力,讓基層自治組織回歸群眾性和自治性。
(據半月談網 作者:周聞韜 李浩)
模式一:政經分離
【專家推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
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后,需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運行,只有跟鄉村自治組織分開,集體經濟才能得到更充分發展;與此相對應,基層自治組織只有將經濟職能剝離以后,才能更專業化、精細化,給村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廣東佛山南海區、浙江溫州等地的政經分離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基層治理實踐。通過經濟組織與自治組織分離,兩者分別履行各自的職能,理順了組織之間的職責關系。這種模式對于發達地區破解外來新增人口帶來的基本公共服務與經濟收益分配的矛盾,也是一種有益的探索。
模式二:監委會
【專家推介】山東大學教授王忠武
支委會統領、村代會定事、村委會辦事、監委會監事,山東濟南市章丘區“四會管村”做到了領導權、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四權”的合理分配和有效結合,實現了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四民主”的責任落實和有機統一。
目前,全國許多村莊都建立了村務監督組織,浙江、山東、安徽、福建、河南、四川、寧夏等省份還下發了專門規范性文件。村務監督委員會這一村級民主自治新模式有效破解了村務監督難和制度落實難兩大難題,從制度層面構建責權明晰、分權制衡的鄉村現代治理機制,讓群眾明白,還干部清白。
模式三:議事會
【專家推介】成都市委黨校教授劉益飛
作為統籌城鄉發展的 “樣板”城市,成都市成立村民議事會探索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充分調動了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積極性和主動性。撬動群眾參與治理的熱情,普通黨員帶頭尤為重要。未來,議事會應“盤活”基層黨建資源。
順應鄉村之變創新鄉村治理
從房舍田園到農作方式,從“面子”到“里子”,中國鄉村正在發生歷史性的嬗變。只是不同的人有不一樣的感知罷了。城里人看鄉村,那是寄托鄉愁的地方,是周末假日采摘休閑的去處,是吸一口好空氣、吃一頓土菜美味的后花園;站在農民自身角度看鄉村,這些年鄉村的基礎條件大變樣了,但鄉村的人氣沒落了,有的農村人帶著集體成員股份權和財產性收益進城了,有的辦起了家庭農場,有的如候鳥般在城鄉之間輾轉。
鄉村嬗變的主要特質表現為農業生產從傳統向現代轉型,農村社會從封閉向開放轉變,城鄉關系從割裂向融合轉化。每年有1000萬農村人口脫貧,有超過1000萬農村居民市民化,2017年返鄉下鄉創業創新人員達到740萬人;過去主要是農村向城市流動,現在呈現出雙向流動的局面;鄉村價值得到進一步釋放,農村生態觀光、休閑旅游、健康養生和電子商務等,催生出大量的新產業新業態;東部一些村莊越長越大,如同一座小城市(譬如江蘇華西村、浙江花園村等);而在中西部,一些傳統村落正在消亡,有的則處于產業“空心化”、農戶“空巢化”、人口“老齡化”的狀態。
“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變革中的中國鄉村,無疑對鄉村治理提出了新課題。如何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把握鄉村發展機遇,激發鄉村發展活力,促進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需要我們因時而變、因勢而變,順應歷史發展方向,遵循鄉村自身演進規律,健全和完善鄉村治理體系。
鄉村之變呼喚治理理念之變。“治大國如烹小鮮”,這是老子所倡導的治國理念。對一個具體地域而言,如何實現良治一般可分為自治與他治兩種方式,就方法而言,有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等。傳統中國社會中的鄉村,正如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所描述的,充滿了自治色彩,傳統鄉村的封閉性、地緣性與自給性決定了皇權向鄉村滲透的有限性,這為鄉村自治的發展和壯大提供了基礎,陳忠實筆下的白嘉軒、鹿子霖對白鹿原的治理對此作了生動的闡釋。近現代以來,隨著國家政治結構的劇烈變遷,國家權力不斷滲透到農村基層,外在力量的治理改變了原有的鄉村秩序,直到20世紀80年代,村民自治得以推行。當前,在鄉村治理理念上,我們有必要來一次重新認知,就是要由“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與民共建共治共享”轉變。這就要求我們堅持農民治理主體地位,重新審視政府與鄉村社會的關系,革除基層政府管得多又管不好的積弊,規范鄉鎮對村民自治的指導和監督,鄉鎮政府的指導和監督行為應當依法進行,不得將指導與被指導關系異化為領導與被領導關系;“村里事,大家辦”,開展形式多樣的群眾協商,促進群眾在鄉村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適應城鄉人口雙向流動趨勢,不斷完善民主議事制度,探索戶籍村民和非戶籍常住村民共同參與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徑,以村務公開和民主理財為重點,切實保障農民群眾的決策權、參與權、知情權與監督權。
鄉村之變催生治理體系創新。當前,我國鄉村治理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既有諸多有利條件,也面臨著不少急需破解的難題,如何實現農村基層在經濟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會治理、生態文明治理上五位一體協同推進,必須以黨的十九大提出的“三治”結合為引領,著力構建以黨的基層組織為核心,以村民自治組織為載體、以法治為保障、以德治為基礎的鄉村治理體系,確保農村社會安定有序,農業發展欣欣向榮。要堅持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激發內生動力,提升鄉村自我管理、服務和監督水平,把鄉村自治和“能人治村”有效地結合起來,讓鄉賢在參與村民事務決策、解決農村矛盾糾紛中發揮更多的作用,發揮好村規民約在鄉村治理中的積極作用;要以法治為保障,加快涉農立法速度,加快完善鄉村法律服務體系,加大普法力度,推動基層干部群眾形成信法、學法、用法的思想自覺,推進平安鄉鎮、平安村莊建設,開展突出治安問題專項整治,加強農村司法所、法律服務所、人民調解組織建設,推進法律援助進村、法律顧問進村;要以德治為支撐,大力推進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文明風尚,培育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力提倡推廣移風易俗,褒揚善行義舉、貶斥失德失范,營造風清氣正的淳樸鄉風。
鄉村之變要求堅持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核心地位不動搖。鄉村自治并不是自由散漫、任意而為,越是自治,越要強化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最根本的保證。要打造千千萬萬個堅強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培養千千萬萬名優秀的農村基層黨組織書記,把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為貫穿鄉村善治道路的一條紅線;要根據黨員從業結構的變化和黨員流動頻繁的特點,探索“村企聯建”“合村共建”“支部+協會”“產業黨支部”等黨建模式,確保基層組織覆蓋到農村各類經濟和社會組織;要針對農村黨員教育存在制度不嚴、方式陳舊、內容單一等問題,建立農村黨員遠程教育網絡終端,切實提高農村黨員干部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堅持問題導向,扎實推進抓黨建促鄉村振興,加強村級換屆選舉監督,依法打擊“村霸”及宗族惡勢力,專項治理農村“小官大貪”和脫貧攻堅中出現的“微腐敗”,把鄉村治理和服務群眾有機結合起來,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