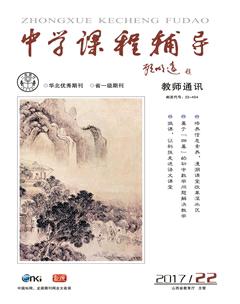語文課,怎能一笑而過?
姚雪飛
【內容摘要】在課堂中,如何體現學生的主體地位是課堂教學策略需要重點研究的環節之一,在這環節中,教師需要融入自己的智慧與藝術,讓學生的不僅在學習中收獲知識與智慧,更收獲幸福與成長。而教師的科學教學策略則是智慧與幸福的保障。
【關鍵詞】語文主體幸福成長
最近,筆者聽了某位教師執教李森祥的《臺階》一課。教者將本課的重點定為“通過文中的細節描寫讀懂父親這一人物形象”。關于這篇小說,由于它主題的多元性,為教師和學生提供了個性化解讀的廣闊空間,但不管是剖析農民謙卑心理的,還是反思落后的地方文化中的人生悲途的,或是感悟要擺脫貧困發展生產力的,小說的悲情色彩卻是濃郁的。可是課堂上我卻聽到了不和諧的笑聲,它不由得引起了我對本課教學的深刻思考。
教學過程中,教師組織學生品讀文中“放喜慶鞭炮”這一細節,目的是引導學生讀出文字背后隱含的人物的性格。學生讀完后,教師模仿父親的動作,在講臺前走了一個來回,教師的動作引起了學生的一片哄笑聲。笑過之后,當老師問及學生能否讀出文字背后隱含的東西時,大部分同學茫然不知,只是覺得父親動作可笑,隨后老師告之,這里可以讀出父親的謙卑。
本堂課教師的表演,目的是引導學生讀懂父親。但事實是他的表演非但沒有幫助學生透徹理解文中人物的性格,反而破壞了整堂課的情感基調。
曾聽一位同行講起某教師執教《背影》一課,該教師在引導學生品讀文中對父親外貌和動作描寫時,讓學生戴上禮帽,穿上長袍,模仿父親穿鐵道爬月臺的動作。學生異樣的穿著打扮和滑稽的動作引起了哄堂大笑,教師可能意識到學生的表演背離了文章的感情基調,就親自穿衣戴帽表演,結果招來學生更大的笑聲。
《臺階》和《背影》這兩篇表現父親的文章,字里行間都流露著淡淡的哀傷。而這兩位老師采用的方法與其說是表演,不如說是搞笑,課堂上的表演嚴重沖淡了作者深沉的悲傷情感。試想:學生在前仰后合的大笑聲中,哪里還能體會到作者悲情之所在,更不用說去讀懂人物了?
浙江特級教師虞大明對語文課的表演曾有過精辟的論述:表演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表演要引導學生關注文本;在表演中落實重點詞句的理解和感悟;在表演中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在表演中落實朗讀訓練。但是實際情況是,我們很多語文課上的表演與文本是割裂的,這樣的表演不僅不能幫助學生深入地理解文本,有時拙劣的表演會適得其反。語文老師,如果你不能很好地駕馭這種手段,那就請慎用。語文課,更不能一笑而過。
那么,就《臺階》這篇文章,教者應該如何引導學生通過有效的文本解讀,從而真正讀懂父親,理解小說的主旨呢?
葉圣陶先生曾說:“文字是一道橋梁。這邊的橋堍站著讀者,那邊的橋堍站著作者。通過了這一道橋梁,讀者才會和作者會面。不但會面,并且了解作者的心情,和作者的心情相契合。”解讀文本的過程,就是讀者通過文本與作者展開對話的過程。因此教師理應指導學生通過誦讀、品味去感知、理解、評價、創獲文本。
比如要想通過品讀“放喜慶鞭炮”這一細節讀懂父親,教者可以引導學生通過文中“無奈,他的背是駝慣了的,胸無法挺得高。”這句話的品讀來體會。引導學生理解這里所說父親的背是駝慣了的,很顯然不是身體上的駝背。因為既然是駝慣了,絕不是一天兩天,而是很長的一段時間。通過閱讀文本,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發現,年輕時的父親絕不是一個駝背,他能將每塊約三百來斤的石板從山上背下來,而且一下子背了三趟,還沒覺得花了太大的力氣。即便是臺階建成后的父親,還能“挑了-擔水回來,噔噔噔,很輕松地跨上了三級臺階。”由此可見,這里的“駝慣了,胸無法挺得高”表現的是父親的地位,關于父親的地位前文也有交代:“父親老實厚道低眉順眼累了一輩子,沒人說過他有地位,父親也從沒覺得自己有地位。”正是長期的缺少地位,父親才希望通過建高臺階獲得別人對他或者對他這個家庭的尊重。但也正是因為長期地位低下,當新屋建成后,沒有習慣于別人尊重眼神的父親,即使在“他仿佛覺得許多人在望他”的處境之下,也會手足無措,明明是該高興,卻露出了尷尬的笑。新臺階建成后,坐在九級臺階上的父親渾身不自在,一級一級往下挪,這些細節描寫無不顯示著一位謙卑的農民特有的心理。他并沒有因為臺階高了,那種謙卑的心理就消失了。高高的臺階與伴他一生的謙卑心理文化之間的溝壑更加深了。辛苦勞碌了一輩子的父親何曾想到,他所追求的不過是形式上的提高地位而已,就象閏土的香爐和燭臺無法祈來幸福安定的生活一樣,父親的九級臺階又怎能真正筑起父親受尊重的地位呢?小說就是通過這樣一個帶著悲情色彩的故事來讓讀者反思中國農民的生活。
在學習一些具有悲情色彩的文章時,課堂上有時會出現一些不和諧的笑聲,老師們往往會抱怨學生感情淡薄,情感沙漠化,卻很少從自身的角度來考慮。為什么自己的引導未能讓學生入情入境而適得其反呢?作為語文老師,如何通過文本將“橋堍”這頭的學生引導到“橋堍”那頭的作者情思中去。我想,應該是我們致力探討的方向。
(作者單位:江蘇省如東縣岔河中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