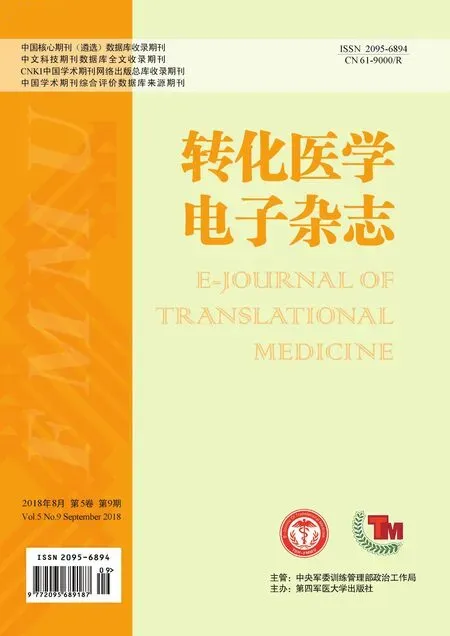胃癌靶向治療機制及中西醫藥物治療情況的研究進展
楊巧紅,張新江,杜 清,李琳琳,藍華全,呂依揚,黃舒蕾,印明柱,魏小勇
(1廣州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2廣州中醫藥大學第四臨床醫學院,廣東 深圳518001;3青海民族大學藥學院,青海西寧810007;4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腫瘤科,河南鄭州450052;5中南大學湘雅醫院腫瘤科,湖南長沙410000)
0 引言
胃癌是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在我國,男性胃癌患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女性胃癌患者的死亡率僅次于肺癌,而女性胃癌的發病率位于乳腺癌和肺癌之后,位居第三[1],每年約有70萬人死于該疾病。傳統治療方法包括外科手術治療、化學治療、放射治療、免疫療法、中醫中藥治療等。隨著精準醫學時代的到來,胃癌的靶向治療機制已被逐漸闡明,各種靶向治療藥物在臨床上取得了較好的療效[2]。靶向治療是以腫瘤細胞中的致癌基因和分子為靶點,選擇相應的靶向藥物阻斷與腫瘤發生發育密切相關的細胞信號轉導通路,從而對腫瘤細胞的增殖、生長、侵襲及轉移產生抑制作用,從而導致腫瘤細胞的死亡。由于靶向治療具有特異性強和副作用小等優勢,目前已成為胃癌精準治療研究的重點[3]。過去幾十年,隨著腫瘤生物學的快速發展以及腫瘤分子標志物的不斷涌現,使眾多靶向治療藥物應運而生[2],分類歸納目前胃癌靶向治療主要的11類靶點,詳細概述每種靶點的用藥情況和作用機制,在中藥治療胃癌方面的機制及作用靶點方面也體現出了巨大可喜的優勢。綜述胃癌靶向治療藥物的研究歷史及進展,為進一步完善和研發新的高效低毒靶向治療藥物提供思路。
1 胃癌靶向治療之西藥作用靶點及機制研究
目前胃癌的靶向治療根據不同的靶點可分為以下11類:抗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1(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1,EGFR1)、抗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2(anti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抗哺乳動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抗重組人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受體(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FGFR2)、抗肝細胞生長因子受體(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receptor, HGFR/c?MET)、抗程序性死亡配體?1(programmed death1 ligand, PD?L1)、抗細胞毒T 淋巴細胞相關抗原 4(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4, CTLA?4)、抗兩面神激酶(janus kinase 2,JAK2)、抗聚腺苷酸二磷酸核糖轉移酶?1[poly(ADP?ribose)polymerase?1,PARP?1]、抗 Claudin 18.2(CLDN18.2),分別論述其作用機制。
1.1 抗EGFR1靶點EGFR1是HER家族的成員之一。HER/ErbB家族屬于I型受體酪氨酸激酶,包含 4 個成員:HER?1、HER?2、HER?3 和 HER?4。 其中HER?1又稱為 EGFR1,主要參與腫瘤細胞的增殖、侵襲、血管生成、轉移等基因的調控。靶向EGFR的治療策略有兩種,均可通過阻斷EGFR酪氨酸激酶活化及下游的細胞內信號轉導,一種是用于胞外配體結合區的單克隆抗體藥物,如西妥昔單抗等,另一種是胞內酪氨酸激酶抑制劑型的藥物,吉非替尼等[2]。
1.1.1 西妥昔單抗(Cetuximab) 西妥昔單抗是EGFR1的人鼠嵌合IgG單克隆抗體。2013年一項EXPANDⅢ期臨床研究[4]顯示,在卡培他濱和順鉑化療的基礎上加用西妥昔單抗,并未能顯著增加晚期胃腺癌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西妥昔單抗應用于胃癌治療研究值得進一步探索。另一項報道[5]表明,西妥昔單抗在部分KRAS基因未突變的胃癌患者中有效,表明其他分子變異體可能參與西妥昔單抗抵抗。EGFR下游效應物如BRAF和PIK3CA的突變表現出對西妥昔單抗治療的抗性[5]。核因子受體活化因子RANK和其配體RANKL在某些胃癌患者中高表達,RANK與EGFR的表達呈正相關,在體外研究中,RANKL誘導EGFR的活化和EGFR的下游通路,進而消除胃癌細胞對西妥昔單抗敏感性和耐藥性,研究顯示c?SRC介導 RANKL/RANK誘導的 EGFR的激活,并且c?SRC抑制劑逆轉了RANKL對西妥昔單抗的抑制作用[6]。
1.1.2 吉非替尼(Gefitinib,Iressa,易瑞沙) 吉非替尼是苯胺喹唑類小分子化合物,屬于可逆性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酪氨酸激酶(EGFR?TK)抑制劑,對EGFR?TK的抑制可阻礙腫瘤的生長、轉移和血管生成,并增加腫瘤細胞的凋亡。EGFR突變可增加EGFR對藥物的敏感性。然而,有研究[7]顯示EGFR激活突變患者對吉非替尼產生耐藥性,其原因與c?MET的異常表達有關。原發性耐藥可能與宿主體內的KRAS基因的突變有關,而繼發性耐藥與EGFR耐藥突變相關,是吉非替尼耐藥的主要原因,與EGFR相關的耐藥途徑有EGFR旁路效應、EGFR信號傳導路徑、EG?FR靶基因的自我突變(二次突變)。如 IGF?1R、EMT、Notch 旁路信號通路的激活,p?AKT、Bcl?2、p?mTOR蛋白的異常表達,c?Met基因擴增,EGFR?T790M 的二次突變等都可誘導耐藥[8]。 DARPP?32可通過促進EGFR和EGF受體ERBB3之間的相互作用和激活 PI3K?AKT信號傳導來增強胃癌細胞(MNK?28)對吉非替尼的抵抗力。 研究[8]顯示,胃癌細胞(MNK?28)中DARPP?32的敲除減少了小鼠腫瘤的平均體積,增加了對吉非替尼的敏感性。另外,EGFR 突變(T790M、D761Y、L747S、T854A),c?Met基因的擴增和PI3K/AKT激活均是吉非替尼耐藥的重要標志物[9]。
1.1.3 帕尼單抗(panitumumab) 結直腸癌治療藥Vectibix(panitumumab),是 IgG2 單克隆抗體,第一個完全人源化單克隆抗體,其靶向作用于EGFR。帕尼單抗在臨床試驗中并未對胃癌患者表現出任何益處,帕尼單抗與其他化療藥物結合的實驗因為其耐藥性和其他預實驗的結果已停止,還有些實驗正在使用帕尼單抗[10]。帕尼單抗聯合EOX(表柔比星+奧沙利鉑+卡培他濱)方案的臨床試驗并沒有明顯改善胃癌患者的疾病情況[11]。
1.2 抗HER2靶點人類HER2,該基因定位于染色體17q12,屬于原癌基因。其編碼產物HER2蛋白為185 kD的跨膜精蛋白,簡稱p185,由1255個氨基酸組成,720~987位屬于酪氨酸激酶區,HER2蛋白是具有酪氨酸蛋白激酶活性的跨膜蛋白。HER2蛋白主要通過與家族中其他成員包括EGFR(HERl/erbBI)、HER3/erbB3、HER4/erbB4 形成異二聚體而與各自的配體結合。HER2蛋白介導的信號轉導途徑主要有Ras/Raf/分裂素活化蛋白激酶(MAPK)途徑,磷脂酰肌醇3羥基激酶(P13K)/Akt途徑,信號轉導及轉錄激活(STAT)途徑和PLC通路等。HER2受體參與促進細胞增殖,抑制凋亡。胃癌患者中有13%~23%存在HER2過表達現象,HER2過表達與胃癌的分化程度、淋巴結轉移及組織分型密切相關[11-12]。 以 HER2 為靶點,阻斷或抑制 HER2 活化的信號轉導通路,可能會為HER2陽性胃癌患者提供一種更佳的治療方式。
1.2.1 曲妥珠單抗(Trastuzumab) 曲妥珠單抗是一種特異性針對HER2胞外區的人源化單克隆抗體,通過拮抗HER2信號傳導而抑制腫瘤細胞的生長與增殖[2]。根據臨床監測,曲妥珠單抗具有一定的心臟毒性作用[13-16]。但曲妥珠單抗作為一線治療在晚期胃癌中的平均有效時間僅一年。PTEN可特異性地催化磷脂酰肌醇三磷酸激酶(PIP3)去磷酸化,使胞質內PIP3的水平降低,抑制 AKT活化,從而下調PI3K?Akt通路。PTEN基因突變缺失的患者中,PI3K?AKT通路異常激活,更容易對曲妥珠單抗產生耐藥[17-18]。 HER3 也可通過激活 PI3K?AKT 信號通路,導致對曲妥珠單抗的耐藥。
1.2.2 拉帕替尼(Lapatinib) 拉帕替尼是口服小分子表皮生長因子(EGFR:ErbB?1,ErbB?2)酪氨酸激酶抑制劑,通過中斷EGFR/HER2相關的下游信號傳導級聯抗腫瘤[19]。因其是雙受體TKI,被賦予了更多的期待,然而數據證明拉帕替尼比所預期的療效低,主要原因可能是機體耐藥。拉帕替尼聯合紫杉醇治療胃癌,患者的總生存率并沒有顯著提高。拉帕替尼耐藥可能與HER2的二次突變、MET超表達以及下游磷酸酶的第10號染色體的缺失、PTEN的缺失和KRAS 的突變有關[20-22]。 研究[23]表明,HER3 受體通過激活PI3K?AKT通路誘導HER2陽性胃癌細胞對拉帕替尼耐藥,阻斷HER3受體可增加HER2陽性細胞對拉帕替尼的敏感性。
1.3 抗VEGF靶點VEGF又稱血管通透因子(vascular permeability factor, VPF)是一種高度特異性的促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具有促進血管通透性增加,細胞外基質變性,血管內皮細胞遷移、增殖和血管形成等作用。新生血管在促進腫瘤的發生發展過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腫瘤細胞需要通過新生血管從宿主向腫瘤組織輸送更多的營養和氧氣供其無限增殖;另一方面腫瘤組織也不斷地通過血管向宿主輸送腫瘤細胞,進而向遠處轉移浸潤[12]。因此抗血管生成已成為實體腫瘤的標準治療,近年來靶向VEGF的抗腫瘤藥物研究也在深入開展。血管內皮生長因子有5種不同的亞型,根據氨基酸的數目命名為 VEGF121、VEGF145、VEGF165、VEGF189、VEGF206,其中VEGF165為VEGF的主要存在形式。
1.3.1 貝伐單抗(Bevacizumab) 貝伐單抗是針對VEGF的重組人源化單克隆抗體。2010年在ASCO會議公布的一項關于貝伐單抗或安慰劑聯合順鉑和卡培他濱(XP方案)的Ⅲ期臨床研究發現,貝伐單抗并未顯著提高晚期胃癌患者的生存期,但貝伐單抗組患者較安慰劑組的無進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和腫瘤反應率(response rate, RR)均明顯提高[24]。
1.3.2 舒尼替尼(Sunitinib,Sutent) 舒尼替尼也是一種多靶點酪氨酸激酶抑制劑,其靶點 VEFGR、PDGFR等均與血管生成相關。遺憾的是,舒尼替尼作為一線藥物治療晚期胃癌患者的臨床療效并不十分顯著。一項納入78名亞洲晚期胃癌患者的Ⅱ期臨床試驗[25]結果顯示,舒尼替尼單藥僅可獲得2.6%的部分緩解率,僅有32.1%的受試者獲得>6周的疾病穩定期。
1.3.3 阿帕替尼(Apatinib) 阿帕替尼競爭性結合細胞內酪氨酸ATP結合位點,阻斷VEGF結合后的信號傳導。可引起白細胞減少、中性粒細胞減少、血小板下降、高血壓、蛋白尿、手足皮膚反應、乏力、食欲減退和腹瀉等副作用[26]。
1.3.4 阿柏西普(Eylea) VEGF 的可溶性誘餌受體,作用于靶點 VEGF?A、VEGF?B 和胎盤生長因子(placental growth factor,PIGF)抑制腫瘤血管的生成。一項FOLFOX聯合阿柏西普或安慰劑用于既往未接受過化療的轉移性胃食管腺癌患者的Ⅱ期(MEGA)研究[27]顯示阿柏西普未能在FOLFOX基礎上表現出顯著的療效。阿柏西普可引起白細胞減少、腹瀉、中性粒細胞減少、蛋白尿、AST增加、ALT增加、口腔炎、疲乏、血小板減少、高血壓、體質量減輕、食欲減退、鼻衄、腹痛、發聲困難、血清肌酐增加和頭痛等副作用。
1.3.5 雷莫蘆單抗(Reudian reab) 雷莫蘆單抗可防止VEGF配體和受體的結合,單藥用藥最常見的副作用(≥10%)有高血壓、腹瀉;聯合紫杉醇最常見的副作用有疲勞、中性粒細胞減少、腹瀉、鼻出血;聯合多西他賽最常見的副作用(≥30%)有中性粒細胞減少、疲勞/虛弱、口腔黏膜炎[28]。
1.4 抗mTOR靶點哺乳動物mTOR是一種絲/蘇氨酸蛋白激酶,其在多數腫瘤中過度激活。抗mTOR的靶向藥物可以阻斷該信號通路異常引起的惡性增殖。依維莫司在細胞內可與胞漿蛋白FKBP?12結合,形成復合物進一步與 mTOR復合物結合,從而抑制mTOR激酶活性[29]。根據近期公布的Ⅲ期臨床研究[30]結果,依維莫司并未明顯改善患者的總生存時間,研究顯示,這與pS6Ser240/4的低表達有關。
1.5 抗FGFR2靶點重組人FGFR2屬于受體型蛋白酪氨酸激酶,目前已知的FGFR主要包括4種類型,即 FGFR1、FGFR2、FGFR3 及 FGFR4。 臨床發現多種癌癥發生中伴隨著腫瘤組織的FGFR過表達和激活,它們可促進腫瘤血管形成和腫瘤細胞分裂增殖等,FGFR2基因的突變也可誘發腫瘤的發生[31]。目前針對FGFR2靶點的藥物主要有兩種:GAL?FR21和GAL?FR22,它們通過 GAL?FR21 與 FGFR2?Ⅲb 亞單位結合,GAL?FR22 與 FGFR2?Ⅲb 和 FGFR2?Ⅲc 亞單位結合,阻止 FGFs與 FGFR2的結合,GAL?FR21還能抑制FGFs誘導的FGFR2磷酸化,抑制胃癌移植瘤的生長[32]。
1.6 抗MET靶點MET也稱c?Met或肝細胞生長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HFG)受體,是一種絡氨酸激酶(tyrosine kinase)。MET基因位于人類7號染色體長臂(7q21?31),長度約 125 kb,同時含有 21個外顯子。c?MET是MET基因編碼產生的具有自主磷酸化活性的跨膜受體,屬于酪氨酸激酶受體(receptor tyrosine kinases, RTKs)超家族,由膜外Sema域、PSI域、IPT域和膜內JM域、催化TK域、C末端組成,主要表達于上皮細胞MET。MET的激活機制有多種,比如過度表達、基因擴增、基因變異、自源性或旁源性的 HGF 激活等[33-34]。
1.6.1 克唑替尼 氧化性DNA損傷是克唑替尼誘導胃癌細胞生長抑制的主要原因;克唑替尼以濃度依賴的方式提高了MET擴增型胃癌細胞的自噬水平[35]。
1.6.2 卡博替尼 卡博替尼是一個神奇的多靶點、小分子抑制劑,主要以抗血管生成為主,同時兼顧RET、MET 等靶點,在各種實體瘤中都有應用[36-37]。
1.7抗PD?1/PD?L1靶點PD?1 是近年來發現的負性刺激分子之一,為Ⅰ型跨膜糖蛋白,分子大小為55 kD,屬于CD28型家族,作為抑制分子表達于活化的T細胞和B細胞表面[38]。腫瘤細胞表面表達和分泌細胞 PD?L1,PD?L1與腫瘤浸潤淋巴細胞表面的PD?1分子結合后會抑制T、B淋巴細胞的活性,是腫瘤細胞逃避機體免疫的主要原因之一[39]。因此在腫瘤免疫治療中,基于PD?1為靶點的免疫治療藥物成為研發的熱點。PD?1由日本京都大學本庶佑(Honjo Tasuku)教授于1992年發現,1999年中國科學家陳列平發現了B7?H1,這是一個對免疫反應發揮負調控作用的蛋白,該蛋白隨后被證實能夠特異性結合PD?1,負調控淋巴細胞的激活。 PD?1/PD?L1通路除在免疫治療中具有重要作用外,抗PD?1抗體還可以作為癌癥診斷和預后的生物標志物發揮重要作用。
1.7.1 納武單抗(BMS?936559,Nivolumab) 施貴寶公司的 BMS?936558(Nivolumab)抗體在 2014年 7月于日本獲得上市批準,是全球首個獲批的抗PD?1抗體藥物,特異性結合 PD?L1,活化 T細胞,激活免疫系統,從而發揮抗腫瘤效果。目前批準上市的藥物適應癥有黑色素瘤、轉移鱗狀或非鱗狀非小細胞肺癌、腎細胞癌、霍奇金淋巴瘤、尿路上皮癌、結腸癌、前列腺癌等[40]。
1.7.2 派姆單抗(Pembrolizumab,商品名 Keytruda,簡稱K藥) 派姆單抗是人源化單克隆抗體,默沙東公司于2014年9月獲美國FDA批準上市的第一個PD?1免疫檢測點抑制劑,特異性結合 PD?L1,通過抑制PD?1/PD?L1細胞通路幫助機體免疫系統對抗癌細胞,從而發揮抗腫瘤效果,臨床證實包括肺癌、腎癌、黑色素瘤、頭頸癌、膀胱癌、尿路上皮癌、乳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腦膠質瘤、結腸癌、霍奇金淋巴瘤等晚期癌癥治療方面有顯著療效,有望實質性改善患者生存期,具有腹瀉、味覺障礙、甲亢、惡心等副作用[40]。
1.7.3 Lambrolizumab(MK?3475) 2014 年 9 月默沙東公司在美國獲批的首個抗PD?1藥物,是一種人源化抗體,為PD?1的抑制劑,主要用于治療晚期黑色素瘤[40]。
1.7.4 特善奇 Tecentriq (Atezolizumab,阿特朱單抗注射液) 2016年5月18日,美國FDA批準了羅氏基因泰克公司生產的Tecentriq,是人工合成的完全人源化單克隆抗體,一種PD?1/PD?L1抑制劑,用于治療非小細胞肺癌、尿路上皮癌、胃癌、膀胱上皮癌,常見有疲勞、咳嗽、惡心、皮膚瘙癢、皮疹、食欲減低、便秘、關節痛和腹瀉等副作用;是首個PD?L1單抗獲美國FDA批準用于治療尿路上皮癌,同時獲批的還有用于檢測 PD?L1蛋白表達水平的診斷性試劑盒Ventana PD?L1 (SP142),用于測定腫瘤浸潤免疫細胞 PD?L1 表達水平[41]。
1.7.5 巴文西亞(阿維木單抗,Avelumab) 由默克雪蘭諾(原研),輝瑞公司研制,2017年3月24日獲FDA批準上市,用于成人和12歲以上兒童的轉移性默克爾細胞瘤(皮膚癌的一種)的治療,也包括之前沒有接受過化療的患者。巴文西亞是一種人源化單克隆抗體,作為PD?L1阻斷劑,能與腫瘤細胞上的PD?L1結合,并阻斷其與T細胞及抗原遞呈細胞PD?1的相互作用,從而解除 PD?1/PD?L1介導的免疫抑制,促進T細胞攻擊腫瘤細胞,從而發揮抗腫瘤效果,具有惡心、轉氨酶升高、乏力等副作用。
1.8抗CTLA?4靶點CTLA?4 又名 CD152,是一種白細胞分化抗原,是T細胞上的一種跨膜受體,與CD28共同享有B7分子配體,而CTLA?4與B7分子結合后誘導T細胞無反應性,參與免疫反應的負調節。基因重組的CTLA?4 Ig可在體內外有效,特異地抑制細胞和體液免疫反應,對移植排斥反應及各種自身免疫性疾病有顯著的治療作用,毒副作用極低,是目前被認為較有希望的新的免疫抑制藥物[42-44]。
易普利姆瑪(Ipilimumab,商標名為 Yervoy),百時美施貴寶公司于2011年3月25日上市的一種單克隆抗體,CTLA?4是一種T淋巴細胞的負調節器,可抑制其活化,Ipilimumab與CTLA?4結合并阻礙后者與其配體(CD80/CD86)的相互作用。 阻斷 CTLA?4可增加T細胞的活化和增殖,Ipilimumab對于黑色素瘤的作用是間接的,可能是通過T細胞介導的抗腫瘤免疫應答而發揮抗腫瘤作用。適用于成人或12歲以上的轉移/不可切除黑色素瘤患者,用于皮膚黑色素瘤術后(包括淋巴結清掃)的輔助治療[45]。
1.9 抗JAK靶點JAK是一類非受體型酪氨酸蛋白激酶,分子量約(120~130)×103。 該家族包括JAK1、JAK2、JAK3、TYK2,JAK 家族無跨膜結構域和Src同源結構域,有7個JH(Janus homology)結構域,其中JH1為激酶結構域,JH2為假激酶結構域。不同的受體與不同的JAK家族成員偶聯。JAK2主要與紅細胞生成素受體、生長激素受體、催乳素受體和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受體等結合,通過信號轉導因子和轉錄激活因子(signal transductors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STAT)調節細胞增殖[46]。 針對 JAK2 的抑制劑,如 TG101209、G?6976、erlotinib、MK0457、CEP?701(lestaurtinib)等。 在體外,發現 G?6976是 JAK2直接的強有力的抑制劑,G?697同樣能夠抑制表達白血病相關的TEL?JAK融合蛋白以及骨髓增殖性疾病相關的JAK2 V617F突變的細胞的活化、存活及增殖。選擇性的JAK2激酶抑制劑TG101209可抑制與JAK2V617F以及MPLW515L相關MPNs細胞的酪氨酸激酶活性,引起JAK2V617F、STAT5以及STAT3的磷酸化受抑,JAK2抑制劑還可引起劑量依賴性的全血細胞減少[47]。JAK2的抑制劑AZD1480正在亞洲進行臨床Ⅰ期試驗(NCT01219543),AZD1480是有效的ATP競爭性的JAK1/2激酶小分子抑制劑,可抑制STAT3磷酸化和腫瘤生長,這種抑制存在STAT3依賴性。AZD1480通過影響腫瘤的微環境而抑制腫瘤血管生成和局部轉移[48-49]。
1.10 抗PARP靶點PARP?1是存在于真核細胞中催化聚ADP核糖化的細胞核酶,參與聚ADP核糖化真核細胞中蛋白質翻譯后的重要修飾方式。PARP?1在DNA修復和細胞凋亡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體外和體內研究表明抑制PARP?1可降低DNA修復功能,增強放療和化療對腫瘤的治療效果。目前PARP?1抑制劑已進入抗腫瘤藥物Ⅰ期臨床研究,PARP?1有望成為腫瘤治療的一個新靶點。
目前奧拉帕尼Olaparib正在對一線治療失敗的晚期胃癌開展Ⅲ期臨床試驗(NCT01924533)[50],其也作用于BRCA1或BRCA2突變。
1.11抗Claudin 18.2靶點人源性 Claudin18基因具有2個不同的第一個外顯子,產生兩種亞型Clau?din 18.1和Claudin 18.2。 這兩個分子的N端69個氨基酸的結構不同,其位于第一個胞外區的環狀結構內。Claudin18的兩種亞型分別在不同的組織中進行轉錄擴增,其中,Claudin 18.1主要表達于肺組織,而Claudin 18.2則特異性表達于胃癌患者的分化型胃壁細胞[51]。 而IMAB362作為全球首個靶向 Claudin 18.2的抗體,當該抗體附著在癌細胞的Claudin 18.2上,IMAB362通過抗體依賴的細胞介導的細胞毒性作用(antibody dependent cell?mediated cytotoxicity, ADCC)和補體依賴的細胞毒性作用(complement dependent cell?mediated cytotoxicity, CDCC)誘導胃癌細胞凋亡,并抑制細胞增殖,發揮其抗腫瘤活性。目前IMAB362已經獲得FDA和歐盟授予治療胃癌和胰腺癌的孤兒藥,IMAB362與化療組合生存期是化療的兩倍[52-53]。
2 中醫藥治療胃癌的研究進展
目前中醫藥抗腫瘤的基礎研究已經發展到了分子及基因水平,中醫藥抗腫瘤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研究中藥有效成分對胃癌細胞生長及凋亡的影響,闡明其對胃癌發生發展相關信號通路所產生的作用,揭示胃癌細胞的耐藥機制等。中醫認為,胃癌的形成與內外因關系密切,正氣不足貫穿于胃癌發病的始終[54]。胃癌細胞需要通過細胞內復雜的級聯信號傳導,調節胞內蛋白質或基因的表達,從而調控著細胞的生長、遷移、凋亡等多種生物學效應。因此治療胃癌強調補氣,以益氣健脾養胃、祛瘀解毒通降為原則,一些中藥復方治療胃癌的機制也被進一步闡明。中藥可以通過干擾信號通路中的某些因子的表達來阻斷信號的傳遞,從而抑制胃癌的發生發展。以下是中藥作用于相關信號通路具體機制的闡述。
2.1金果胃康膠囊Shen 等[55]研究發現,57 例胃癌前病變患者服用中藥制劑金果胃康膠囊后,在中高劑量組中可以明顯抑制EGFR的表達,臨床療效顯著,是逆轉胃癌前病變比較理想的方劑。
2.2 參佛胃康湯劑VEGF在胃癌細胞中高表達,參與腫瘤血管的生成。藺煥萍等[56]研究發現慢性萎縮性胃炎癌前病變小鼠胃黏膜組織中HIF?1α高表達,并且與VEGF、STAT3的表達可能成正相關,應用參佛胃康湯劑可以明顯降低 HIF?1α、VEGF和 STAT3的表達,并修復癌前病變小鼠的胃粘膜組織,減少異型性細胞的增生。
2.3消痰散結方白細胞介素?8(interleukin 8, IL?8)作為促血管生成因子與胃癌轉移密切相關。Shi等[57]研究發現消痰散結方可以抑制 VEGF?A的表達,并且通過抑制IL?8誘導的VEGFR?1和VEGFR?2的表達來抑制胃癌血管的生成。
2.4 胃安寧顆粒許尤琪等[58]發現胃安寧顆粒可通過抑制VEGF、Ki67的表達來抑制腫瘤血管的生成。
2.5 西黃丸Guo等[59]研究發現西黃丸可以阻止體內VEGF的表達,從而抑制胃癌細胞的生長。
2.6 健脾化瘀解毒方胃炎Ⅰ號曾進浩等[60]采用名老中醫劉友章教授的健脾化瘀解毒方胃炎Ⅰ號對胃癌前疾病(precancerous lesion of gastric cancer,PLGC)大鼠模型進行灌胃治療10周,發現該方能下調位于細胞核和細胞質中的Wnt信號通路Wnt1、Wnt3a、Cyclin D1 的表達,抑制 Wnt/β?catenin 信號通路的異常激活,在一定程度上阻斷和逆轉胃粘膜惡性轉變。
2.7 熊果酸熊果酸使ROCK1和PTEN激活,導致cofilin?1從細胞漿向線粒體轉位,細胞色素c釋放,caspase?3 和 caspase?9 活化,最終誘導胃癌 SGC?7901細胞凋亡[61]。
2.8 木犀草素木犀草素能夠抑制MAPK信號通路中細胞外信號調節激酶的磷酸化和PI3K信號通路中AKT,PI3K和雷帕霉素機制靶點的磷酸化,以此抑制胃癌的發生發展[62]。
2.9 蟾毒靈/順鉑順鉑是最常見的胃癌化療藥,但是由于其能夠激活AKT,所以會出現獲得性耐藥,研究[63]發現,蟾毒靈可以有效抑制AKT下游被順鉑活化的分子,從而逆轉順鉑的獲得性耐藥。
2.10葫蘆素葫蘆素(Cu?I)通過抑制 NRF2 通路顯著降低細胞內GSH/GSSG比率,從而破壞細胞氧化還原穩態,隨后以不依賴 p53的方式誘導GADD45α的表達,同時激活JNK/p38MAPK信號傳導,從而導致胃癌細胞凋亡[64]。
2.11硫化砷硫化砷(arsenic sulfide, As4S4)是雄黃的主要成分,可以抑制胃癌MGC803細胞的增殖,誘導細胞凋亡。研究[65]發現硫化砷能夠上調胃癌細胞中Bax和MDM2的表達,同時下調Bcl?2的表達,抑癌基因P53的表達也顯著增加。
2.12黃芩素PAR?2 活性、MMP?2 及 MMP?9mRNA的表達與胃癌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活化的 PAR?2可通過上調 MMP?2及 MMP?9 mRNA的表達而參與癌細胞遷移及侵襲。黃芩素能顯著抑制人胃癌SGC7901 細胞的 PAR?2 活性和 MMP?2、MMP?9 mRNA的表達,從而降低癌細胞遷移及侵襲能力,這與其抑制胰蛋白酶活性有密切關系,從而導致胃癌細胞SGC?7901的S期停滯,破壞線粒體膜電位,誘導細胞凋亡[66-67]。
2.13 復方胃腸安姬穎華等[68]發現中藥復方胃腸安可顯著提高Caspase?3的表達,促進細胞凋亡,并抑制腫瘤生長。
2.14 養正消積方熱休克蛋白27(HSP27)的磷酸化與AKT1和雌激素受體間的相互作用有關。HSP27的磷酸化可以促進胃癌的進展。研究[69]發現中藥養正消積方的提取物可以有效阻斷HSP27的磷酸化,從而抑制胃癌的進展。
2.15 苦參堿uPA蛋白的高表達可以促進胃癌的轉移。研究[70-71]發現,苦參堿可以有效降低 uPA蛋白的表達,并且能夠通過PI3K/Akt/uPA途徑抑制胃癌SGC?7901細胞的增殖和轉移。
2.16 小歸芍化濁解毒方RegI是再生基因家族的成員之一,主要參與組織的損傷和腫瘤的發生,血清PGI是反映胃粘膜形態和分泌功能良好的指標。研究[72]發現小歸芍化濁解毒方能夠明顯抑制RegI基因的表達并升高PGI的含量,能夠逆轉胃癌前病變并抑制胃癌的形成。
2.17 益氣健脾化積方益氣健脾化積方能逆轉胃癌SGC?7901/VCR細胞對長春新堿的耐藥性。其機制是通過下調耐藥基因/蛋白(P?gp、MRP、TUBB3 和STMN1)的表達,逆轉耐藥性,增強胃癌細胞對化療藥物的敏感性[73]。
2.18 斑貞一號聯合川芎嗪和5?氟尿嘧啶研究[74-75]發現斑貞一號聯合川芎嗪和氟尿嘧啶可以抑制胃癌細胞的耐藥性,原因在于用藥后降低了耐藥基因MDR1、LRP的表達。
2.19 健脾理氣方在胃腸道腫瘤中,TP的表達升高意味著胃癌對5?FU(五氟尿嘧啶)的敏感性提高,DDP的高表達與胃癌組織對5?FU的敏感性降低有關。CYP3A4是一種能夠活化5?FU的酶。研究[76]顯示于爾辛教授的健脾理氣方可以提高TP和CYP3A4的表達,降低DDP的表達,說明健脾理氣方可以提高胃癌對5?FU的敏感性和療效。
3 結論和展望
胃癌是全球范圍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中國的胃癌發病率高達 679.1/10 萬,死亡率達 498.0/10 萬[1](早期>50%,晚期<30%),但因早期診斷困難、漏診率高[77],確診時多為晚期,已喪失最佳治療時間[78]。胃癌的主要治療方式有手術、化學療法、放射療法和靶向藥物治療,但在治療的同時出現了耐藥、腫瘤轉移和復發等未解決的問題[79]。缺少有效的分子靶點和高效低毒的抗癌藥物是目前胃癌治療的難點和熱點。
通過分類歸納目前胃癌靶向治療主要的11類靶點,詳細總結了每種靶點靶向治療胃癌的西藥用藥情況和分子作用機制;綜述19類胃癌靶向治療中藥物的作用靶點和調控機制,大多數都是通過抑制或阻斷靶點通路、蛋白質抗體或受體、上調或下調基因功能和蛋白的表達而抑制胃癌腫瘤細胞的生長、增殖,使胃癌腫瘤細胞萎縮、凋亡直至死亡,從而達到中藥的治療作用。由此可見,中藥在治療胃癌方面體現出了巨大的優勢,但胃癌的形成機制復雜,并受多方面因素影響,而且中藥包括單方制劑和復方制劑,治療的機制和作用也非常復雜,其中復方中藥制劑由于成分復雜,其靶向治療胃癌的效應機制仍存在爭議。過去對胃癌的用藥主要是側重傳統化療藥物,副作用較大,近年來應用靶向藥物進行抗腫瘤的研究,我們應該更加深刻地認識腫瘤的發病機制,深入了解靶點的分子機制,真正做到“對癥下藥”,才能解決小分子靶向藥物的獲得性耐藥和毒副作用等方面的問題,才能使靶向藥物發揮更好的療效[80]。另外,靶向藥物的應用需根據患者自身遺傳學背景和腫瘤細胞生物學特性進行選擇,實行“個體化治療”[81-82]。
隨著中醫藥抗腫瘤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萃取中藥抗腫瘤有效成分,從分子水平闡明中醫藥自身結合腫瘤細胞相互作用的抗腫瘤機制,為進一步研發出新的靶向治療藥物提供思路,并采用先進的生物免疫機理研發出有效的抗腫瘤中藥,應用中醫藥靶向治療胃癌,同時降低毒副作用,在提高患者的治愈率和生活質量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和廣闊的前景。從中藥中篩選有效單體可開發為高效低毒的靶向抗胃癌中藥,同時把 ID1、MYC、SHMT1[83-86]等這些在胃癌或其他多種惡性腫瘤中高表達的基因或蛋白作為中醫藥抗癌靶標,是我們團隊目前和未來研究的目標和方向之一。